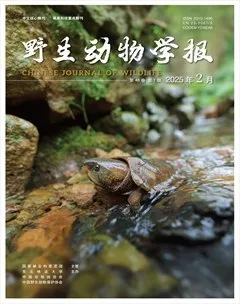大豐沿海濕地越冬雁鴨類的種子傳播網絡研究






關鍵詞:雁鴨類;植物種子;沿海濕地;種子傳播網絡;網絡結構
鳥類是生態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植物種子傳播的過程中充當著重要角色[1]。對于濕地植物而言,水鳥的種子傳播對于植物更新和定殖尤為重要[2?3]。依據傳播方式的不同,濕地水鳥對種子傳播分為體外傳播和體內傳播。水鳥不僅可以通過糞便在水生和陸地生態系統內部或之間傳播種子,也可以讓種子附著在其羽毛中進行長距離傳播[4]。海岸帶濕地植物的主要傳播鳥類有大型食草性鳥類(雁類和鶴類)、中型雜食性鳥類(潛鴨類和鷗類)以及小型食無脊椎動物的鳥類(鸻鷸類)等。其中,雁鴨類被認為是濕地植物種子的主要傳播類群,它們依賴濕地生存,取食濕地植物種子,數量眾多,流動性強,通常在繁殖區和越冬區之間進行長途遷徙[5]。雁鴨類與濕地植物間的互相作用也形成了復雜的種子傳播網絡。
現有鳥類互作網絡研究主要是利用R語言中的bipartite函數繪制帶有節點和邊際的圖形來表示鳥類與植物間的關系[6]。同時,也可以從網絡水平根據嵌套度(nestedness metric based on overlap and decreasingfill,NDOF)、連接度(connectance,C)、模塊性(modularity,Q)、專化程度(specialization,H'2)和物種度(species degree,SD)等結構特征對鳥類-植物網絡的拓撲結構進行定量分析[7?13]。鳥類-植物之間的互作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植物與鳥類的連接包含在一組更大的連接集合中,顯示出明顯的嵌套結構[14]。當物種處于由高度聯系的物種組成的半獨立群體時,這種網絡或許也是模塊性的[15?16]。互作網絡的結構對群落穩定及其從干擾中恢復的能力具有重要影響[14,17]。因此,了解鳥類-植物互作網絡的結構非常重要。目前對食果鳥類的種子傳播網絡研究相對較多[18]。相比之下,涉及雁鴨類等濕地水鳥的種子傳播研究在所有生物群落中仍然很少[19?20]。近年研究表明,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顯示出嵌套結構,其方式與食果鳥類的傳播網絡相似,但模塊性有高有低,如Sebastián-González et al.[21]研究的古北界水鳥種子傳播網絡顯示出低模塊性,而Silva et al.[22]研究的新熱帶地區的水鳥種子傳播網絡是呈模塊性的,這可能與每個網絡內在因素的差異或者研究方法之間的差異相關。
大豐沿海濕地是一個典型的海岸濕地生態系統,水鳥種類豐富,植被類型繁多,是進行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研究的理想地。本研究選取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北部區域為研究地,調查4種不同生境類型中的雁鴨類多樣性,收集雁鴨類糞便排放數據;鑒定糞便中植物種子種類并構建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以期回答以下2個問題:(1)大豐沿海濕地雁鴨類及其傳播植物物種如何組成?(2)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具有什么樣的特點?研究結果擬探討雁鴨類與濱海濕地植物之間的互作關系,為揭示雁鴨類對濕地植物的種子傳播作用及其在濕地生態系統功能和多樣性維持中的作用機制,進而為濱海濕地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恢復提供案例支撐。
1 研究區概況
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位于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32°59′—33°3′ N,120°47′—120°53′ E),是典型沿海灘涂濕地類型的保護區。保護區地處亞熱帶向暖溫帶的過渡地帶,氣候特點是海洋和季風的過渡類型。冬季受大陸季風影響,干旱少雨,低溫霜凍;夏季受海洋季風影響,高溫,降雨豐富。常年平均氣溫14. 1 ℃,年降水量1 068 mm,降雨多集中在6—9月[23]。研究區位于保護區北部,其中分布有河流、灘涂和池塘等多類型濕地,為雁鴨類提供了適宜的棲息環境。
2 研究方法
于2022年11月—2023年5月,采用樣點法調查雁鴨類多樣性,分別在灘涂、河道、魚塘和農田4種生境各設置4個樣點,共16個樣點。每個樣點觀察范圍是半徑為500 m的圓形區域,只記錄飛入樣圓的雁鴨種類和數量,飛出的雁鴨類不記錄。根據潮汐情況,選擇合適的時間進行調查,一般調查時間段為08:00—11:00和14:00—17:00。使用Kowa雙筒望遠鏡(BD 10 × 42 XD)和SWAROVSKI單筒望遠鏡(ATS 80HD)觀察并用佳能相機拍照,數據記錄包括每個樣點的經緯度、生境類型、雁鴨類的種類和數量等信息。當雁鴨類數量較低時,直接記錄雁鴨類種類、數量等;當數量較高無法確切計算時,以拍照來估計雁鴨類集群數量。每天調查2種生境,共8個樣點,2 d為一個調查周期,每個周期重復9次,累積調查時間108 h。
在每種雁鴨類集群處定點駐守觀測,在其停歇地設置多個1 m × 1 m 的樣方,收集樣方內新鮮糞便,并輔以糞便的外形、長度和顏色等特征進行區分,分裝在密封袋內保存,并標記樣方編號、鳥種名稱及糞便數量[24]。糞便收集后,先用自來水通過0. 062 mm(250目)的篩子沖洗每個糞便樣本以獲得植物種子,然后將種子歸類并采用直接計數統計種子數量[25]。采用改良2 × CTAB法提取植物種子總DNA,使用葉綠體基因片段,通過NCBI數據庫進行BLAST堿基比對,進行物種鑒定。
3 數據分析
雁鴨類的種類鑒定主要依據《中國鳥類分類與分布名錄》(第4 版)[26],居留型劃分按照《江蘇鳥類》[27]。當某種雁鴨的個體數量占雁鴨類總數量的比例P ≥ 10. 0% 時,該種雁鴨為優勢種;當1. 0% ≤P lt; 10. 0% 時,該種雁鴨為常見種;當0. 1% ≤ P lt;1. 0%時,該種雁鴨為稀有種;當P lt; 0. 1%時,該種雁鴨為罕見種[28]。
在雁鴨類群落結構特征分析中,采用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Pielou均勻度指數和Simpson優勢度指數來評價不同雁鴨群落的多樣性[29]。
基于雁鴨類各物種與植物種子之間的取食關系,構建種子傳播網絡,在R 4. 1. 0軟件中利用plotweb函數繪制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在網絡水平上,采用連接度、嵌套度、模塊性和專化程度4種網絡結構參數評估雁鴨類在網絡結構中的作用。在物種水平上,采用物種度(species degree,SD)、物種強度(species strength,SS)、連接多樣性(partner diversity,PD)和專化指數(specificity index,SI)4 種參數評估。網絡水平和物種水平參數均在R 4. 1. 0軟件中使用Bipartite包中species level函數運算。
4 結果
4. 1 不同生境雁鴨類群落多樣性
2022年11月—2023年5月共記錄雁鴨類11種5 666 只。斑嘴鴨(Anas zonorhyncha)和綠頭鴨(A.platyrhynchos)為優勢種,普通秋沙鴨(Mergus mer?ganser)為罕見種,另有赤膀鴨(Mareca strepera)、羅紋鴨(M. falcata)和綠翅鴨(Anas crecca)3種為常見種,豆雁(Anser fabalis)、赤頸鴨(Mareca penelope)、琵嘴鴨(Spatula clypeata)、翹鼻麻鴨(Tadorna tadorna)和針尾鴨(Anas acuta)5 種為稀有種。調查到近危(NT)物種1種,即羅紋鴨。從居留型上看,11種雁鴨類均為冬候鳥。雁鴨類總體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為1. 144,Pielou 均勻度指數為0. 477,Simpson優勢度指數為0. 401。
從不同月份雁鴨類的種類和數量變化來看,其種類和數量從2022年11月(8種1 894只)起呈短暫的遞增趨勢,至2022 年12 月均達到峰值,為9 種2 632只,之后逐月遞減,到2023年5月僅記錄到1種7只斑嘴鴨。
從不同生境間雁鴨類的種類和數量來看,灘涂生境的雁鴨類種類和數量最高,河道生境次之,農田生境僅記錄到5只斑嘴鴨,魚塘生境未發現雁鴨類。從多樣性指數來看,灘涂生境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和Pielou均勻度指數均高于河道生境,而河道生境Simpson優勢度指數高于灘涂生境(表1)。
4. 2 雁鴨類糞便中植物種子組成
在調查的11種雁鴨類中,有4種雁鴨參與了濕地植物種子傳播(圖1)。在灘涂生境采集到斑嘴鴨、赤膀鴨、綠頭鴨和綠翅鴨的糞便共1 551粒,其中斑嘴鴨的糞便數量最多,占糞便總數的59. 19%;綠翅鴨的糞便數量最少,占糞便總數的2. 77%。在6. 77%的鴨類糞便中至少含有1顆植物種子,其中1. 16%的鴨類糞便中含有完整種子,5. 61%的鴨類糞便中含有破碎種子。
在鴨類糞便中分離出植物種子共121顆,其中14. 88%的種子完整,85. 12%的種子破碎。斑嘴鴨糞便中分離出的種子數量最多,占種子總數的85. 95%,綠翅鴨糞便中分離出的種子數量最少,占種子總數的0. 83%。斑嘴鴨糞便中分離出95. 19%的植物種子均是破碎種子,綠頭鴨和綠翅鴨的糞便中分離出的種子均是完整的(表2)。
通過種子葉綠體基因鑒定表明,在雁鴨類糞便中的植物種子共有9種112顆,其中5種鑒定到種水平,包括扁稈荊三棱(Bolboschoenus planiculmis)、齒果酸模(Rumex dentatus)、葎草(Humulus scandens)、烏桕(Triadica sebifera)和水稻(Oryza sativa);4種鑒定到屬水平,包括莎草屬(Cyperus)種子3種和楊屬(Populus)種子1種(圖2)。從種子數量上看,扁稈荊三棱種子占比最高,為82. 64%,其次是水稻種子(3. 31%),烏桕種子和莎草屬種子占比均為1. 65%,其他3種種子的占比較少,均為0. 83%。
4. 3 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
2022 年11 月—2023 年5 月的鴨類與植物種子傳播網絡由9種植物和4種鴨類構成(圖3)。網絡結構分析(圖3)顯示,網絡連接度為0. 25,專化程度為1,嵌套度為0,模塊性為0. 152。鴨類物種度為1 ~4,其中斑嘴鴨最高,與4 種植物連接;物種強度為1 ~ 4,斑嘴鴨最高,綠頭鴨和綠翅鴨最低;連接多樣性為0 ~ 1. 040,其中赤膀鴨最高,而綠頭鴨和綠翅鴨只記錄到傳播1種植物種子,連接多樣性為0;專化指數均為1(表3)。植物物種度均為1,每一種植物種子只被一種鴨類傳播;物種強度為0. 010 ~1. 000,其中水稻和楊屬最高,齒果酸模和葎草最低;專化指數為0 ~ 1. 000,其中水稻和楊屬最高,齒果酸模、葎草和烏桕最低(表4)。
5 討論與結論
大豐沿海濕地灘涂遼闊、河蕩眾多,為水鳥的棲息生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該區域地處候鳥遷徙通道的重要地段,是候鳥遷徙的重要停歇地、也是部分候鳥的越冬地,其中雁鴨類種類豐富且數量較多[30]。本研究首次以大豐沿海濕地為研究地,調查了雁鴨類與植物之間的互作關系,其結果有利于濱海濕地的科學保護。
本研究共記錄雁鴨類11種,大多分布于灘涂生境,其中有4種雁鴨傳播9種植物種子。與已有的雁鴨類等水鳥傳播網絡研究相比,大豐沿海濕地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的結構簡單,雁鴨類種類和植物種類較少,顯示出無嵌套(NODF = 0)且模塊性(Q =0. 152)較低的特征。Sebastián-González et al.[21]通過對古北界雁鴨類等水鳥和被子植物互作網絡的研究發現,其與食果鳥類種子傳播網絡之間存在重要差異,種子傳播網絡的結構與鳥類特征和植物特征有關,如鳥類體型和果實營養成分等,并未發現物種特征對雁鴨類等水鳥網絡有顯著影響。相比之下,大豐沿海濕地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結構簡單,網絡中物種量較少,網絡無嵌套。這或許是由于一些雁鴨類更喜歡取食植物根莖或水生無脊椎動物等[31];其次由于雁鴨類喙中的細薄片結構,使得不少體積小的種子在取食時被過濾掉[32]。因此本研究中雁鴨類種類和雁鴨類糞便中的種子十分有限,每種植物種子也只存在于一種雁鴨類糞便中。無嵌套性說明種子傳播網絡穩定性差,應對環境變化的抵抗力低[33]。在大豐沿海濕地中,每種植物只與一種雁鴨類連接,若一些雁鴨類消失,可能會影響該植物種子的傳播。低模塊性可能由于本研究網絡中只包含一類具有相同分類地位的鳥種即雁鴨類,當種子傳播者具有較大的形態或生態差異時,種子傳播網絡中的模塊性才更為常見[34]。低模塊性也可能由于大豐沿海濕地種子傳播的生境為連續的灘涂,與內陸濕地相比,灘涂破碎化程度較低,受環境壓力較小,雁鴨類和植物間緊密互作較少。
斑嘴鴨在本區域數量最多,分布范圍最廣,采集到的糞便量及完整種子數量都高于其他雁鴨類,故推測斑嘴鴨對于濕地植物種子傳播的貢獻最大。常見雁鴨類除了可以幫助植物種子進行長距離傳播之外還有著一些潛在貢獻,如雁鴨類取食植物種子后,植物種子經腸道作用可打破種子的休眠限制,提高種子萌發率;同時,以糞便排出的種子具有足夠的有機質作肥料而更容易萌發[32]。此外,在被傳播的植物中扁稈荊三棱種子數量最多,均被斑嘴鴨所傳播。扁稈荊三棱是一種常見的水生植物,多生于水田、河灘和沼澤地等處[35],繁殖方式多樣,包括種子繁殖、根莖分生和碎片生殖等,使其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擴張,占據水域資源[36],因此易于被斑嘴鴨輕松取食。扁稈荊三棱結實量較大能夠產生廣告效應,吸引斑嘴鴨取食。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大豐沿海濕地雁鴨類種子傳播網絡的結構特征,以及常見雁鴨類在濱海濕地中的生態作用,為評估濱海濕地植物群落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推動生態保護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科學依據。鳥類-植物相互作用是生態系統中較為復雜的過程,想要系統了解海岸帶雁鴨類鳥類種子傳播網絡應開展長期持續研究,延長年度調查時間,并擴大研究水鳥類群,不斷充實互作網絡的物種組成。此外,本研究并未涉及植物種類多樣性對種子傳播網絡結構的影響分析,在后續試驗中應加以研究,以期更好地揭示濕地生態系統中水鳥與濕地植物之間的互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