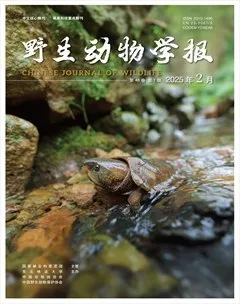紅喉歌鴝黑龍江種群遺傳多樣性和遺傳結構分析






關鍵詞:紅喉歌鴝;細胞色素b 基因;遺傳多樣性;遺傳結構;種群擴張
紅喉歌鴝(Calliope calliope)又名紅點頦,屬雀形目(Passeriformes)鹟科(Muscicapidae)[1],外觀美麗、鳴聲悅耳,是野生鳥類非法捕捉和貿易的重要目標之一[2]。同時,棲息地的破壞和片段化嚴重威脅該物種的生存和繁殖,導致其種群數量進一步下降[3?4],現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5]。
紅喉歌鴝廣泛分布于古北界地區,包括指名亞種(C. c. calliope)、勘察加亞種(C. c. camtschatken?sis)[6?7],以及3個尚有爭議的亞種(庫頁島亞種C. c.sachalinensis、阿納德爾亞種C. c. anadyrensis 和青海亞種C. c. beicki)[6,8?10]。其繁殖地域從烏拉爾山脈延伸至太平洋西岸及鄰近島嶼,包括中國東北、西北部分地區[6?11]。紅喉歌鴝是遷徙鳥類,每年4 月初和9月末沿中亞和東亞-澳大利亞2條路線遷徙[12?15]。它們具有固定的遷徙路線和較強的筑巢保守性,使得各個種群的繁殖區每年保持相對穩定[8]。
紅喉歌鴝的線粒體基因組順序與家雞相同,只有一個細胞色素b 基因(Cyt b)拷貝[4]。Spiridonovaet al.[8?10]揭示了紅喉歌鴝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種群具有較高的Cyt b 基因遺傳多樣性,并將其劃分為3個支系(Clade):西伯利亞大陸支系,庫頁島支系及勘察加半島、千島群島、北海道支系。基于西部支系Cyt b 的核拷貝(nuclear copies of mitochondrial genes,Numt)與東部支系Cyt b 序列間的高度相似性,Spiridonovaet al.[9?10]提出了Numt與線粒體基因的同源重組機制,并以此為線索說明了紅喉歌鴝由西伯利亞向遠東地區擴散、定殖的過程。
紅喉歌鴝是黑龍江常見的繁殖鳥類,其遺傳多樣性水平和遺傳結構,以及是否存在東部支系的單倍型滲入仍不清楚。為此,本研究測定了黑龍江種群85只個體的Cyt b 基因序列,結合已有報道的同源序列進行了綜合分析,以期揭示該種群遺傳狀況,為制定合理的物種保護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 1 樣品采集和序列下載
采集黑龍江省北安市(48°18′ N,126°42′ E)繁殖種群(n = 85只)紅喉歌鴝死體肌肉樣本,根據形態學方法[16]鑒定,包括40只雄性、45只雌性。所有樣本均由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野生動植物檢測中心查沒所得。此外,從GenBank中下載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135只紅喉歌鴝的Cyt b 基因序列(表1),以及黑胸歌鴝(C. pectoralis)(KJ456329)[19]和歐歌鴝(Lus?cinia luscinia)(MT410894)的同源序列。220只紅喉歌鴝樣本信息依據產地不同劃分為7個種群,分別標記為Pop1 ~ Pop7(圖1)。
1. 2 DNA 提取、擴增和測序
使用DNA 提取試劑盒(UElandy,蘇州)提取基因組總DNA。為消除Numt 干擾,利用NCBI 的Primer-BLAST程序設計2對引物(5′-TGAAAATACCAGCTTTGGGA-3′,5′-TCGTATCTTGATCTATCCTACAAT-3′;5′-CTTTGCCTTATCCATCCTCA-3′,5′-TAACTCTAAGAAGGGGCGAA-3′),采用巢式PCR 策略擴增。PCR 體系為50 μL,包括2 × Easy Taq Super‐Mix(TransGen,北京)25 μL,DNA模板10 μL(20 ng/μL),正、反向引物各1 μL(10 μmol/L),滅菌去離子水13 μL。擴增采用PE-9700 型DNA 擴增儀,反應程序:94 ℃預變性6 min;94 ℃變性30 s,55 ℃退火30 s,72 ℃延伸1 min 30 s,30個循環;72 ℃延伸10 min。利用1. 5% 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PCR 產物,將條帶清晰且單一的PCR產物送至黑龍江箭速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進行純化和雙向測序。
1. 3 數據分析
利用DNAstar軟件包的SeqMan校對雙向測序峰圖。利用ClustalW2[20]對所有Cyt b 序列進行多重序列比對。利用MEGA 11統計[21]序列堿基組成、突變位點數以及轉換/顛換比。利用DnaSP 6[22]確定單倍型,計算核苷酸多樣性(nucleotide diversity,π)、單倍型多樣性(haplotype diversity,h)和平均核苷酸差異(average number of nucleotide differences,K)。
使用ModelFinder 2. 2. 2[23]根據BIC(Bayesian informationcriterion)標準選擇最佳堿基替換模型。利用MrBayes 3. 2[24](密碼子1和2為HKY+F+I;密碼子3為GTR+F+G4)和IQ-TREE 2. 2. 2[25](密碼子1和2為TN+F+R2;密碼子3 為TIM2+F+G4)分別構建BI(Bayesian inference)和ML(maximum likelihood)系統發育樹。BI 法將馬爾可夫鏈運行5 000 000 代,每100 代采樣一次,舍棄前面25% 的樹,由后驗概率(posterior probability,PP)評估置信度。ML法采用自舉法(bootstrap,BP)抽取1 000次檢驗分支可信度。利用POPART[26]基于中值連接法(median joiningmethod)構建單倍型網絡。利用Arlequin 3. 5[27]開展分子方差分析AMOVA(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并計算種群間的遺傳分化指數(FST)。
利用DnaSP 6 進行中性檢驗(Tajima’s D,Fu’sFS),基于恒定群體模型(constant population size)估計核苷酸錯配分布。利用BEAST 1. 8. 4[28]的貝葉斯天際線圖(Bayesian skyline plot,BSP)分析種群歷史動態。基于最適替換模型(GTR+F+I+G4)和嚴格的分子鐘(0. 021/Ma[29])獨立運行2次,每次運行200 000 000代,每200代采樣一次。BI和BSP的結果在Tracer 1. 7中[30]通過判斷所有參數的有效樣本量(effective sample size,ESS)是否大于200來確定是否收斂。
2 結果
2. 1 Cyt b 序列特點和遺傳多樣性分析
測序獲得85條Cyt b 基因全長序列(1 143 bp),已提交至NCBI(登錄號PP407082—PP407166);結合在GenBank下載的1條尚志市的序列,共計86條黑龍江種群Cyt b 序列。序列平均堿基組成為:27. 81% A、24. 75% T、33. 87% C、13. 57% G,A + T含量(52. 56%)略高于C + G 含量(47. 44%)。檢測到64個變異位點(5. 6%),其中26個為簡約信息位點,38個為單突變位點。序列轉換顛換比為15. 4,沒有出現堿基插入/缺失現象。
220只紅喉歌鴝鑒定出138個Cyt b 基因單倍型(表1,表2)。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2個單倍型為H2(31次)、H9(9次),單倍型H2分布于7個種群、H9分布于3個種群(種群1、6、7)。黑龍江種群(種群1)具有42個獨特的新單倍型,以及8個共享單倍型。7 個種群都有較高的單倍型多樣性(h 為0. 934 ~1. 000),而核苷酸多樣性和平均核苷酸差異在不同的種群間差異較大。種群4、7遺傳多樣性較高(h 為0. 971 ~ 0. 982,π 為0. 008 0 ~ 0. 008 1,K為9. 142 9 ~9. 204 7),其次是種群2、3、5、6(h 為0. 960~ 1. 000,π 為0. 004 3~ 0. 005 9,K 為4. 964 3~ 6. 719 1)。種群1 的遺傳多樣性最低(h 為0. 934,π 為0. 003 0,K = 3. 405 2),主要體現在π 和K 兩個指標。
2. 2 種群遺傳結構和種群歷史動態分析
根據系統發育分析和單倍型網絡(圖2,圖3),138個Cyt b 基因單倍型可以劃分為3個支系,分別代表大陸種群(西部的Clade Ⅰ),庫頁島種群以及勘察加半島、千島群島、北海道種群(東部的Clade Ⅱ和Clade Ⅲ)。黑龍江種群的單倍型均聚集于西部支系、屬于大陸種群(圖2,圖3)。然而,3個支系間的系統發育關系尚未明確,ML樹和BI樹存在拓撲沖突。將3個支系展示在地圖上(圖1),發現7個種群都含支系Ⅰ的單倍型,其所占的比例由西向東逐漸降低,這與Spiridonova et al.[9?10]的結果一致。黑龍江種群不包括島嶼種群的單倍型,譜系混合的現象僅出現在海岸線及鄰近地區。雌雄個體在系統發育上無明顯區別。
7個種群的分子方差分析表明種群間變異和種群內變異相當,分別占總變異的51. 43%和48. 57%(表3)。將大陸種群(種群1、2、3、4、7)作為一個整體分析時,種群間變異略微提高(54. 12%)。種群1與種群4、5、6、7存在顯著分化(P lt; 0. 05)(表4),其中,與種群4屬于中等遺傳分化(FST = 0. 283),而與種群5、6、7 屬于高度遺傳分化(FST 為0. 432 ~0. 736)。
中性檢驗顯示(表2),除種群7的Tajima’s D 為正值外,其他種群均為負值,種群1 中差異極顯著(P lt; 0. 01);所有種群的Fu’s FS均為負值,種群1、4、5、6差異極顯著(P lt; 0. 14);種群1中性檢驗的值均最小(Tajima’s D = -2. 460 4,Fu’s FS = -26. 234 9)。這表明種群1最近經歷了明顯擴張,與核苷酸錯配分布呈現單峰曲線結果一致(圖4,雄∶雌= 0. 9∶1)。貝葉斯天際線圖(圖5)顯示,Clade Ⅲ群體在大約3. 5萬 ~ 4. 3萬a前有略微增長,Clade Ⅱ群體趨于穩定,而Clade Ⅰ群體在1. 5萬 ~ 5. 5萬a前經歷了快速增長。在屬于Clade Ⅰ的3 個種群中,只有種群1在2. 5萬 ~ 5. 5萬a前經歷了擴張。然而,種群1雌性群體的錯配分布為多峰特征,不同于雄性群體,不支持種群增長的推斷。
3 討論
遺傳多樣性是物種生存與進化的基礎,具有較高遺傳多樣性的種群有更強的適應性和生存能力[31?32]。h 和π 是評價遺傳多樣性的2個主要指標。h 關注單倍型的數目和頻率,與短期種群動態更為相關,而π 表示隨機2個單倍型核苷酸位點差異的數量,通常需要長時間積累[33]。根據Grant et al.[34]以h和π 評估種群遺傳多樣性水平的標準(臨界值分別是0. 5和0. 5%),黑龍江紅喉歌鴝種群h 較高、π 較低。然而,這2個指標都低于同屬于Clade Ⅰ的種群2和3,特別是π。這暗示黑龍江種群過去可能經歷了遺傳多樣性的丟失,然后通過種群擴張增加了h,但因時間較短,π 積累不足。結合黑龍江種群近期的擴張和其他種群的穩定,可能的解釋是該種群經歷了瓶頸事件。然而,由于分子標記的限制,無法獲取黑龍江種群更早期的動態。此外,考慮到黑龍江種群的h 仍低于其他種群,不能排除先前過度捕獵活動和生境破壞對該種群遺傳多樣性的影響。《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將紅喉歌鴝增列為二級保護動物[5],通過嚴格執法能減少非法捕捉行為。結合對黑龍江種群繁殖區棲息地的保護,特別是紅喉歌鴝偏好的森林、灌叢和草地等[11],有利于維護其種群遺傳多樣性水平。
本研究表明紅喉歌鴝種群呈現較為清晰的遺傳結構(圖2,圖3),這與對蘆鹀(Emberiza schoenic?lus)[35]和煤山雀(Periparus ater)[36]的研究結果類似。不同的是,北長尾山雀(Aegithalos caudatus)受到不完全譜系分選(incomplete lineage sorting)或二次接觸(secondary contact)的影響而存在譜系混合[35]。黑龍江種群個體均屬于大陸種群單倍型、且與大陸沿海及島嶼種群(種群4、5、6、7)間均存在顯著分化。這證實了黑龍江種群屬于指名亞種,并厘清了島嶼單倍型(Clade Ⅲ)向大陸滲入的界限:海岸線附近、形成一個“過渡帶”,未深入大陸內部。這種“過渡帶”可由生態應力帶(tension zone)理論解釋[37],即其是由個體擴散和自然選擇相互平衡產生的副產物。另外,大陸種群和島嶼種群可能具有不同的遷徙路線[12?15],這可能會減少島嶼種群在遷徙過程中向大陸種群的滲透機會。
動物種群的擴張通常與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maximum,LGM,1. 6萬 ~ 2. 7萬a前[38])后的地理分布的擴張有關[39]。然而,黑龍江種群在更新世晚期的LGM前經歷了種群的快速擴張(2. 5萬 ~ 5. 5萬a前),這可能與中國東北地區更新世晚期的氣候波動有關[40]。同時,該地區具有豐富森林棲息地和其他潛在避難所[41?42],為紅喉歌鴝度過LGM提供了生存空間。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北美北方森林19種同域分布鳥類種群歷史動態的研究中[43]。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BSP 分析使用的Cyt b 突變率為Weir etal.[29]估計的12個目鳥類的平均堿基替換速率。考慮到體型較小的紅喉歌鴝可能具有更高的堿基替換率[44],這可能導致估計的種群擴張時間偏早。此外,與種群擴張相反,雌性群體的核苷酸錯配分布呈現多峰特征,這可能是雌性偏倚擴散(female-biaseddispersal)的結果[45?46]。環志研究發現雌性個體對領地的忠誠度較低,或者更難重新捕獲(own data)[13]。這也符合紅喉歌鴝的繁殖特性:雄鳥負責筑巢和領地防御,雌鳥通過選擇雄鳥及其領地參與繁殖;這導致雄性對出生地的環境和資源更加熟悉、傾向于留在出生地,而雌性則更傾向于向外擴散。然而,目前仍缺乏紅喉歌鴝雌性偏倚擴散的直接證據,對該現象的判斷還需結合更廣泛的宏微觀研究結果。
由于線粒體基因僅通過母系遺傳,無法涵蓋父系遺傳信息,因此可能無法提供完整的種群遺傳信息。對黑龍江紅喉歌鴝種群遺傳多樣性、遺傳結構的深度剖析還需要配合其他分子標記的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