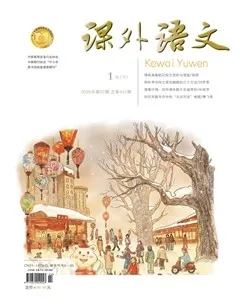賞析《馬說》:古代文學中的隱喻藝術
★“隱喻”——作為凝聚中華歷史文化與先祖審美而產生的文學藝術,歷經數千年文學典籍的靈氣滋養,已經成為中國文學藝術寶庫中一株耀眼的奇葩,因此,它已經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修辭手法與寫作手法,更是革新之后極具美學功能的文學手段。這種更新,不僅體現在傳統文章的遣詞造句之中,更體現在藏于隱喻背后的對作品本身的深度思考。以韓愈的《馬說》為例,他突破性地選擇以馬來作為喻體,意向跳躍,想象大膽,在整部作品中通篇使用隱喻意象,以馬喻人,構筑了暗諷封建統治者埋沒人才的意義層次,從而提升了《馬說》的文學及審美境界。因此,本文將對《馬說》中的寫作手法進行拆解,分析藏于其中的隱喻藝術。
一、“說”字立骨,理隨情生
說字立骨,理隨情生,一個“說”字,便奠定了《馬說》的全文脊骨,其中既是馬之悲鳴,亦是人之憤慨。在正常的邏輯思維下,一匹馬,要想成為世人所公認的千里馬,首先要滿足的第一個硬性條件就是自身要才美,即必須擁有日行千里的能力,然而這只是最為基礎的先天條件。其次,還需要人為因素,即一定要吃得飽,要擁有較為充沛的后天補給。在《馬說》一文中,作者運用隱喻,通過千里馬需要足夠的后天補給,映射當時的社會現實,便是統治者需要為人才提供施展能力的廣闊舞臺。一個“說”字,既是全文以喻說理的主線,也體現了古代文學的隱喻藝術。
在《馬說》中,韓愈首先以馬暗喻,從正面亮出了自己對于人才的觀點:“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緊接著在下一句中對該觀點進行反面議論——“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由此點出伯樂和千里馬之間的密切關系。在這兩句中,作者表面看似是在說千里馬的困境,實則以馬喻人,以千里馬借指人才。指出了封建社會下人才被埋沒的悲慘處境,以及作者對統治者摧殘人才的憤懣和控訴。在韓愈看來,千里馬的存在就像是一種主觀存在的事實,盡管它的才能擺在眼前,但如果缺少了伯樂的賞識,那么千里馬也就不復存在。在這里,他借用二者關系,既是在點明了人才與封建統治者之間的依賴關系,也是在隱喻之中表明當時人才的艱難處境。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這是千里馬能夠發揮才能的第二個必要條件——要吃得飽,只有吃飽之后才有可能跑出成績,才能得到大家賞識,最后成為世人口中的千里馬。這個邏輯順序在正常社會下是不可逆的,然而在《馬說》中,作者卻揭示了一個可笑又荒唐的社會邏輯——“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作為社會中選拔人才的官僚,卻不能發現千里馬的才能,不為千里馬提供充足的物質裝備,不為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廣闊舞臺,因此才造成了社會上“千里馬”的困境。“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現”,可這分明是由封建官僚識人不慎種下的因,后果卻要由千里馬被埋沒才能來承擔,一句“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更是深中肯綮地揭示了千里馬被埋沒的根本原因。作者以馬比人,通過對千里馬悲慘處境的描寫,折射出現實社會荒謬且顛倒的人才選拔邏輯。
在正常的社會邏輯下,千里馬先吃飽之后,才會跑出成績被大家認可,可在《馬說》中,現實就是如果你不能先被認可,不能先讓當權者賞識你,那么便會連吃的都不給你,更何況得到認可呢?如此周而復始,社會人才的選拔便陷入了一個極為昏聵的惡性循環——“用人無用,無人可用”,這便是韓愈藏在《馬說》中極為高超的隱喻藝術。以馬喻人,以人言馬,通過對千里馬識用過程的描寫,暗諷當下社會人才選拔的荒唐,這也正是《馬說》一文中最為深刻的地方。因此,在捋清這個邏輯順序之后,再順著這個顛倒邏輯去看韓愈,去看古代的文人,便能明白他們在面對權力的時候為何會如此卑微。
然而文章寫到這里,作者仍覺不夠。前文“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是韓愈從千里馬自身的角度出發,直言它所面臨的艱難處境,但這樣的描述是主觀的,只能令讀者看到自我角度下千里馬的悲哀,于是作者又用“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從飼養者的角度——伯樂,做了更深一層的闡釋與講解。但是在這里,作者并沒有立即譴責飼養者的不識,而是選擇讓他聽到千里馬的嘶叫,卻依舊拿著馬鞭走到它的跟前,發出“天下無馬”的悲嘆。從作者筆下飼養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人”在主觀動機方面還是不錯的,他并非不想選拔人才,并非沒有求賢用賢之心,奈何賢人賢才太“少”了。韓愈通過這樣看似平靜且客觀的敘述,卻直接將千里馬與伯樂的矛盾激至最大化,明明是“人”主觀上出了問題,可卻將這種局面的形成原因推脫成了客觀條件的不如意,眼前站的分明是一匹優秀的千里馬,飼馬者卻對著千里馬發出“天下無馬”的慨嘆,認為它連常馬也不如。作者在這里,以馬代人,既是在寫馬,也是在寫人,韓愈通過千里馬自喻,希望統治者能夠識別人才,欣賞人才,也希望自己能夠得到重用,使自己能像一匹真正的千里馬一樣,在適合自己的職位上盡情馳騁,盡情發揮自己的才干和能力,盡情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
二、喻不平之音
《馬說》寫于唐貞元十一年(795)至十六年(800)間,彼時韓愈剛及弱冠,初登仕途。他意氣風發地寫下《上宰相書》《三上宰相書》,來拜謁當時的宰相,請求擢用,然而得到的結果卻是“待命四十余日”,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再加上朝中奸佞當權,政治黑暗,才能之士不受重用,于是他郁憤之余,提筆寫下《馬說》一文來控訴當時黑暗的社會體制。在這里,千里馬象征人才,飼馬者暗指當時的統治者,借伯樂和千里馬的故事,將人才比作千里馬,將愚妄淺薄、不識人才的統治者比作飼馬者,指出有才之士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不幸的處境,寄托了作者的憤懣不平和窮困潦倒之感。同時,作者也對統治者埋沒人才、摧殘人才進行了諷刺、針砭和控訴,他希望統治者能夠識別人才、重用人才,使有才之士能夠充分發揮才能。
因此,通過《馬說》中的隱喻可以看出,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并非文人墨士沒有尊嚴,沒有骨氣,而是他們所面對的一切決定了他們要想干出一點事,就一定要對權力卑躬屈膝、搖尾乞憐,這是一種無奈,也是那時制度所帶來的惡。
三、言不平之氣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一文中曾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著名觀點,這句話的表面意思是說物體會因為放置不平產生振動而發出聲響,但與《馬說》相結合后,便有了新的釋義——即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會表達自己的思想和主張,成語“不平則鳴”便出于此處。
《馬說》的寫作初衷,歸根到底并非作者為馬申冤,而是以馬喻人,借此來表達自己內心的不平。因為此時的韓愈人微言輕,又不能直白言事、直吐怒氣,于是他只好將自己心中的不滿、壓抑等情感訴諸筆端,以文章的形式托物寓意,借千里馬與伯樂喻事諷人,抒發對自己懷才不遇的慨嘆和不平。“物不平則鳴”,韓愈寫《馬說》,就是為了將自己的懷才不遇、心中不平告訴世人,更重要的是告訴當時的統治階層,希望統治者能夠懂得識別、欣賞人才。
四、結語
《馬說》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篇經典佳作,其隱喻藝術手法的運用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在《馬說》一文中,作者通過對千里馬前途的描繪和思考,隱喻人才的難得與埋沒,表達了對社會不公以及現實的無奈。這種隱喻手法的運用,不僅深化了文章的主題思想,同時也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此外,《馬說》中的隱喻藝術手法也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啟示作用,例如劉禹錫的《陋室銘》和周敦頤的《愛蓮說》等。這些文章告訴我們:在寫作中巧妙地運用隱喻手法,可以使得文章更加含蓄而深遠、更加生動而感人;同時也可以引發讀者對隱喻問題的深入思考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