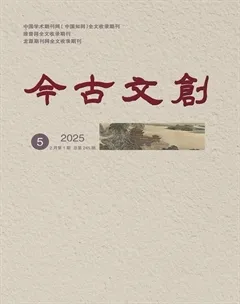論劉歆《遂初賦》中的天象書寫
【摘要】劉歆的《遂初賦》以天象比附人間場景,兼具雙關含義,既蘊含賦作家對神化天界的瞻仰與崇拜;也以委婉隱晦的筆觸勾勒人間朝堂的風云變幻。天上人間的意蘊交織,發揮其獨特的功能,以詭譎的天象隱射人間的政治現實,以波動的天象隱喻賦作家個體的坎坷命運,同時,在星象與物候的交相呼應中,呈現賦作家的情感變化。與充滿浪漫悲劇色彩的楚辭相比,《遂初賦》的天象書寫更加凝聚于漢代帝國統一秩序;與夸張藻飾的漢大賦相比,《遂初賦》的天象書寫更加熔鑄個人志向情感。究其原因,與豐富的時代特征和賦作家的創作意識有緊密聯系。
【關鍵詞】劉歆;《遂初賦》;星宿;隱喻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5)05-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05.004
劉歆的《遂初賦》是漢代述行賦的開端,其創作背景,據《漢書》所載,乃是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之時,因支持古文經學,由于當時的執政大臣和眾多儒生的不滿,恐招致禍端而遠征,隨后被任命為五原太守。在前往任職的途中經過三晉舊地,良多感慨,因而以賦作之。作者一連運用了多個天文星象來引領全篇,以天文星象意象書寫入辭賦,以廣闊的天象視角開拓了賦作的空間場景: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跖三臺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備列宿于鉤陳兮,擁大常之樞極。總六龍于駟房兮,奉華蓋于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①
《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②,其中便已論及天人關系,在《周易》中,有諸多對自然天象的描述與取象,如“天玄地黃”等表述。乾卦所象征的天,具有廣袤、高遠、運行不息等自然特性,它是日月星辰運行的空間,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的根源。這種自然之天的觀念反映了古人對宇宙自然的直觀觀察與初步認知,是構建天人關系的基礎層面。《九歌·東君》中游歷天外的場景也不乏浪漫天文意象的書寫:“青云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③這里將東君的服飾比作青云與白霓,富有浪漫色彩。同時,還提到了弧矢星、天狼星和北斗星等星辰,東君舉長矢射天狼,操弧星向西沉落,又以北斗星為勺酌酒,既展現了日神的英勇與豪邁,又巧妙地將天象與神話傳說相結合,使詩歌更具奇幻色彩和神秘氛圍。到了漢代,天文星象并不局限于客觀的星空視野,隨著天文知識探索的深入、漢家天下統一的帝國秩序,天文與政治的紐帶更加緊密,這一時期天官學說的研究也更趨向于嚴謹完整,辭賦中的星象描繪也附著了更多的政治寓意。
一、《遂初賦》中的星象表述
“紫宮”,即“紫微宮”,自《史記·天官書》至《甘石星經》皆有詳細記載,其中包含了一組星辰,周圍星官環繞,構成一組星象群落。紫宮中有帝星,因而也成為人間帝王居所的象征,漢代繼承了先秦時期的傳統,將紫宮作為帝王之居的代稱,將其周遭星宿與帝王宮室相聯系,宮殿建筑的布局以及命名,亦與紫宮有一定的聯系,用以體現帝王居中至尊的地位。
“閶闔”,即紫微垣東蕃和西蕃之間的天門,《離騷》中亦有此意象,屈原借以想象自己通往天庭的天門,超凡脫俗、溝通天際。閶闔作為天門,象征著人間宮殿大門,漢代仿照天門修筑宮城門,體現古代等級秩序的森嚴和禮制的嚴謹。劉歆在開篇寫出入天門無阻,實際寓意著自己可以自由出入宮門,是因為在朝為官。
“北辰”,即北極星,居于夜空中央,《論語·為政》將政德與北辰星聯系在一起,體現其猶如“眾星拱月”般的中心地位。《晉書·天文志上》:“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④體現北辰的至尊地位。“三臺”指的是三臺星,位于太微垣。根據《史記索隱》所述,三臺的主旨在于開啟德行,宣揚符號,目的是為了調和陰陽,理順萬物。又“三臺、三衡者,皆天帝之庭”,說明“三臺”亦代表三公,即朝堂。“太階”,也被稱為“泰階”。在《史記·天官書》中提到,魁下的六顆星,兩兩相對者,被稱為“三能”,因此,“太階”與“三能”“三臺”的意義是相同的。“太階”的變化關系到天下清明,太平與否。
“鉤陳”,即勾陳星,是紫微桓內的星名。有兩種解釋,一是引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⑤;二是引《樂汁圖》曰:“鉤陳,后宮也”⑥,即“勾陳”既主后宮妃子,又為天子護軍。“大常”在《全漢賦校注》中被解釋為“太一”,亦作“泰壹”,即北極神。“樞極”,即北極星和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星,用來比喻最高權勢。因而二者用以代指皇帝。
《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房為府,曰天駟。”故而“駟房”是以天駟星指代天子御馬。《晉書·天文志上》云:“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⑦因此“華蓋”是借星指帝王車駕頂蓋。天樞、天璇、天璣、天權合稱為“魁”,玉衡、開陽、搖光合稱為“杓”。“機衡”即北斗星中第三星“天璣”和第五星“玉衡”的合稱,“魁杓”合稱即指北斗。北斗被認為是天的樞紐,這里就指代政權的中樞機構權,即天子的政令。
《三輔黃圖·未央宮》云:“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⑧在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下,四象被賦予方位的含義,因此“玄武”即為四象中的北方之象,用以代指北方。
二、《遂初賦》天象書寫的文學功能
《漢書》記載劉歆年少通曉《詩》《書》且擅長著文章,其后為漢成帝詔黃門郎一職。河平年間,劉歆受詔與父親劉向共同負責統領校訂秘書一職,隨后又被任命為中壘校尉。漢哀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薦劉歆為侍中太中大夫,隨后又升遷為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地位尊貴且深受寵幸。結合劉歆本人的仕途經歷,可見開篇一系列的星象描寫別有隱喻。
《遂初賦》以天門閶闔開通比喻仕途之路的暢通無阻;劉歆與父領校秘書,屬大司空的屬官,故以三臺星自譽為登三公之位;以紫宮、北辰、太常比喻政治權力的中心,以彰顯自己曾經的仕途何其顯赫。至于“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為之難運”話鋒一轉,以異象暗示漢哀帝時外戚擅三公之權,君臣失和,劉歆遂無奈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此開篇看似是星宿意象的鋪陳,實際上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內涵,天上客觀的自然星象移植到人間,書寫權力中心的現實政治。
星象的描寫是以天上的樞紐比附人間的朝堂,蘊含著作者對神化世界的瞻仰與想象;除此之外,《遂初賦》中氣候景象的描寫則是作者以細膩、立體的筆觸集中描繪了較為真實的風云變幻,蘊蓄著作者對人間氣息的感知與觸動。天上人間的意象交織,天文星象與氣候景象融會貫通,體現了賦作家起伏波動的人生與情感。
其一,以詭譎的星象隱射人間的政治環境。劉歆《遂初賦》中就提到作者言賦的緣由是“政事已多失”,指出漢哀帝時期三公擅權,所以開篇看似描寫天文,實則是以天文樞紐對應漢代的中央政府,星辰分布運行的紊亂、無序或變化,暗示了政治上的失序,“機衡為之難運”一語雙關,既交代當時的天象變化,直指北斗星象運動異常,亦暗示漢哀帝時政治之機要為旁人所干涉。
其二,以波動的星象鋪墊個體的坎坷經歷。劉歆《遂初賦》開篇星象意象的內涵,在前文已詳述,北辰居于樞紐與至尊之極的地位,因而借指漢代的帝王,三臺、鉤陳的位置在北極星的周圍,接近北辰的位置,便暗喻賦作家個人曾經亦是在帝王身邊的重要輔臣,以樞極、駟房彰顯賦作家昔日顯赫無量的仕途高位。然而,一句“機衡之難運”,賦作家于登峰造極之地之后,轉而面對的卻是時運不濟的現實,“懼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濱”,看似寫天象之變化,但一“懼”字隱射出賦作家一語雙關的意思,中央樞紐機構權力受到近臣干預,預示著賦作家并非正常的官位變動,而是劉歆本人內心對朝堂現狀深感不安而遠征。
其三,氣候景象與天文星象相照應。劉歆歷經漫長的旅程,走過三秦舊地,到達五原境內,寒冬時節蒼茫寥廓的景象呼嘯而來。當劉歆步入臨沃之時,他有意駐足在這片荒無人跡之地,只見一望無際的荒原上,旋風寂寥隱約,沙塵蔽日,飄忽不定的旋風席卷萬物,泠泠作響的狂風侵襲著凍結凝滯的河川,哀風陰冷嚴寒,從清冷的山谷、凝結的厚霜呼嘯而過,飛鳥走獸在一陣陣蕭條冷瑟的狂風中倉皇失措,旗幟也在狂風中飄卷,一片清冷肅殺之景。可見,賦作家對這些景象有著強烈而敏銳的反應。
《文心雕龍·物色》:“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四時的天象和物候變化能夠引起文學家的性情感應,產生濃厚并具有相應特點的情感體驗。這些異常的景象與開篇的星象變化一樣,一方面使賦作家聯想到歷史現實與個人命運,暗發胸中感慨與理性思考,一方面也蘊含著賦作家個人深厚的情感與生命深意,真實地記錄下賦作家細膩而強烈的生命感知。無論是星象還是氣候的書寫,賦作家除了記錄客觀的自然景象,還將自身的生命體驗融入文學作品的想象之中,成就了自身獨特的風格。
三、《遂初賦》星象書寫的文化內涵
《遂初賦》乃劉歆記錄遠征途中所見所感之賦作,賦作家每及一處,不僅對歷史典故信手拈來,其所見之景亦如臨其境,感人泣下,賦作具有強烈的歷史厚重感與紀實性,但賦作家卻在開篇不吝筆墨地鋪排星宿,一系列意象恢宏遠大,其中亦蘊含豐富的時代特征與賦作家的創作意識。
其一,彰顯漢代豐富的星象知識體系與賦作家個人深厚的天文學識。
天文學自先秦以來已有悠久的歷史沉淀,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不少天象占卜,《左傳》《國語》也對星占多有記載,這就更加強調了天象與世間吉兇禍福的聯系。春秋戰國時期的日月、五星等研究也相當深入,二十八宿、二十八次等制度已較為完善,文學家甘德和石申的《天文星占》和《天文》中已有記載,石氏星表也為秦漢時期的天文發展提供重要的基礎。漢代不僅繼承鞏固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理論基礎,也將天文星占的研究推向了較為鼎盛的程度,使之變得更加細致全面。因此漢代涉及天文的著作也非常豐富,《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綜合參考先秦以來的文獻,對天象知識毛舉縷析,并對照人間秩序描摹出天上的模式,總結了當時的星官知識,成為研究漢代及以前天文知識的重要文獻。也由此可見,至于漢代,人們對星象的認知,已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星官系統。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后,《太初歷》的制定和《史記·天官書》的編纂,都體現當時的社會政治對天文學的重視。漢代的政治環境為天文學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天象的記載和觀察也是體察天意的重要途徑,漢代精通經術的博士儒生必然都有著淵博的天文學識。劉歆本人不僅具有豐厚的天文知識,也對漢代的天文發展頗有建樹。劉歆主持編訂《七略》,對西漢以前的學術考鏡源流,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其后他補充了日、月食周期和五星運行方面的內容,把“三統”說附會在《太初歷》上而編成《三統歷》,把《太初歷》改稱《三統歷》,成為我國保留至今的第一部完整的歷法。由此可見,劉歆作為漢代重要的天文歷法家,對星象有著系統而又高深的了解,在賦作的創作過程中,有充分的條件將天文意象融于其中,形成意蘊隱晦而又深遠的表達方式,體現賦作家自己獨到的天文學、文學修養。
其二,體現漢代時期的天文宇宙觀念以及對傳統哲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遂初賦》開篇天文意象的鋪排,并非簡單的羅列,其背后的創作思維與劉歆本人的宇宙觀念息息相關。劉歆繼承了先秦陰陽家的宇宙觀念,他認為太極運轉著三辰和五星于天,而元氣則調和著三統和五行于地。在人方面,皇極統一了三德和五事。因此,三辰與三統相結合,日與天統相合,月與地統相合,斗與人統相合。五星則與五行相互關聯,水與辰星對應,火與熒惑相連,金與太白相配,木與歲星相合,土與填星相連。三顆星辰以經緯相互交織。以五行為宇宙框架,配以天上五星,人間五物,“天施”“地化”“人事”“三統相通”,體現天、地、人有機統一的整體觀念,與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學說一脈相承。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使漢代賦作家得心應手地將天文要素融入創作中。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西京賦》、司馬相如的《大人賦》等作品,都將天子權威與天道秩序相比擬,劉歆的《遂初賦》亦如出一轍,“閶闔”“北辰”“紫宮”“大常”“華蓋”等意象都指向漢代宮廷,彰顯漢代王權至高無上的地位,體現漢代賦作家天人異質同構的“天人合一”觀念。劉歆在《遂初賦》中將天文星宿移植于人間朝堂,不僅以星宿照應中央權力,將天道與王權緊緊聯系在一起,也將星象變化與個人仕途經歷、追求相比擬,“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后”的急轉直下,使得《遂初賦》開篇的天文意象具有鮮明的隱喻作用,寥寥數字便使讀者聯想到賦作家的個人處境與志向,這一聯動反映了賦作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認為天象是天意的反映,能夠預示人間的吉兇禍福,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賦作家在作品中將星象與人事緊密結合,通過星象描寫來隱晦表達個體對自身命運以及朝堂局勢的感慨。將人間的皇權觀念與等級秩序投射在星官體系中,星宿意象的描寫轉化成為現實政治的真實寫照。
其三,星象意象運用的文學創作傳統及其內涵的拓展。
早在《詩經》中就已有不少星象意象運用于文學創作中,《小雅·大東》《小雅·巷伯》《召南·小星》等諸篇都有涉及,巧妙地將星象融入詩歌的意境之中,增強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其意象內涵又貼近現實,凸顯真摯的情感,意蘊悠長,也體現了先民在農耕生活中對自然現象的觀察、獨特的自然崇拜情感,對天文星象的無限遐想。屈原的《楚辭》更是將天文意象的運用發揮至浪漫的境界,《九歌·東君》《遠游》《離騷》以瑰麗的想象游歷奇幻天界,將星官體系納入辭賦創作過程中,與奇幻的想象相結合,營造出神秘莫測的意境,開創浪漫主義先河。可見,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有一定基礎的天官知識體系,已有將星象寓意融入文學創作的傳統,為后世賦作家的創作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思路,展現了賦作家淵博深厚的學識涵養與寬廣遼闊的天人哲思,開創了一種富有想象力的文學書寫模式。
先秦時期文學作品的星象意象運用,更多的是將創作視角凝聚于客觀的星空本身,體現一種自然崇拜與浪漫的想象,而到了漢代時期,帝國統一秩序與學術思想觀念的發展,也推動漢代的文學書寫場域更加聚焦于現實人間秩序,辭賦創作中的星象寓意也隨之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星宿不再僅僅是詩人想象中的游歷問道的外域,它被賦予了強大的政治內涵,更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象征——統一帝國的語境中的權力和話語。因而漢代賦作家常以星象象征政治權力和地位,劉歆在《遂初賦》中便是通過描繪與權力相關的星象來暗示朝廷中的地位和權力斗爭,并以星象的變化預示個人命運的起伏,表達對自身命運變化的擔憂。
注釋:
①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校注:《全漢賦校注》,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頁。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75頁。
③(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4頁。
④⑦(唐)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89頁。
⑤鄭文箋注:《揚雄文集箋注》,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4頁。
⑥(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40頁。
⑧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