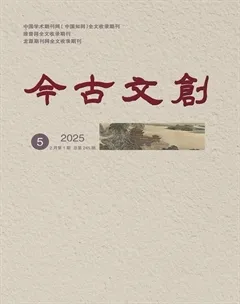“式”字所指代的上古漢語詞
【摘要】在上古傳世文獻中,“式”字的解釋向來或者含混或者牽強,各家注解莫衷一是。結合近代以來的上古出土文獻和出土文物研究中認為和“式”字具有文字關系、語源關系以及事物關系的文字、詞和事物,并從語言學本位的角度進行語音、語義和語法的研究,從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式”字的初文是“弋”字,可考的最早對應事物是繞線棒,在詞匯意義{法度}的基礎上語法化為半虛半實的副詞表示{應、當}的意義,繼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語法化為具有將來時語法范疇的副詞表示{將、會、要}的意義,進而又在將來時語法范疇方面發展出具有時間和程度漸進語法意義的副詞表示{越來越、愈加}的意義,在詞匯意義{式樣}的基礎上語法化為現代漢語湖北英山方言的部分單音節動詞和部分單音節動詞的重疊式的構詞后綴。
【關鍵詞】上古漢語;同族詞;“式”字;“弋”字;語義引申;語法化
【中圖分類號】H109"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5)05-0104-06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05.032
一、“式”字詞匯意義的溯源與梳理
(一)“式”字的初文是“弋”字
先秦傳世文獻中多次出現的“式”字的初文是“弋”字,而“式”字是以初文“弋”作為形旁兼聲旁,再加上表示意義范疇的形旁“工”,來構成一個形聲兼會意的分化字“式”,《說文解字》的“式”字條分析“式”字為“從工弋聲”是不準確的,應當改為“從工弋,弋亦聲”,但是《說文解字》提供了“式”與“弋”字語音在東漢許慎的時期相近甚至相同的語言事實。
從語音角度來看這兩個字所代表的詞的語音,也是符合漢語語音歷時客觀事實的。“弋”字在《廣韻》里屬以母職韻,而“式”字在《廣韻》里屬書母職韻,以母即中古韻圖里的喻母四等(假四等),書母即中古韻圖里的審母三等,而根據曾運乾先生的《喻母古讀考》中關于中古音上溯上古音的規律“喻四歸定”一條,可知中古以母(即喻母假四等)在上古時與定母發音部位相同皆屬舌頭音,又根據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第二章第四節第(四)點認為“在上古語音系統里,照系三等接近端透泥”,可知中古審母三等在上古時也是和定母相同發音部位的舌頭音,所以中古以母和書母在上古時期發音部位完全相同,發音方法不同。由此看來,從語音方面來說,上古的“弋”和“式”二字的語音,聲母極其相近,韻母和聲調完全相同,這是戴震先生提出的考求漢語同族字原則“音近義通”中“音近”的一面。
從文字角度來看,“式”字是“弋”字的后起字,這說明“弋”字已經可以表示“式”字的本義了,所以表示“式”字意義范疇的“工”字的本義和“弋”字的本義是屬種關系,因此“弋”是一種特化的工具,如此,考察“弋”字的本義就是在考察“式”字的本義。
(二)“弋”字的本義是{繞線棒}
考察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弋”字,其字形象一根豎直的立桿,中間有一個圓形、方形、倒三角形或紡錘形的物體,上端帶有一個分枝,在甲骨文絕大多數字形中這個分枝都是斜向下的,而在西周中期和西周晚期金文絕大多數字形中這個分枝要么水平要么斜向上,在這里以早期分枝斜向下的“弋”字字形來考察其所表征的造字時的本義。《甲骨文字編(下冊)》第1342頁編號為4258.30717(B6)的甲骨文“弋”字字形 右下方有表征右手的形旁“又”,所以“弋”字所象形的事物應當是一種可以手持的器具,又根據第1341頁編號為4252.04284(A7)、4252.06816(A8)兩個甲骨文“弋”字字形" 判斷這是一種可以繞線圈的器具。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字釋林》里的《釋弋、弟》一篇在闡述“弋”字與“弟”字關系時提到“弟”字甲骨文字形是“弋”字所象形的事物纏之以繩,林義光先生在《文源》中解釋“弟”字為“按古作" ,從弋," 束之,束杙亦有次第也”,并且在語音方面,“弟”在《廣韻》里就是定母字,與上文提到“弋”字上古音是定母相符合,二字上古音聲母完全相同,字形和語義兩個方面都具有文字孳生和詞族孳生的關系,所以“弋”字和“弟”字也是為兩個同族詞所造的兩個字。這其實就從解釋“弟”字本義是“束弋之次第”的角度側面證明了“弋”字所象形的事物就是一種用來繞線的工具。然后,結合廈門大學王君妍碩士《楚墓出土繞線棒研究》一文,發現“弋”字的本義應當是中端或者下端帶有紡錘并且上端帶有橫枝的繞線棒。《楚墓出土繞線棒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江西省多地曾出土過“工”字形的繞線工具,因此聯系“弋”字的后起分化字“式”字,“工”這個意符兼有形符和義符的雙重性質。這與前面判斷“形旁‘工’表示‘式’字這個形聲兼會意字的意義范疇”這個結論并不矛盾。
(三)“弋”字在上古漢語里表示過的實詞的詞匯意義
在語義這個方面,《楚墓出土繞線棒研究》一文中提到了繞線棒的三種用途,其中用于春秋戰國時期“弋射”活動的用途,正好也解釋了“弋”字所代表的詞的詞匯意義從{繞線棒}引申到{弋射}的發展過程。“弋”表示{弋射}的例子有:“弋,繳射也(《玉篇》)”“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詩經·鄭風·女曰雞鳴》)”“公弋取彼在穴(《易經·小過卦》)”“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莊子·胠篋》)”“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呂氏春秋·功名》)”。“弋”字由{弋射}引申出{繳矢}的引申義,例子有:“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楚辭·九章·惜誦》)”。
“弋”字所表示的詞由{弋射}引申出{可弋射之鳥}的引申義,這個詞匯意義后來寫作分化字“鳶”,從語音角度來講,“鳶”在《廣韻》里是以母仙韻,古人把入聲韻尾歸在陰聲韻尾中,所以“鳶”和“弋”也是陰陽對轉的關系。例子有:“十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后言弋者,何也?鳴而后知其弋也(《大戴禮記·夏小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詩經·大雅·旱麓》)”“鳶鳥丑,其飛也翔(《爾雅·釋名》)”“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禮記·曲禮》)”。
因為“弋”字所表征的繞線棒這種工具是用來治線和理線的,它就使得亂線有了規律,所以引申出了{治理絲線}這個詞匯意義,比如《甲骨文合集》編號4775序號1的拓片的內容:“庚寅卜,爭鼎:叀?弋絺。八月”,“弋”字在此處所代表的詞用的就是{治理絲線}這個引申義。由{治理絲線}這個表示具體動作的詞匯意義就很自然的引申到了{法式}{規律}{節度}{制度}{典范}{楷模}和{式樣}等抽象名詞意義,以及{以之為法度}{使之有規律}{制定節度}{樹為法度}{制定法度于}{以其為榜樣}和{效法}等抽象的動詞意義。比如在出土文獻方面,《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合集補編》中有關“弋”字的文段中常出現“A令B弋C”和“A乎B弋C”的句式,其中A、B和C均為人名、官職名和族姓,A和B可以省略,C一定會出現且C有時是廟號和謚號,這其實就是一個上古漢語的兼語短語(甲骨文時代已經出現使令式的兼語短語結構,參看張穎煒的《漢語遞系結構發展演變史》、劉鑫鑫的《上古漢語中的兼語句》以及林琳的《上古使令類兼語動詞的演進和發展》三篇論文),“弋”字所代表的詞在這里詞性是動詞,用了{效法、以其為榜樣}的詞匯意義。
另外,西周中期青銅器《" 鐘》中的“弋皇且考高,對爾剌,嚴才上”中的“弋”用的也是{樹為法度、效法}這個引申義。這些先秦出土文獻中“弋”字所表示的實詞,和下文先秦傳世文獻中“式”字所表示的實詞,語義相同或者相通,這又是戴震先生提出的考求漢語同族字原則“音近義通”中“義通”的一面。據此,便可以判斷上古漢語中“弋”字所代表的詞和“式”字所代表的詞是屬于同一個詞族的同族詞,這個詞族的諸多孳生詞用字除了有“弋”字和“式”字以及上文提到的“弟”字和“鳶”字之外,還有下文即將提到的“代”字、“貣”字、“貸”字和“忒”字,該詞族最初的母詞所用的初文是“弋”字。
(四)“式”字在上古漢語里表示過的實詞的詞匯意義
先秦傳世文獻有這些例子:“式”字為名詞詞性,訓為{自然規律、法度、制度、法式、典范、節制}的:“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詩經·大雅·下武》)”。“式”作句子謂語,詞性為及物動詞,訓為{樹為法度、效法},也可以理解為“式”訓為{法度}在此處名詞活用為意動用法{以之為法度}的:“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詩經·大雅·思齊》)”。“式”句子謂語,詞性為及物動詞,訓為“制定法度于”,也可以理解為“式”訓為“法度”在此處名詞活動為使動用法“使其有法度”的:“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詩經·大雅·崧高》)”“命仲山甫,式是百辟(《詩經·大雅·烝民》)”。
在《詩經》和《尚書》的歷代注解中絕大多數注解家都注解為“式,法也”和“式,用也”,究其源頭,是《毛詩詁訓傳》中毛亨所開的端倪,而馬敘倫先生在《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九提到:“倫按法也非本義,或非本訓。用也者,試字義,校者加之”。馬敘倫先生的看法是正確的,《詩經》和《尚書》中的所有“式”字,發現“式,法也”不能概括大多數的實詞“式”字的詞匯意義,“式,用也”甚至不能去解釋得通所有的副詞和虛詞“式”字,{任用、用}其實是“式”字的一個引申義,后來分化為“試”字,《說文解字》“試”字下釋義“用也”即是此詞匯意義。比如:“今予將試以女遷(《尚書·盤庚》)”“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詩經·小雅·采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詩經·小雅·大東》)”“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易經·無妄》)”“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禮記·樂記》)”“吾不試,故藝(《論語·子罕》)”“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戰國策·秦策》)”。
這些例子中的“試”都是{用、任用}的詞匯意義。后來“試”由于經常放在動詞“嘗”的后面一起使用,逐漸從實詞短語語法化凝固為了雙音節動詞,“嘗試”中的“試”的詞匯意義逐漸消失,“嘗試”在后來就逐漸就只剩下先秦“嘗”的引申義{嘗試、試探},甚至最后連單獨的“試”也可以被“詞義感染”(“詞義感染”的定義見伍鐵平先生《詞義的感染》一文)而表示先秦“嘗”字的引申義{嘗試、試探}了,這樣一來“試”變成了先秦“嘗”的引申義{嘗試、試探}的同義詞了,所以《廣雅》中“試”字的釋義已經變成了“試,嘗也”。比如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里的“試”還有{任用}這個詞匯意義,但到了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試用于今日,先帝稱之曰能”中的“試”顯然就是先秦“嘗”的引申義{嘗試、試探}了,這種變化后的詞匯意義一直延續并成了現代漢語里“試”和“嘗試”的基本義。
“式”字由{式樣}這個詞匯意義引申出{清理使之成為應有的樣子}的詞匯意義,這個詞匯意義被寫作分化字“拭”字或其異體字“巾式”字,《爾雅·釋詁》中“拭,清也”即是此詞匯意義,《禮記·雜記》中的“雍人拭羊”和《儀禮·聘禮》中的“賈人北面坐拭圭”,也應當作此訓。
由于系物的木樁形似“弋”字的本義所表征的繞線棒,所以“弋”字后來引申表示{系物的木樁}{把東西系在木樁上}這些意思,后來分化為“杙”字,《說文解字》中的“弋”字條“橛也,象折木衺銳著形。從" ,象物掛之也”解釋的就是這個詞匯意義。比如《尚書大傳》卷四里有“椓杙(一本作弋)者有數”,鄭玄注:“杙者,系牲者也”,《左氏春秋傳·襄公十七年》里有“以杙抉其傷而死”,再如王安石詩《后元豐行》里有“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杙小舟”用的即是{把東西系在木樁上}這個引申義。又由于“杙”表示的{系物的木樁}引申出{可憑依之物}這樣的意思,比如所以{車前橫木}這種可憑依之物在后來或者用“式”字或者專門用分化字“軾”來表示,比如《說文解字》里“軾”字釋義為“車前也”、《左氏春秋傳·莊公十年》里的“登軾而望之”、《禮記·仲尼燕居》里的“車得其式”和“車失其式”。由于周朝貴族在車上憑依于車前橫木來互相行禮致敬,所以“式”和“軾”字又引申出了{憑依著車前木來表示行禮致敬}這個引申義,因此《釋名》中有“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比如:“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尚書·周書·武成》)”“兇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論語·鄉黨》)”“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淮南子·修務》)”。之后也引申出了{憑依他物}的引申義,這里并沒有{禮敬}的意思,比如《戰國策·楚策》里的“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駎而后能立,式而后能起”。
陳夢家先生在《老子分釋·十八》中認為“為天下式”的“式”是上古天官用來“定日月,分度衡,視吉兇”(《史記·龜策傳》里有“運式定日月,分度衡,視吉兇”)的一種可旋轉的上圓下方的天文工具,類似于后來的渾天儀。這種天文工具因為形式與繞線棒相似,所以被發明之后定名為“式”,可以算作是“弋”和“式”二字的一個引申義。另一方面,陳夢家先生之所以認為《禮記·仲尼燕居》里的“車得其式”和“車失其式”的“式”與“載”同音同義,均為{天文工具},是根據鄭玄注里的“式謂載也”得來的,但是《廣韻》中“載”是精母海韻、精母代韻和從母代韻三讀,在上古時期,不論精母還是從母都與“式”的審母三等相去甚遠,依據見王力先生《漢語史稿》第二章第四節第(四)點,所以,陳夢家先生認為《詩經》中的虛詞“式”和“載”是同一個詞的觀點(《詩經》中真正與虛詞“式”字是同一個詞的是虛詞“職”字,下文將要討論),以及“載、戴”這一組字與“弋、式、代、忒、貣(貸)”這一組字(下文將要討論)在上古時期同音的觀點,本文不予采納。
(五)“弋”字和“式”字所代表的詞的其他同族詞及其用字
西周中期周穆王時期的農卣銘文中有“母卑農弋,事氒友聘農”一句,張程昊先生在《農卣銘文考釋》一文中認為“弋”即后來的分化字“貣”,是{乞物于他人}之義,這個字后來又被寫作“貸”。《說文解字》里有“貣,從人求物也,從貝弋聲”,《荀子·儒效》里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用的也是此義。{乞物予他人}這個詞匯意義是從{弋射}引申而來的,以弋射索取鳶鳥發展出了弋求物品于他人的意思,是一個詞義擴大的過程。
《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中的“貣”字字形有的形旁“貝”字字形尖端向下開口向上,形似“心”字甲骨文字形,而甲骨文和金文中找不到“忒”字,所以后來的“忒”字是“貣”字的形訛,“忒”字后來又有被寫作從心代聲的字形的。《說文解字》中“忒”字條解釋為“更也”,和段玉裁注中解釋為“不相值”“差也”“更改”和“失常也”也都是“貣”字的詞匯意義{乞物于他人}的引申義,由{乞物于他人}到{不相值}再到{失常},因為{失常}所以又有了{更改、更替}的引申義,比如上文提到的《老子》中的“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這句,“忒”與“式”對文反義,與“常”也構成反義,用的正是{失常、更改、更替}之義。《說文解字》“忒”字條段玉裁注最后提到“忒之叚借或作貣”,為上面判斷“忒”字是“貣”字的形訛提供了側面證據,其實“貣”才是所謂的正體字,段玉裁當時沒有看見甲骨文材料,只依據傳世文獻材料,所以判斷結論出了偏差。另外,“代”字在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中也是找不到的,地名的“代”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寫作從邑弋聲的字,判斷后來的“代”字是“貸”字或者從心代聲的字的省寫,《說文解字》中“代”字條釋義“更也,從人弋聲”,《左氏春秋傳·莊公八年》里的“及瓜而代”,《莊子·逍遙游》里的“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史記·項羽本紀》里的“彼可取而代也”,張衡《東京賦》里的“四時迭代”,王充《論衡》里的“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用的都是{更替}這個詞匯意義。
從語音角度來說,在《廣韻》里,“貣”字屬定母德韻和透母德韻兩讀,“忒”字屬透母德韻,“代”字屬定母代韻,而“貸”字屬透母代韻。透母和定母發音部位相同,區別僅在于發音方法不同(透母是次清聲母不帶音送氣,定母是全濁聲母不送氣帶音),兩個聲母極其接近。“弋”和“式”字所屬的職韻,與“忒”和“貣”字所屬的德韻,同屬曾攝,同屬開口呼,僅是介音和韻等不同(職韻是三等韻,德韻是一等韻),兩韻部是極其接近的。
二、“式”字語法意義的發展和變化
(一)傳世文獻中作勸令副詞用的“式”字
下面來看先秦傳世文獻和先秦出土文獻中作副詞用的“式”字的例子。這些作副詞用的“式”字在歷代注解中要么被籠統地稱為“發語”,要么簡單地訓為{用}(上文已經提到{用}是“式”字所代表的詞的一個引申義,字形后分化為“試”字),要么被誤訓為其他的實詞。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在這個問題上也只是簡單地訓為“用”和“以”,本質上是將其當作虛詞來處理的。首位將“式”字作副詞討論的學者是丁聲樹先生的《詩經“式”字說》一文。
“式”字為表示對未來情況的勸令副詞,訓為{應、當、要}:“嘉賓式燕以敖(《詩經·小雅·鹿鳴》)”“嘉賓式燕以樂(《詩經·小雅·南有嘉魚》)”“式燕且譽(《詩經·小雅·車舝》)”“式燕且喜(《詩經·小雅·車舝》)”。朱熹《詩集傳》對此的解釋是:“雖無他人,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也”。丁聲樹先生當時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啟發。值得注意的是丁聲樹先生提到的“職”與“式”音近假借的一例:“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詩經·唐風·蟋蟀》)”,顯然這里的“職”也應是勸令副詞“應、當”。從語音角度來看,“職”字在《廣韻》中屬章母職韻,與“弋”“式”二字韻母聲調完全相同,且章母即照母三等,與上文討論的“式”字的書母即審母三等一樣,根據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第二章第四節第(四)點認為“在上古語音系統里,照系三等接近端透泥”,章母和“弋”字在上古時期的定母發音部位完全相同,發音方法不同。所以“弋”“式”與“職”的上古語音是極其接近的。
(二)“式”字所表示的虛詞的語法化過程
“式”字的實詞引申義{法式、法度、規律}是可以引申出{應、當、要}這種勸令副詞意義的,又因為勸令副詞包含有將來時的含義,很自然地就會引申出表示將來時的副詞意義,當“式”字進入表示時態的語法范疇之后,就會很自然地被用在過去和現在所敘述的預測情況中,進而“式”字在表示時態的語法范疇里逐步取得了過去時和現在時。另外,由表示將來時,逐漸引申出表示時間漸進甚至引申出表示程度漸進的副詞用法。裘錫圭先生在《卜辭“異”字和詩、書里的“式”字》第三部分第9、10、12、14段中談到了這個問題,即《詩經》和《尚書》里“式”字作副詞,由表示意愿,引申出表示對未來情況的勸令、表示未來可能的用法,也可以引申出對過去已發生情況的某些用法,情況類似于現代漢語的助動詞“要”和副詞和連詞“就”的語法功能和語法意義。
虛詞“式”字表示將來時的副詞語法意義,相當于現代漢語“將、會、要”的例子:“式飲庶幾(《詩經·小雅·車舝》)”“庶曰式臧(《詩經·小雅·雨無正》)”“式穀似之(《詩經·小雅·小宛》)”。
虛詞“式”字語法意義為過去式和現在時,表示在過去和現在所敘述的預測情況中的例子:“式禮莫愆(《詩經·小雅·楚茨》)”“式固爾猶(《詩經·魯頌·泮水》)”“帝式是惡、帝式是增(《墨子》引《逸尚書·仲虺之告》)”。
這些句子里的“式”字是表示遞進關系的連詞“就”,這種相當于連詞“就”的用法引申自“式”表示副詞“就”的用法,而相當于副詞“就”的用法引申自“式”表示副詞“將、會、要”的用法,區別在于副詞“將、會、要”表示將來時的語法范疇,而副詞和連詞“就”可以表示過去、現在、將來三種時的語法范疇。“式”字在這些句子中表示現在時或過去時,沒有將來時的語法意義。
虛詞“式”字表示時間和程度漸進的語法意義的副詞,訓為“愈加、越來越”的例子:“式月斯生(《詩經·小雅·節南山》)”“式微式微(《詩經·邶風·式微》)”“上帝耆之(《詩經·大雅·皇矣》)”。
虛詞“式”字所代表的勸令副詞的語法意義、三種時的語法范疇意義和時間漸進以及程度漸進副詞的語法意義,是先秦漢語已經出現“語法化”端倪的有力例證。根據裘錫圭先生的觀點,進一步判斷這種勸令副詞在甲骨文時代已初現端倪,除了用“弋”字來書寫之外,還常用“異”“翼”字來書寫,如裘錫圭先生認為可靠的《逸周書》兩例“翼”字。在西周中期和西周晚期的金文中用“弋”字來書寫這個副詞的例子,如裘錫圭先生提到的曶鼎(西周中期周恭王時)和召伯虎簋(今改稱琱生簋,西周末期周宣王時)銘文的例子,還有冬方鼎(西周中期)和史墻盤(西周中期)銘文。
從語音角度來看,在《廣韻》中,“弋”和“翼”完全同音都是以母職韻,“弋”和“異”僅聲調不同,并且《廣韻》認為從羽弋聲的[羽弋]字是“翼”字的古字,所以“異”曾經作過“弋”的假借字。裘錫圭先生在《卜辭“異”字和詩、書里的“式”字》中也認為“式~弋”和“異~翼”是寫法不同的同一個詞,與根據語音聯系和《廣韻》古字材料的判斷是相吻合的。
程少峰先生在《〈詩經〉“襯字”說略》中認為“襯字”即馬建忠《馬氏文通》中引進的“詞頭、詞尾”概念,認為《詩經》中的襯字是有音無義,協調音節的修辭現象。并提出了襯字的五條判別原則。《詩經》中的副詞“式”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條件的。但是對于“無義”這一點不置可否,因為漢語副詞本就是介于實詞與虛詞之間的一種詞類,副詞“式”字是帶有微弱的語義意義(詞匯意義)的。僅看《詩經》中的副詞“式”字絕大多數都出現在謂詞之前(“式月斯生”一例是個例外),就會把副詞“式”字當作形容詞詞頭和動詞詞頭,它的出現的位置和“薄”“載”“曰”“不”這一類經常出現在四字句第一字位置或者占四字句第一字和第三字位置的詞頭大致相似,這一點其實也是陳夢家先生在《老子分釋·十八》中誤解虛詞“式”字和詞頭“載”字是同一個詞的另一個原因。
聯系到曶鼎(西周中期周恭王時)、五年召伯虎簋(西周末期周宣王時)、冬方鼎(西周中期)和史墻盤(西周中期)銘文中的“弋”字,西周晚期虛詞“式”字確實是存在于當時的書面語中的。成書于春秋晚期的《詩》中《國風》部分僅僅在《邶風·式微》出現虛詞“式”字,其他的“式”字都出現在《雅》和《頌》的部分。“式微”是用當時的民歌反映了當時東周口頭語里虛詞“式”字已經語法化到了這個階段了,并且從“式”字語法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式微”的“式”表示程度漸進的語法意義也應當是上古時期很晚的階段才出現的,與《邶風·式微》這種當時民歌的口頭語反映也是大致相吻合的。《雅》和《頌》保留“式”字既有西周及之前的口頭語的共時反映,又有沿襲了宗廟禮器銘文和《尚書》中的書面語的歷時結果,因為不同的詩篇創作時間不一,用“式”字的原因也就不盡相同。戰國時期的作品《老子》中出現“式”字全部表示實詞,只是知識分子階級在書面語和天文、占卜和交通行業專用的一般詞匯中保留較早的文字用法的結果。戰國時期的作品《墨子》也出現了“式”字,是引《尚書》逸文的結果,所以在《墨子》里不是引文的部分并未出現表示虛詞的“式”字,這也是在《墨子》成書的戰國時期“式”字所表示的虛詞已經在口頭語中消失的一個證據。程少峰先生認為這些“襯字”的存在起到了湊足音節、湊足四字句式的詩歌語言表達效果,語言是先于文學格式的,即語言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存在沒有這種語法組合規則的文學格式,所以文學格式并不是產生作副詞用的“式”字這種用法的原因,而是在語言中“式”字所表示的這個副詞先有這種語法組合規則,然后才有這種文學格式。但是程少峰先生提出的這一點卻恰好解釋了《詩經》之后的書面語中表示副詞的“式”字突然絕跡的現象,即在書面語中隨文學體裁而消失的現象,呂玉仙先生在《虛詞“式”在〈詩經〉中的含義探析》一文中也提到了這一點。但是口頭語中虛詞“式”字仍在使用并在繼續進行著語法化,并最終變成了現代漢語湖北英山方言中的構詞后綴“式”字(見陳淑梅女士的《湖北英山方言“式”字的用法》一文)。
參考文獻:
[1]毛亨.宋本毛詩詁訓傳[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2]孔穎達.宋本尚書正義[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3]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和尚書正義(清嘉慶刊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和尚書正義(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M].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5]陳彭年.宋本廣韻(永祿本)[M].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08.
[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經韻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朱熹.詩集傳(宋刊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7.
[8]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9.
[9]丁聲樹.丁聲樹文集上卷·詩經“式”字說[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10]裘錫圭.古文字論集·釋柲·釋弋[M].北京:中華書局,1992.
[11]陳夢家.陳夢家學術論文集·老子分釋·十八[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2]李宗焜.甲骨文字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5.
[14]金祥恒.續甲骨文編[M].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社,1982.
[15]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華書局, 1999.
[16]郭沫若,胡厚宣.甲骨文合集補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9.
[17]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M].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7.
[18]劉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19]容庚.金文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0]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21]裘錫圭.卜辭“異”字和詩、書里的“式”字[J].中國語言學報,1982,(1):173-188.
[22]方有國.《詩經》虛詞“式”辨釋[J].語言研究, 2003,23(03).
[23]程少峰.《詩經》“襯字”說略[J].紅河學院學報, 2012,10(06).
[24]陳淑梅.湖北英山方言“式”字的用法[J].方言, 1996,(1):64-67.
[25]呂玉仙.虛詞“式”在《詩經》中的含義探析[J].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20(01).
[26]伍鐵平.詞義的感染[J].語言研究,1984,(3): 57-58.
[27]張程昊.農卣銘文考釋[J].考古,2018,(12).
[28]王君妍.楚墓出土繞線棒研究[D].廈門大學, 2018.
[29]張穎煒.漢語遞系結構發展演變史[D].蘇州大學,2017.
[30]劉鑫鑫.上古漢語中的兼語句[D].西南大學, 2008.
[31]林琳.上古使令類兼語動詞的演進和發展[D].暨南大學,2010.
作者簡介:
胡帥,男,海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漢語方言學、江淮官話、語音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