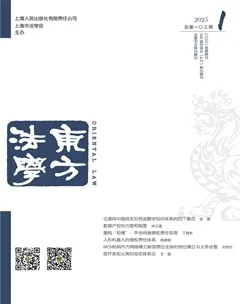重構(gòu)“知情”: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反思
關(guān)鍵詞:平臺(tái)責(zé)任 注意義務(wù) 通知?jiǎng)h除 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 算法推薦 知情狀態(tài)
一、問(wèn)題的提出
在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制度中,平臺(tái)的知情狀態(tài)被視為關(guān)鍵因素。一方面,傳統(tǒng)的共同侵權(quán)制度都將知情狀態(tài)作為判斷平臺(tái)是否存在間接侵權(quán)的標(biāo)準(zhǔn)。以我國(guó)相關(guān)制度為例,《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第22條、《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第44條、《電子商務(wù)法》第38條、《民法典》第1197條、《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司法解釋》)第7、9條,《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利用信息網(wǎng)絡(luò)侵害人身權(quán)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網(wǎng)絡(luò)人身權(quán)益司法解釋》)第6條都以“知道”“明知”“應(yīng)當(dāng)知道”等作為判斷平臺(tái)責(zé)任的依據(jù)。另一方面,以“通知-刪除”規(guī)則為代表的避風(fēng)港制度也與平臺(tái)的知情狀態(tài)密切相聯(lián)。“通知-刪除”規(guī)則規(guī)定,平臺(tái)只有在接到被侵權(quán)人的通知后,才有履行刪除侵權(quán)內(nèi)容的義務(wù)。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制度可以被解釋為“知情-刪除”規(guī)則,即平臺(tái)對(duì)于平臺(tái)內(nèi)的一般間接侵權(quán)并不知情,只有平臺(tái)在被告知和處于知情的狀態(tài)下,平臺(tái)才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
不過(guò),以知情狀態(tài)分析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卻存在種種困境。其一,間接侵權(quán)與避風(fēng)港制度雖然都涉及知情,但前者以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中的角色判斷與責(zé)任分擔(dān)為基礎(chǔ),后者則以合規(guī)免責(zé)為基礎(chǔ),兩者存在緊張甚至沖突。其二,何謂知情具有很大彈性。法律對(duì)于知情狀態(tài)的要求各不相同,既包括事實(shí)上的“知道”,也包括規(guī)范意義上的“明知”或“應(yīng)知”等要求。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知情的判斷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在算法推薦等技術(shù)等背景下,平臺(tái)是否對(duì)第三方侵權(quán)知情再次引發(fā)爭(zhēng)議。其三,通過(guò)知情狀態(tài)判斷平臺(tái)責(zé)任,也可能帶來(lái)平臺(tái)作為與平臺(tái)審查的悖論。平臺(tái)可能故意無(wú)視,以避免相關(guān)責(zé)任,從而導(dǎo)致“不做不錯(cuò)”的悖論。平臺(tái)也可能因?yàn)榉e極履責(zé)而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侵權(quán)行為知情,從而承擔(dān)責(zé)任,導(dǎo)致“做多錯(cuò)多”的悖論。
本文對(duì)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的知情困境進(jìn)行分析與反思,指出困境的根源在于典型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與傳統(tǒng)的個(gè)案性侵權(quán)、非治理型的共同侵權(quán)存在根本性不同。在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中,其典型形態(tài)是特定個(gè)案的侵權(quán),在這類侵權(quán)中,共同侵權(quán)人的知情狀態(tài)可以作為判斷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與責(zé)任的依據(jù)。但典型的平臺(tái)侵權(quán)具有大規(guī)模治理特征,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是整體性和概率性的,而非僅僅是個(gè)案性的。從典型平臺(tái)侵權(quán)的大規(guī)模治理特征出發(fā),本文對(duì)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進(jìn)行重構(gòu)。
二、問(wèn)題的分析與展開(kāi)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以知情狀態(tài)分析與判斷平臺(tái)責(zé)任,可能存在種種困境。本部分首先對(duì)本文引言所提到的若干困境進(jìn)行系統(tǒng)化分析與展開(kāi)。
(一)兩種制度中的知情
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的知情問(wèn)題首先涉及兩種制度。一方面,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可以適用幫助侵權(quán)、教唆侵權(quán)、替代責(zé)任等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法制度。例如我國(guó)《民法典》在第1168條規(guī)定了一般共同侵權(quán)責(zé)任。第1169條第1款規(guī)定了教唆、幫助侵權(quán)責(zé)任,第2款規(guī)定了替代責(zé)任,第1171和1172條規(guī)定了可分割的共同侵權(quán)責(zé)任。此外,《民法典》在第1197條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網(wǎng)絡(luò)用戶利用其網(wǎng)絡(luò)服務(wù)侵害他人民事權(quán)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wǎng)絡(luò)用戶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這一條款也可以被視為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制度在網(wǎng)絡(luò)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這一條款雖然被置于《民法典》互聯(lián)網(wǎng)專條部分,但與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制度并無(wú)不同。另一方面,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也適用以“通知-刪除”規(guī)則為代表的避風(fēng)港規(guī)則。例如我國(guó)《民法典》在第1195和1196條引入了以美國(guó)數(shù)字千禧年版權(quán)法案為基礎(chǔ)的通知-刪除規(guī)則,要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在收到權(quán)利人的侵權(quán)通知后及時(shí)“采取必要措施”。
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與避風(fēng)港制度雖然都將知情狀態(tài)視為是否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但二者對(duì)于知情狀態(tài)的理解并不相同。一方面,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以過(guò)錯(cuò)或過(guò)失來(lái)理解平臺(tái)的知情狀態(tài),其對(duì)平臺(tái)所施加的責(zé)任相對(duì)較重。當(dāng)平臺(tái)“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平臺(tái)內(nèi)存在侵權(quán)時(shí),都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共同侵權(quán)責(zé)任。另一方面,避風(fēng)港規(guī)則以合規(guī)免責(zé)的立場(chǎng)理解平臺(tái)的知情狀態(tài),其對(duì)平臺(tái)所施加的責(zé)任相對(duì)較輕。以我國(guó)為例,只要平臺(tái)履行《民法典》第1195、1196條所規(guī)定的義務(wù),就不應(yīng)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美國(guó)數(shù)字千禧年版權(quán)法案》的規(guī)定則更為具體,如果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并不實(shí)際知道”侵權(quán)行為,或者“不知道存在明顯侵權(quán)活動(dòng)的事實(shí)或情況”,那么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就不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這兩種知情狀態(tài)常常被總結(jié)為“實(shí)際知情”與“紅旗知情”。此外,《美國(guó)數(shù)字千禧年版權(quán)法案》還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不必承擔(dān)對(duì)侵權(quán)行為的一般審查義務(wù)。
在法律實(shí)踐中,法院對(duì)知情的理解與判斷常常在兩種制度間搖擺,經(jīng)常出現(xiàn)不一致的理解。以我國(guó)司法為例,法院一方面以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來(lái)理解知情狀態(tài),要求平臺(tái)承擔(dān)合理注意義務(wù)。例如,韓某訴北京某度網(wǎng)訊科技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認(rèn)為某度公司應(yīng)有合理的理由知道相關(guān)文檔侵權(quán);某果公司訴北京某鐵數(shù)盟信息技術(shù)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認(rèn)為某果公司應(yīng)當(dāng)能夠知道相關(guān)侵權(quán)行為。另一方面,法院在其他案件中也利用避風(fēng)港規(guī)則來(lái)理解平臺(tái)的知情狀態(tài)。例如,某健(中國(guó))日用品有限公司訴浙江某寶網(wǎng)絡(luò)有限公司侵犯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糾紛案中,法院認(rèn)為,對(duì)于平臺(tái)內(nèi)的疑似商標(biāo)侵權(quán),對(duì)平臺(tái)提出過(guò)高的審查義務(wù)與注意義務(wù),會(huì)導(dǎo)致對(duì)“避風(fēng)港規(guī)則的否定”。相對(duì)而言,美國(guó)對(duì)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與侵權(quán)責(zé)任采取相對(duì)寬松的立場(chǎng),但也面臨兩種制度的緊張。一方面,美國(guó)法院不斷解釋與適用《數(shù)字千禧年版權(quán)法案》中的“實(shí)際知情”與“紅旗規(guī)則知情”標(biāo)準(zhǔn),將其解釋為需要對(duì)某一特定侵權(quán)具體知情。另一方面,美國(guó)法院也不斷適用普通法間接侵權(quán)上的知情標(biāo)準(zhǔn)。例如,維亞康姆公司訴油管一案中,法院指出,普通法上的“故意無(wú)視”原則并未被避風(fēng)港規(guī)則所取代。MGM工作室公司訴格羅克斯特案等一系列案件中,法院引入了普通法上的教唆侵權(quán)的教義,對(duì)平臺(tái)施加了一定的“應(yīng)知”責(zé)任。
(二)知情的不確定性
知情狀態(tài)面臨的另一問(wèn)題是其判斷標(biāo)準(zhǔn)高度不確定。這不僅是因?yàn)樯衔奶岬降膬煞N制度對(duì)于知情狀態(tài)的理解不同;還因?yàn)榧词乖趦煞N制度內(nèi)部,法律對(duì)知情的規(guī)定、理解與判斷也存在巨大彈性。
以我國(guó)為例,2006年公布并于2013年修訂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規(guī)定,如果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不知道也沒(méi)有合理的理由應(yīng)當(dāng)知道”,則其可以免責(zé);而處于“明知或者應(yīng)知”的狀態(tài)下則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2009年制定的侵權(quán)責(zé)任法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處于“知道”的狀態(tài)下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2013年制定的《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交易平臺(tái)提供者“明知或者應(yīng)知”銷售者或者服務(wù)者利用其平臺(tái)侵害消費(fèi)者合法權(quán)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與該銷售者或者服務(wù)者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2018年制定的《電子商務(wù)法》規(guī)定,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經(jīng)營(yíng)者“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平臺(tái)內(nèi)經(jīng)營(yíng)者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務(wù)不符合保障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費(fèi)者合法權(quán)益行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與該平臺(tái)內(nèi)經(jīng)營(yíng)者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2020年制定的《民法典》采取與《電子商務(wù)法》類似表述,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網(wǎng)絡(luò)用戶利用其網(wǎng)絡(luò)服務(wù)侵害他人民事權(quán)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wǎng)絡(luò)用戶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此外,《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司法解釋》和《網(wǎng)絡(luò)人身權(quán)益司法解釋》則更明確地規(guī)定,認(rèn)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是否屬于“應(yīng)知”或“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應(yīng)當(dāng)考慮多重因素。
在法律解釋上,我國(guó)對(duì)于知情狀態(tài)的理解與適用也存在爭(zhēng)議與不確定性。例如有觀點(diǎn)認(rèn)為,我國(guó)法律中的“應(yīng)知”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應(yīng)當(dāng)解釋為類似美國(guó)法上的“推定知道”,即根據(jù)已有證據(jù)與事實(shí)可以反證平臺(tái)處于知情狀態(tài)。但也有觀點(diǎn)為,“應(yīng)知”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不應(yīng)解釋為限于證據(jù)層面的推定知道,而應(yīng)當(dāng)解釋為包括其過(guò)失狀態(tài)所導(dǎo)致的“應(yīng)知而未知”。此外,對(duì)于平臺(tái)內(nèi)的疑似侵權(quán)行為,法院對(duì)于平臺(tái)的知情狀態(tài)的判斷也不同。例如在某健(中國(guó))日用品有限公司訴浙江某寶網(wǎng)絡(luò)有限公司侵犯商標(biāo)專用權(quán)糾紛案中,對(duì)于平臺(tái)內(nèi)的網(wǎng)店經(jīng)營(yíng)者所進(jìn)行疑似專利侵權(quán)行為,法院認(rèn)為平臺(tái)對(duì)于此類行為不屬于知道或明知。而在杭州某廣告有限公司與深圳市某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害發(fā)明專利權(quán)糾紛再審案中,法院認(rèn)為,對(duì)于平臺(tái)內(nèi)疑似專利侵權(quán)的行為不必以法院的判決為基礎(chǔ),某廣告有限公司“明知”其平臺(tái)上的疑似侵權(quán)行為而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應(yīng)當(dāng)對(duì)權(quán)利人擴(kuò)大的損失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
域外國(guó)家對(duì)于知情的法律規(guī)定與判斷也存在不確定性。以美國(guó)為例,美國(guó)成文法在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制定了“通知-刪除”規(guī)則,平臺(tái)在“實(shí)際知情”與“紅旗規(guī)則知情”的情形中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何謂“實(shí)際知情”與“紅旗規(guī)則知情”,法院的司法解釋不僅不斷變化,而且與立法意圖也存在較大差異。在不涉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言論侵權(quán)領(lǐng)域,美國(guó)則在其《通訊風(fēng)化法》230條款及其司法解釋中對(duì)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完全免責(zé),這就意味著即使平臺(tái)對(duì)平臺(tái)內(nèi)侵權(quán)完全知情,平臺(tái)也不承擔(dān)任何責(zé)任。而在普通法上,美國(guó)法院對(duì)于間接侵權(quán)在不同領(lǐng)域的知情要求也并不相同。例如在專利幫助侵權(quán)中,美國(guó)法院一般要求對(duì)侵權(quán)行為實(shí)際知情,但在著作權(quán)幫助侵權(quán)中,美國(guó)法院傾向于認(rèn)為,對(duì)侵權(quán)行為“推定知情”即可,即“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存在侵權(quán)行為。
近年來(lái),隨著算法推薦技術(shù)在網(wǎng)絡(luò)領(lǐng)域的廣泛應(yīng)用,有關(guān)于平臺(tái)知情狀態(tài)與責(zé)任的分析再次成為爭(zhēng)議焦點(diǎn)。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平臺(tái)既然可以利用算法技術(shù)進(jìn)行個(gè)性化推薦,就對(duì)存在侵權(quán)的算法推薦知情,或者至少“應(yīng)當(dāng)知道”相關(guān)侵權(quán)行為。而相反的觀點(diǎn)則認(rèn)為,算法推薦技術(shù)并沒(méi)有改變平臺(tái)責(zé)任的基本原理。既然避風(fēng)港制度將平臺(tái)知情限定在有限范圍內(nèi),那么平臺(tái)就沒(méi)有責(zé)任利用算法技術(shù)進(jìn)行一般審查。因此,利用算法技術(shù)的平臺(tái)并不需要承擔(dān)更高的注意義務(wù)。
(三)平臺(tái)作為的悖論
以知情狀態(tài)來(lái)分析和判斷平臺(tái)責(zé)任,不僅面臨上文提到的兩種制度協(xié)調(diào)與不確定性困境,而且還會(huì)導(dǎo)致平臺(tái)作為的悖論。一方面,以知情狀態(tài)分析與判斷平臺(tái)責(zé)任,可能導(dǎo)致平臺(tái)不作為或“不做不錯(cuò)”的悖論。如果以我國(guó)法上的“知道”或美國(guó)法上的“實(shí)際知情”“紅旗規(guī)則知情”界定知情,那么一些平臺(tái)可能會(huì)故意無(wú)視平臺(tái)內(nèi)的侵權(quán)行為。上文提到,美國(guó)法院認(rèn)定“故意無(wú)視”無(wú)法得到避風(fēng)港的保護(hù),就是為了避免平臺(tái)承擔(dān)過(guò)低的注意義務(wù)。而且,即使以我國(guó)法律中的“應(yīng)當(dāng)知道”或平臺(tái)過(guò)失來(lái)界定知情,法律也可能對(duì)平臺(tái)設(shè)置過(guò)低的責(zé)任。例如,當(dāng)平臺(tái)對(duì)于平臺(tái)內(nèi)侵權(quán)的審查與預(yù)防措施遠(yuǎn)低于同類平臺(tái)或行業(yè)的一般技術(shù)水平時(shí),可能導(dǎo)致平臺(tái)內(nèi)侵權(quán)行為的大量出現(xiàn),對(duì)被侵權(quán)人與社會(huì)造成嚴(yán)重負(fù)擔(dān)。在人身?yè)p害等嚴(yán)重侵權(quán)類型中,此類問(wèn)題將更為突出,平臺(tái)所產(chǎn)生的大量侵權(quán)行為將給社會(huì)帶來(lái)嚴(yán)重的負(fù)外部性。
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平臺(tái)作為可能出現(xiàn)“做多錯(cuò)多”的悖論。因?yàn)槠脚_(tái)越注意審查與防范平臺(tái)內(nèi)的侵權(quán)行為,平臺(tái)就越可能處于知情狀態(tài)。例如在上海某網(wǎng)絡(luò)科技有限公司與北京某信息技術(shù)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糾紛案中,法院認(rèn)為,從某視頻網(wǎng)站的后臺(tái)頁(yè)面來(lái)分析,被告在對(duì)網(wǎng)站進(jìn)行日常維護(hù)和管理過(guò)程中,會(huì)對(duì)網(wǎng)絡(luò)用戶上傳的節(jié)目進(jìn)行審批和推薦,這說(shuō)明其有權(quán)利和能力去掌握和控制侵權(quán)活動(dòng)的發(fā)生。
事實(shí)上,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的避風(fēng)港制度之所以被提出,正是因?yàn)橹殂U撍鶎?dǎo)致的種種亂象。1995年,在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之初,美國(guó)法院在斯特拉頓·奧克蒙特訴奇跡服務(wù)公司案中認(rèn)定,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內(nèi)容進(jìn)行了刪除、編輯和管理,這說(shuō)明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對(duì)侵權(quán)內(nèi)容知情,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類似出版商的角色,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言論侵權(quán)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這一判決引發(fā)了平臺(tái)的巨大擔(dān)憂和不作為,為了避免可能承擔(dān)的侵權(quán)責(zé)任,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索性不再作為,任由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各類違法信息泛濫,以此來(lái)證明自己對(duì)侵權(quán)信息不知情和不具有控制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在1996年制定了《通訊風(fēng)化法》230條款,免除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在言論領(lǐng)域的侵權(quán)責(zé)任,以保護(hù)對(duì)網(wǎng)絡(luò)內(nèi)容進(jìn)行治理的“好心人”。
在法律對(duì)平臺(tái)施加公法審查義務(wù)的背景下,“做多錯(cuò)多”的悖論會(huì)更突出。我國(guó)在若干法律法規(guī)中都規(guī)定了審查義務(wù),例如2000年制定的《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服務(wù)管理辦法》規(guī)定,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服務(wù)提供者不得制作、復(fù)制、發(fā)布、傳播九類個(gè)人信息,其中除了危害國(guó)家安全等具有明顯公法屬性的信息,還將“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quán)益的”也包括在內(nèi)。《電子商務(wù)法》《食品安全法》也規(guī)定了相應(yīng)的資質(zhì)資格審核義務(wù),要求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商業(yè)主體進(jìn)行實(shí)名登記、審查許可證。當(dāng)平臺(tái)履行其公法審查義務(wù),平臺(tái)就可能在審查過(guò)程中接觸了相關(guān)內(nèi)容,從而可能被認(rèn)定為對(duì)相關(guān)侵權(quán)內(nèi)容“知情”。
三、困境根源: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
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的知情分析之所以面臨挑戰(zhàn)與困境,與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的典型形態(tài)密切相關(guān)。典型的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是一種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與傳統(tǒng)特定個(gè)案型、共同侵權(quán)人相互獨(dú)立的侵權(quán)形態(tài)非常不同。一方面,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具有大規(guī)模的整體性特征,難以被分解為多個(gè)獨(dú)立、特定個(gè)案的共同侵權(quán)。另一方面,平臺(tái)與平臺(tái)內(nèi)主體具有治理關(guān)系,平臺(tái)既對(duì)于平臺(tái)內(nèi)主體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和侵權(quán)預(yù)防能力,同時(shí)又需要建立容錯(cuò)機(jī)制。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的形態(tài)變遷使得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分析難以直接適用。
(一)侵權(quán)形態(tài)的變遷
就小型、各自獨(dú)立的傳統(tǒng)間接侵權(quán)而言,此類侵權(quán)形態(tài)可以視為傳統(tǒng)一對(duì)一侵權(quán)的復(fù)合形態(tài)。一方面,傳統(tǒng)間接侵權(quán)不具有顯著的大規(guī)模性或外溢性,即該間接侵權(quán)行為是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發(fā)生的事件,該間接侵權(quán)行為與其他侵權(quán)行為并不具有聯(lián)動(dòng)性。例如,一個(gè)人撞傷他人或打破他人物品往往是偶發(fā)事件,侵權(quán)人并不對(duì)被侵權(quán)人或被侵權(quán)人親屬之外的一般人群產(chǎn)生影響。另一方面,傳統(tǒng)間接侵權(quán)行為中的共同侵權(quán)人彼此具有獨(dú)立性,相互之間并不存在管理或支配性關(guān)系。也因此,傳統(tǒng)間接侵權(quán)行為可以被拆分或被視為兩個(gè)獨(dú)立侵權(quán)行為的疊加。
但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的形態(tài)則非常不同。一方面,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典型形態(tài)具有大規(guī)模或外溢性特征。在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平臺(tái)所扮演的角色是普遍性而非特定的。平臺(tái)不僅與某一侵權(quán)行為有關(guān),而且涉及大量的同類侵權(quán)行為,是一種典型的一對(duì)多或一對(duì)海量的侵權(quán)關(guān)系。只有在少數(shù)情形下,平臺(tái)才會(huì)對(duì)某一特定對(duì)象進(jìn)行幫助侵權(quán)或教唆侵權(quán)。例如平臺(tái)對(duì)某一特定個(gè)體進(jìn)行言論誹謗,或者精準(zhǔn)化打擊平臺(tái)內(nèi)的某一商家,或者故意將某一熱點(diǎn)視頻編輯推送至網(wǎng)站首頁(yè)播放,此時(shí)平臺(tái)可能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侵權(quán)主體提供特殊幫助或進(jìn)行教唆。在此類情形中,平臺(tái)所參與的間接侵權(quán)就與傳統(tǒng)侵權(quán)具有類似性,也是偶發(fā)獨(dú)立事件,而且不會(huì)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一般主體產(chǎn)生影響。另一方面,平臺(tái)與平臺(tái)內(nèi)的經(jīng)營(yíng)者、消費(fèi)者、創(chuàng)作者等各類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并非完全獨(dú)立或平等,平臺(tái)與共同侵權(quán)人具有管理性或從屬性關(guān)系。兩者的這種關(guān)系使得平臺(tái)既可以對(duì)平臺(tái)內(nèi)主體進(jìn)行一定的風(fēng)險(xiǎn)預(yù)防,又需要避免在管理過(guò)程中對(duì)平臺(tái)內(nèi)主體造成傷害。
(二)知情狀態(tài)的相關(guān)性
從間接侵權(quán)的形態(tài)出發(fā),就可以發(fā)現(xiàn)知情狀態(tài)分析為何曾經(jīng)具有重要意義,又為何會(huì)在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陷入泥沼。傳統(tǒng)間接侵權(quán)雖然比直接侵權(quán)復(fù)雜,但其基本原理與直接侵權(quán)并無(wú)區(qū)別,都以過(guò)錯(cuò)(包括故意或過(guò)失)為前提。在此背景下,分析間接侵權(quán)人在個(gè)案中知情狀態(tài)就具有重要意義。在道德正當(dāng)性層面,判斷間接侵權(quán)人在個(gè)案中是否對(duì)直接侵權(quán)知情,是否在個(gè)案中故意促成直接侵權(quán)或放任直接侵權(quán)事件發(fā)生,可以對(duì)間接侵權(quán)人的過(guò)錯(cuò)與責(zé)任進(jìn)行較為合理的判斷。在效率與功利主義層面,分析知情狀態(tài)可以更為合理地對(duì)間接侵權(quán)人的一般行為進(jìn)行免責(zé),對(duì)故意或放任參與侵權(quán)行為的間接侵權(quán)人進(jìn)行威懾預(yù)防,從而維持人們行動(dòng)自由與預(yù)防侵權(quán)之間的平衡。
但在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分析間接侵權(quán)人在特定個(gè)案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已經(jīng)不再契合。在經(jīng)典的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案件中,平臺(tái)并不參與個(gè)案性的幫助侵權(quán)或教唆侵權(quán),平臺(tái)在間接侵權(quán)中并沒(méi)有個(gè)案性的意圖。因此,以個(gè)案中的知情狀態(tài)來(lái)判斷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并不能反映平臺(tái)在間接侵權(quán)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反,更為合理的方式是分析與判斷平臺(tái)在治理意義上是否履行合理注意義務(wù),是否平衡了各方利益。按照這一判斷標(biāo)準(zhǔn),平臺(tái)在間接侵權(quán)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應(yīng)當(dāng)從大規(guī)模和整體性的意義上進(jìn)行分析,也應(yīng)當(dāng)從兼顧預(yù)防與容錯(cuò)的治理意義上進(jìn)行分析。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應(yīng)當(dāng)避免僅僅關(guān)注特定個(gè)案,也不能僅僅從預(yù)防侵權(quán)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
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并非完全為平臺(tái)共同侵權(quán)所特有,一些非平臺(tái)侵權(quán)也可能具有部分類似特征。在這些類型的侵權(quán)中,以知情狀態(tài)分析侵權(quán)中的過(guò)錯(cuò)也面臨問(wèn)題。第一,工業(yè)化時(shí)代產(chǎn)品缺陷等侵害所導(dǎo)致的大規(guī)模侵權(quán)不再注重個(gè)案意義上的知情狀態(tài)。在此類侵權(quán)中,判斷侵權(quán)者是否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重要是產(chǎn)品制造者是否存在履行社會(huì)義務(wù)上的過(guò)失。美國(guó)學(xué)者威廉·普羅西(William#Prosser)將這一變化視為以個(gè)案知情與過(guò)錯(cuò)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城堡的崩潰”。在我國(guó),過(guò)失仍然被視為一種過(guò)錯(cuò),但這種過(guò)錯(cuò)已經(jīng)“客觀化”,與侵權(quán)方在特定個(gè)案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具有本質(zhì)區(qū)別。第二,很多侵權(quán)也具有管理型侵權(quán)的特征。例如當(dāng)勞動(dòng)者在履行工作職責(zé)時(shí)侵犯他人權(quán)益、跳蚤市場(chǎng)中的商家出售假冒偽劣商品,音樂(lè)廳允許他人演奏未獲版權(quán)的作品,此時(shí)用人單位、跳蚤市場(chǎng)的組織者、音樂(lè)廳組織者都可能因?yàn)槠涔芾斫巧袚?dān)連帶侵權(quán)責(zé)任。在此類侵權(quán)中,法律往往不需要考慮管理者是否知情,而是分析管理者是否從被管理者那里獲得直接經(jīng)濟(jì)收益。如果管理者從被管理者那里獲得直接經(jīng)濟(jì)收益,那么管理者將承擔(dān)替代責(zé)任。
不過(guò),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與一般過(guò)失侵權(quán)以及傳統(tǒng)管理型侵權(quán)仍具有重大區(qū)別。首先,就過(guò)失侵權(quán)而言,產(chǎn)品制造者在侵權(quán)中主要扮演的直接侵權(quán)角色,這與平臺(tái)所扮演的間接侵權(quán)角色不同。只有在少量的專利侵權(quán)中,才會(huì)出現(xiàn)生產(chǎn)者的共同侵權(quán)或間接侵權(quán)問(wèn)題。因此,各國(guó)對(duì)于產(chǎn)品責(zé)任的規(guī)定都限于直接侵權(quán)責(zé)任,排除了產(chǎn)品缺陷所導(dǎo)致的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而對(duì)于專利間接侵權(quán)中的產(chǎn)品責(zé)任,法律也排除了制造“通用商品”的生產(chǎn)者責(zé)任。這使得產(chǎn)品生產(chǎn)者的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仍然限于與傳統(tǒng)的間接侵權(quán)形態(tài)。此外,產(chǎn)品缺陷所引發(fā)的主要是人身財(cái)產(chǎn)侵害,而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除了在一部分情形中涉及人身安全,其他更多的情形主要涉及言論侵權(quán)、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商標(biāo)侵權(quán)等侵權(quán)類型。在言論與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等侵權(quán)形態(tài)中,其侵害程度較低,而且平臺(tái)更需要維持言論自由、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合理使用與保護(hù)權(quán)利人之間的平衡。基于這些原因,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與產(chǎn)品責(zé)任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分析仍然非常不同。產(chǎn)品責(zé)任可能適用過(guò)失責(zé)任(negligence)或嚴(yán)格責(zé)任(strict#liability),即要求產(chǎn)品責(zé)任承擔(dān)過(guò)失意義上的注意義務(wù)或更高的嚴(yán)格責(zé)任。但對(duì)于平臺(tái)而言,要求平臺(tái)承擔(dān)類似產(chǎn)品生產(chǎn)者的責(zé)任,對(duì)其適用產(chǎn)品責(zé)任法上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分析并不合理。
第三,就管理型侵權(quán)而言,用人單位、跳蚤市場(chǎng)的組織者、音樂(lè)廳組織者的用戶規(guī)模一般較小,這些管理者往往能夠?qū)ζ涔芾淼闹黧w進(jìn)行個(gè)案性監(jiān)管。而平臺(tái)則往往涉及海量用戶的管理,不太可能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主體進(jìn)行一一監(jiān)管。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如果適用替代責(zé)任,要求平臺(tái)承擔(dān)嚴(yán)格責(zé)任意義上的知情與注意義務(wù),也只能限定在平臺(tái)能夠直接獲益的特定案件中。在司法實(shí)踐中,美國(guó)法院認(rèn)定,替代責(zé)任只能適用于平臺(tái)能夠識(shí)別特定侵權(quán),并且具有直接經(jīng)濟(jì)利益的情形中。我國(guó)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司法解釋》第11條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因提供網(wǎng)絡(luò)服務(wù)而收取一般性廣告費(fèi)、服務(wù)費(fèi)”,并不屬于“獲取經(jīng)濟(jì)利益”。《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司法解釋》第22條規(guī)定,平臺(tái)“未從服務(wù)對(duì)象提供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中直接獲得經(jīng)濟(jì)利益”,將不需要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這些規(guī)定都反應(yīng)了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與傳統(tǒng)替代侵權(quán)的不同,不能將傳統(tǒng)替代侵權(quán)中的個(gè)案知情狀態(tài)與注意義務(wù)簡(jiǎn)單移植到平臺(tái)上。
四、原理重構(gòu)
上文已經(jīng)指出,判斷典型間接侵權(quán)中的平臺(tái)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分析大規(guī)模治理意義上的合理注意義務(wù),而非分析特定個(gè)案中的平臺(tái)知情狀態(tài)。本部分對(duì)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的具體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分析,指出其判斷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代價(jià)、治理難度、治理的比較優(yōu)勢(shì)等角度進(jìn)行分析。綜合而言,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分析平臺(tái)是否在整體治理意義存在過(guò)錯(cuò)。就平臺(tái)的間接侵權(quán)賠償責(zé)任而言,平臺(tái)在同一類型案件中的賠償總額應(yīng)當(dāng)與平臺(tái)因?yàn)橹卫磉^(guò)錯(cuò)而需要受到的罰款保持一致。
(一)注意義務(wù)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
首先,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侵權(quán)的危害程度進(jìn)行判斷。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所造成的社會(huì)危害性越大,平臺(tái)所應(yīng)承擔(dān)的注意義務(wù)就越大。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的類型很多,包括但不限于侵犯隱私權(quán)和個(gè)人信息、侮辱誹謗、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專利、侵犯?jìng)€(gè)人財(cái)產(chǎn)與人身安全。當(dāng)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僅僅造成偶發(fā)性的微型損害時(shí),此時(shí)平臺(tái)一般不需要承擔(dān)注意義務(wù)與相應(yīng)責(zé)任。相反,當(dāng)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造成了他人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損害,特別是造成了大范圍的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損害時(shí),平臺(tái)就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較高的注意義務(wù),防止此類事件的發(fā)生。我國(guó)法律在共同侵權(quán)與避風(fēng)港規(guī)則之外,進(jìn)一步規(guī)定了平臺(tái)的安全保障義務(wù),正是因?yàn)榘踩U狭x務(wù)涉及嚴(yán)重侵權(quán)。例如我國(guó)《電子商務(wù)法》第38條規(guī)定:“對(duì)關(guān)系消費(fèi)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wù),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經(jīng)營(yíng)者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經(jīng)營(yíng)者的資質(zhì)資格未盡到審核義務(wù),或者對(duì)消費(fèi)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wù),造成消費(fèi)者損害的,依法承擔(dān)相應(yīng)的責(zé)任。”美國(guó)一直是平臺(tái)免責(zé)的堅(jiān)定支持者,但在刑事犯罪領(lǐng)域,美國(guó)仍然于2015年制定了《停止廣告剝削受害者法案》,要求平臺(tái)對(duì)在線性販賣(Sex-trafficking)承擔(dān)責(zé)任。
其次,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應(yīng)結(jié)合其促進(jìn)的合法活動(dòng)與社會(huì)利益進(jìn)行判斷。其提供的公共服務(wù)和促進(jìn)的合法活動(dòng)越多,其注意義務(wù)越低。平臺(tái)的興起不僅帶來(lái)了侵害,也同時(shí)帶來(lái)了收益。對(duì)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與責(zé)任進(jìn)行分析,需要同時(shí)考慮二者。而此處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要求平臺(tái)對(duì)侵權(quán)承擔(dān)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也會(huì)同時(shí)導(dǎo)致平臺(tái)對(duì)一般內(nèi)容與用戶活動(dòng)進(jìn)行審查,傷害平臺(tái)內(nèi)的正常活動(dòng)。因?yàn)橹挥袑?duì)平臺(tái)內(nèi)進(jìn)行一般審查,平臺(tái)才有可能避免承擔(dān)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菲利克斯·吳將這種現(xiàn)象稱為平臺(tái)責(zé)任常常導(dǎo)致的“附帶傷害”,即平臺(tái)常常會(huì)因?yàn)楸苊馄溟g接侵權(quán)責(zé)任而進(jìn)行過(guò)度審查,附帶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合法活動(dòng)與合法用戶造成傷害。例如,如果要求平臺(tái)對(duì)所有疑似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承擔(dān)責(zé)任,那么平臺(tái)就會(huì)加大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各類言論、圖片與視頻的審查,刪除或下架很多表面侵權(quán)但實(shí)質(zhì)并非侵權(quán)的作品。因此,在判斷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時(shí),法律不僅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其可能造成的侵權(quán),而且應(yīng)關(guān)注預(yù)防侵權(quán)所帶來(lái)的“附帶傷害”。
再次,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通過(guò)平臺(tái)辨識(shí)侵權(quán)活動(dòng)的難度、改善平臺(tái)內(nèi)生態(tài)的成本進(jìn)行判斷。平臺(tái)越能夠以較小的技術(shù)與管理成本減少侵權(quán)行為,同時(shí)不影響平臺(tái)內(nèi)的合法活動(dòng),其注意義務(wù)就越高。以信息核驗(yàn)義務(wù)為例,此類辨識(shí)技術(shù)與管理方式難度較小,也不會(huì)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合法活動(dòng)造成影響,將其納入法定義務(wù)就具有更高的合理性。例如上文提到的《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第44條和《食品安全法》第131條都規(guī)定,如果平臺(tái)不能提供平臺(tái)內(nèi)經(jīng)營(yíng)者的“真實(shí)名稱、地址和有效聯(lián)系方式的”,平臺(tái)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電子商務(wù)法》第38條則規(guī)定,“對(duì)關(guān)系消費(fèi)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wù),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經(jīng)營(yíng)者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經(jīng)營(yíng)者的資質(zhì)資格未盡到審核義務(wù)”,“造成消費(fèi)者損害的, 依法承擔(dān)相應(yīng)的責(zé)任”。而在其他很多情形下,平臺(tái)精確辨識(shí)侵權(quán)活動(dòng)的難度或成本常常非常高。有的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常常需要高度專業(yè)化的知識(shí),例如,專利侵權(quán)、個(gè)人信息侵權(quán)具有很強(qiáng)的專業(yè)性,平臺(tái)很難憑借自身力量判斷某一主體是否侵犯了專利,某一平臺(tái)內(nèi)的信息處理者是否侵犯?jìng)€(gè)人信息。平臺(tái)對(duì)此類間接侵權(quán)承擔(dān)的責(zé)任相對(duì)較低,其通知?jiǎng)h除義務(wù)常常以法院的生效判決為前提。還有的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則常常需要權(quán)衡侵權(quán)與合理使用的邊界。例如侮辱誹謗等言論侵權(quán)常常需要考慮言論自由的抗辯,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常常遭受合理使用的抗辯。在此類間接侵權(quán)中,平臺(tái)很難通過(guò)算法技術(shù)或人工審查對(duì)言論侵權(quán)進(jìn)行精準(zhǔn)識(shí)別與刪除。如果平臺(tái)對(duì)疑似言論侵權(quán)或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內(nèi)容都進(jìn)行刪除,那就會(huì)導(dǎo)致大量正常表達(dá)的內(nèi)容遭受刪除,影響平臺(tái)內(nèi)用戶的言論自由。
最后,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應(yīng)分析是否首要侵權(quán)者承擔(dān)責(zé)任比平臺(tái)承擔(dān)責(zé)任更有效。首要侵權(quán)者責(zé)任與平臺(tái)責(zé)任的關(guān)系大致可以視為侵權(quán)與規(guī)制的關(guān)系,首要侵權(quán)者承擔(dān)責(zé)任越有效,平臺(tái)所需要履行的注意義務(wù)就越低。例如,當(dāng)平臺(tái)內(nèi)的商家為消費(fèi)者提供侵權(quán)損害保險(xiǎn),消費(fèi)者可以較為便利地獲得損害賠償;或者當(dāng)平臺(tái)履行信息核驗(yàn)與資質(zhì)審查義務(wù)、為被侵權(quán)方提供侵權(quán)起訴的途徑,且平臺(tái)內(nèi)商家具有足夠的賠償資金時(shí),直接侵權(quán)制度就可以有效地應(yīng)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侵權(quán)行為;而讓平臺(tái)承擔(dān)較高注意義務(wù)和承擔(dān)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則會(huì)逆向激勵(lì)平臺(tái),促使平臺(tái)對(duì)平臺(tái)內(nèi)內(nèi)容與活動(dòng)進(jìn)行過(guò)度規(guī)制與審查。反之,當(dāng)直接侵權(quán)制度無(wú)法有效發(fā)揮作用,此時(shí)平臺(tái)需要承擔(dān)更高的注意義務(wù)。例如直接侵權(quán)者從事高風(fēng)險(xiǎn)行為,但不具有足夠資金、無(wú)力履行損害賠償,使得受害人無(wú)法得到賠償,此時(shí)平臺(tái)就需要對(duì)此類行為承擔(dān)較高的注意義務(wù),防止平臺(tái)內(nèi)將大量的負(fù)外部性損失轉(zhuǎn)移給社會(huì)。在此類情形中,由平臺(tái)承擔(dān)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可以激勵(lì)平臺(tái)將負(fù)外部性內(nèi)部化,彌補(bǔ)直接侵權(quán)制度的不足。
(二)作為治理的侵權(quán)
關(guān)注平臺(tái)責(zé)任域外研究的讀者可能會(huì)發(fā)現(xiàn), 本文所論述的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的四大要素與道格拉斯·李其曼(Douglasamp;Lichtman)教授和威廉·蘭德斯(Williamamp;Landes)教授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20年前關(guān)于著作權(quán)幫助侵權(quán)的一篇研究中,兩位教授指出,平臺(tái)是否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幫助侵權(quán)責(zé)任,取決于四大要素:(1)第三方侵權(quán)的危害越大,平臺(tái)越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2)合法使用平臺(tái)的收益越少,平臺(tái)越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3)改進(jìn)平臺(tái)治理以不實(shí)質(zhì)性干擾合法活動(dòng)、減少侵權(quán)活動(dòng)的成本越低,平臺(tái)越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4)在執(zhí)法與預(yù)防侵權(quán)過(guò)程中,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制度相比直接責(zé)任制度的成本越低,平臺(tái)越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本文的分析大致對(duì)應(yīng)兩位教授所提出的四種考慮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 李其曼和蘭德斯的分析并未從平臺(tái)侵權(quán)的性質(zhì)層面對(duì)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進(jìn)行分析。對(duì)于讀者來(lái)說(shuō),其分析的論點(diǎn)與結(jié)論可能具有啟發(fā)性,但難免會(huì)讓人對(duì)其論述邏輯感到難以把握。尤其對(duì)于其提到的四點(diǎn)要素,一般讀者可能會(huì)感到困惑:為何是這四大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 這四大因素之間有何邏輯聯(lián)系?
從本文所論述的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出發(fā),就可以理解其中的邏輯與原理。首先,第三方侵權(quán)的危害性越大,即平臺(tái)在此類情形中的大規(guī)模治理義務(wù)越重。其次,合法使用平臺(tái)的收益越少,即平臺(tái)在此類情形中的治理間接侵權(quán)的附帶損失越小。再次,改進(jìn)平臺(tái)治理以不實(shí)質(zhì)性干擾合法活動(dòng)、減少侵權(quán)活動(dòng)的成本越低,即平臺(tái)在此類情形中的治理改進(jìn)難度越小。最后,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制度相比直接責(zé)任制度的成本越低,即平臺(tái)治理相對(duì)于侵權(quán)制度的優(yōu)勢(shì)越大。綜上所述,這四種要素分別從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代價(jià)、治理難度、治理的比較優(yōu)勢(shì)角度進(jìn)行分析。從大規(guī)模治理的角度理解間接侵權(quán),上述困惑就會(huì)迎刃而解。
需要指出的是,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的判斷也同樣納入了這些因素。例如《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司法解釋》第9條對(duì)判斷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是否屬于“應(yīng)知”,列舉了六項(xiàng)因素:(一)基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提供服務(wù)的性質(zhì)、方式及其引發(fā)侵權(quán)的可能性大小,應(yīng)當(dāng)具備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二)傳播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類型、知名度及侵權(quán)信息的明顯程度;(三)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是否主動(dòng)對(duì)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進(jìn)行了選擇、編輯、修改、推薦等;(四)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是否積極采取了預(yù)防侵權(quán)的合理措施;(五)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是否設(shè)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權(quán)通知并及時(shí)對(duì)侵權(quán)通知作出合理的反應(yīng);(六) 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是否針對(duì)同一網(wǎng)絡(luò)用戶的重復(fù)侵權(quán)行為采取了相應(yīng)的合理措施。這六項(xiàng)因素除了第(二)(三)項(xiàng)可能屬于特定個(gè)案侵權(quán)外,其他都屬于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中的考慮要素。
從本文所論述的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出發(fā),平臺(tái)在間接侵權(quán)中所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也可以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平臺(tái)的賠償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以平臺(tái)的治理過(guò)錯(cuò)為前提,當(dāng)平臺(tái)不存在治理過(guò)錯(cuò),平臺(tái)無(wú)需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當(dāng)平臺(tái)存在治理過(guò)錯(cuò),則其承擔(dān)的賠償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首先從整體性的角度進(jìn)行考慮,其對(duì)于某一類型的侵權(quán)賠償數(shù)額應(yīng)當(dāng)與平臺(tái)因?yàn)橹卫磉^(guò)錯(cuò)而需要受到的罰款保持一致。例如某一平臺(tái)企業(yè)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某類大規(guī)模侵權(quán)存在治理過(guò)錯(cuò),理想情況下應(yīng)對(duì)其處以5000萬(wàn)元罰款,那么其在所有此類間接侵權(quán)案中的整體賠償額也應(yīng)當(dāng)維持在5000萬(wàn)元。至于此類間接侵權(quán)案中的個(gè)案賠償額度,法院則可以考慮權(quán)利人受到的損失、對(duì)權(quán)利人進(jìn)行救濟(jì)的必要性等因素進(jìn)行綜合考慮,對(duì)賠償總額進(jìn)行合理分配。
五、制度重構(gòu)
從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知情問(wèn)題的一般原理出發(fā),可以對(duì)本文開(kāi)篇所提到的制度挑戰(zhàn)與制度困境進(jìn)行分析。本文開(kāi)篇提到,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的知情面臨三大問(wèn)題:共同侵權(quán)與避風(fēng)港制度中的知情要求不一致;知情判斷存在不確定性;知情判斷存在“做的少、知道的少、錯(cuò)的少”“做的多、知道的多、錯(cuò)的多”的悖論。克服這三大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是區(qū)分特定個(gè)案型侵權(quán)與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對(duì)前者適用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分析,對(duì)后者適用治理意義上的注意義務(wù)與責(zé)任分析。
(一)兩種制度中的知情
在特定孤立的平臺(tái)侵權(quán)案件中,無(wú)論是共同侵權(quán)還是避風(fēng)港制度,都可以按照傳統(tǒng)侵權(quán)中的知情過(guò)錯(cuò)進(jìn)行分析。以2020年修訂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司法解釋》為例,其中的若干條款屬于此類情形。例如,第4條規(guī)定“有證據(jù)證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與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情形;第10條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在提供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時(shí),對(duì)熱播影視作品等以設(shè)置榜單、目錄、索引、描述性段落、內(nèi)容簡(jiǎn)介等方式進(jìn)行推薦,且公眾可以在其網(wǎng)頁(yè)上直接以下載、瀏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得的”情形,第12條規(guī)定“將熱播影視作品等置于首頁(yè)或者其他主要頁(yè)面等能夠?yàn)榫W(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明顯感知的位置的”“對(duì)熱播影視作品等的主題、內(nèi)容主動(dòng)進(jìn)行選擇、編輯、整理、推薦,或者為其設(shè)立專門的排行榜的”情形。在上述情形中,平臺(tái)都主動(dòng)參與了特定的侵權(quán)案件。當(dāng)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存在上述情形,就應(yīng)當(dāng)推定平臺(tái)知道侵權(quán)行為和具有過(guò)錯(cuò),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責(zé)任。
在特定孤立的平臺(tái)侵權(quán)案件中,基于通知-刪除規(guī)則的平臺(tái)免責(zé)制度則不應(yīng)適用。因?yàn)榇祟惏讣c傳統(tǒng)的共同侵權(quán)案件類似,平臺(tái)無(wú)論是作為還是不作為,都具有顯著的主觀意志。在避風(fēng)港規(guī)則中,各國(guó)也將存在“明顯侵權(quán)事實(shí)”排除在保護(hù)范圍之外。避風(fēng)港規(guī)則整體上是一種合規(guī)免責(zé)制度,其主要功能是為平臺(tái)的自我治理提供法律保護(hù)。而特定、孤立的平臺(tái)侵權(quán)案件并不涉及自我治理,與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無(wú)異,其制度適用也就不應(yīng)受到避風(fēng)港規(guī)則的保護(hù)。
在典型的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中,首先應(yīng)避免套用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制度的邏輯分析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上文提到,《民法典》第1197條、《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第22和23條、《電子商務(wù)法》第38和45條、《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第44條都使用了“應(yīng)當(dāng)知道”或“應(yīng)知”的表述,這些表述常常被視為要求平臺(tái)承擔(dān)更高注意義務(wù)。此處需要強(qiáng)調(diào),此類注意義務(wù)應(yīng)當(dāng)是治理意義上的,而非傳統(tǒng)個(gè)案侵權(quán)中的注意義務(wù),也非產(chǎn)品責(zé)任等過(guò)失侵權(quán)中的注意義務(wù)。正如本文一再?gòu)?qiáng)調(diào),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是整體性而非個(gè)案性的,其對(duì)平臺(tái)治理的注意義務(wù)需要考慮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代價(jià)、治理難度、治理的比較優(yōu)勢(shì)等綜合性因素,而不能僅僅注意預(yù)防侵權(quán)事故。
在典型的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中,避風(fēng)港制度中的注意義務(wù)也應(yīng)按照治理的原則進(jìn)行理解與建構(gòu)。就事前而言,避風(fēng)港制度雖然免除了平臺(tái)的一般審查義務(wù),但這并不意味著平臺(tái)完全沒(méi)有治理意義上的事前注意義務(wù)。例如,當(dāng)平臺(tái)內(nèi)的嚴(yán)重侵權(quán)行為導(dǎo)致受害人無(wú)法獲得正常賠償,而平臺(tái)本可以利用很低的成本就此類侵害行為,且不會(huì)影響平臺(tái)內(nèi)的正常活動(dòng),此時(shí)平臺(tái)就應(yīng)被認(rèn)定為未履行治理意義上的注意義務(wù)。當(dāng)然,平臺(tái)的此類事前注意義務(wù)也應(yīng)當(dāng)是有限度的,并且應(yīng)結(jié)合本文所提到的要素進(jìn)行分析,這也是為何避風(fēng)港制度具有強(qiáng)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就事中而言,應(yīng)避免將權(quán)利人通知等同于平臺(tái)知情。如果將權(quán)利人通知等同于平臺(tái)知情,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將會(huì)回到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的邏輯:平臺(tái)在接到通知前處于不知情和沒(méi)有過(guò)錯(cuò)的狀態(tài),在接到通知后則參與到特定個(gè)案的共同侵權(quán)中。但這種理解并不合理。事實(shí)上,權(quán)利人所發(fā)出的通知可能是錯(cuò)誤通知,很多通知還可能是由權(quán)利人通過(guò)機(jī)器所發(fā)出的批量通知,甚至有的通知可能不是權(quán)利人所發(fā)出。無(wú)論何種情形,平臺(tái)在收到通知后都并未直接進(jìn)入完全確定的知情狀態(tài)。相反,平臺(tái)在收到通知后仍然需要對(duì)平臺(tái)內(nèi)侵權(quán)行為的事實(shí)進(jìn)行判斷,例如平臺(tái)需要判斷權(quán)利人所發(fā)出的通知是真誠(chéng)的還是惡意的? 其平臺(tái)內(nèi)侵權(quán)行為有多大概率是真實(shí)的? 從治理型侵權(quán)的視角看,平臺(tái)所接收到的通知更類似于舉報(bào)。對(duì)于舉報(bào),平臺(tái)需要對(duì)其性質(zhì)、概率進(jìn)行綜合性判斷,而非簡(jiǎn)單將某一方的舉報(bào)認(rèn)定為事實(shí)。就事后而言,平臺(tái)所采取措施中的知情狀態(tài)也應(yīng)按照平臺(tái)治理的邏輯進(jìn)行理解。平臺(tái)在接到權(quán)利人或法院通知后,可能需要采取刪除之外的多種不同措施。例如歐盟著作權(quán)法采取了較為嚴(yán)格的要求,要求對(duì)確定侵權(quán)的內(nèi)容進(jìn)行“屏蔽”,以確保侵權(quán)內(nèi)容不會(huì)重復(fù)上傳。這一規(guī)則實(shí)際上要求平臺(tái)對(duì)于預(yù)防侵權(quán)采取更高的注意義務(wù),因?yàn)橹挥袑?duì)平臺(tái)內(nèi)容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審查才能避免侵權(quán)內(nèi)容重復(fù)上傳。加拿大著作權(quán)法則采取較為寬松的規(guī)則,僅要求平臺(tái)進(jìn)行反通知,但不要求平臺(tái)刪除相應(yīng)侵權(quán)內(nèi)容。這一規(guī)則實(shí)際上將平臺(tái)視為消極被動(dòng)的裁決者,免除了平臺(tái)的積極注意義務(wù)。限于篇幅,本文在此無(wú)法對(duì)避風(fēng)港的具體制度進(jìn)行詳細(xì)論述。但可以指出的是,典型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的避風(fēng)港制度應(yīng)當(dāng)按照治理與舉報(bào)的原理進(jìn)行理解,而非轉(zhuǎn)換為傳統(tǒng)特定個(gè)案的共同侵權(quán)進(jìn)行理解。
(二)走出知情的不確定性
就知情分析的不確定性而言,通過(guò)區(qū)分個(gè)案特定型侵權(quán)與治理型侵權(quán),可以破解知情標(biāo)準(zhǔn)的統(tǒng)一性問(wèn)題。首先,無(wú)論是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制度還是避風(fēng)港制度,其知情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都應(yīng)當(dāng)是一致的,即在個(gè)案特定型侵權(quán)中按照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進(jìn)行判斷,在治理型侵權(quán)中按照治理意義上的注意義務(wù)進(jìn)行判斷。如果對(duì)于同一侵權(quán)類型與侵權(quán)形態(tài),采用共同侵權(quán)制度與避風(fēng)港制度對(duì)其進(jìn)行分析導(dǎo)致了不同答案,那只能表明相關(guān)制度設(shè)計(jì)或制度適用出現(xiàn)了偏差。
其次,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的分析應(yīng)避免法律解釋學(xué)上的語(yǔ)義學(xué)之刺,不必過(guò)于關(guān)注具體語(yǔ)詞與表述。上文提到,我國(guó)立法在知情問(wèn)題上采取了不同表述,例如《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使用了“不知道也沒(méi)有合理的理由應(yīng)當(dāng)知道”,《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法》使用了“明知或者應(yīng)知”,《電子商務(wù)法》和《民法典》使用了“知道或者應(yīng)當(dāng)知道”。《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司法解釋》則除了使用“明知或應(yīng)知”,還規(guī)定了“明顯感知”的表述。在本文看來(lái),對(duì)這些不同表述進(jìn)行詞義辨析意義不大。一方面,很多表述的區(qū)別不大,立法者在進(jìn)行表述選擇的時(shí)候并沒(méi)有特別清晰的考慮,甚至在立法草案與終稿中也不斷變化表述。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對(duì)于知情狀態(tài)與注意義務(wù)的分析主要與本文所提到的侵權(quán)形態(tài)與其涉及要素相關(guān)。如果相關(guān)侵權(quán)形態(tài)屬于特定個(gè)案型侵權(quán),則可以利用平臺(tái)在個(gè)案中的知情狀態(tài)來(lái)判斷平臺(tái)的過(guò)錯(cuò)與責(zé)任。相反,如果相關(guān)侵權(quán)屬于治理型侵權(quán),則其注意義務(wù)分析取決于本文所提到的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代價(jià)、治理難度、治理的比較優(yōu)勢(shì)等因素。平臺(tái)是否具有過(guò)錯(cuò)與是否承擔(dān)責(zé)任取決于其大規(guī)模治理意義上的注意義務(wù),而非個(gè)案中的知情。
再次,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的分析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不同領(lǐng)域而進(jìn)行建構(gòu)。對(duì)于不同領(lǐng)域,平臺(tái)治理特征非常不同,而同一領(lǐng)域的平臺(tái)治理特征則具有相似性。例如在涉及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特別是公民健康的侵權(quán)中,法律所要保護(hù)的權(quán)利屬于絕對(duì)性權(quán)利,對(duì)其進(jìn)行治理具有很強(qiáng)的必要性。而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法律所要保護(hù)的權(quán)利常常需要與他人的合理使用權(quán)利進(jìn)行平衡。因此對(duì)于涉及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的侵權(quán)與涉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侵權(quán),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就應(yīng)當(dāng)有所不同,法律應(yīng)當(dāng)對(duì)前者施加更高的注意義務(wù)或安全保障義務(wù),對(duì)后者則應(yīng)當(dāng)施加較輕的注意義務(wù),賦予平臺(tái)更大的自治權(quán)。而且,即使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內(nèi)部,針對(duì)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專利、商業(yè)秘密的平臺(tái)侵權(quán)也具有差異,對(duì)不同類型的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也應(yīng)建構(gòu)不同規(guī)則。目前,我國(guó)一方面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消費(fèi)者權(quán)益保護(hù)、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食品安全等不同領(lǐng)域確立了不同的注意義務(wù),這種設(shè)置具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我國(guó)的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也面臨碎片化與不協(xié)調(diào)問(wèn)題。例如《電子商務(wù)法》對(duì)涉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間接侵權(quán)做出了特殊規(guī)定,這一規(guī)定有可能引起法律解釋的不一致。更為合理的方式是根據(jù)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專利等不同領(lǐng)域的間接侵權(quán)進(jìn)行特殊規(guī)定,實(shí)現(xiàn)同一領(lǐng)域的規(guī)則統(tǒng)一性。
最后,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應(yīng)借助個(gè)案認(rèn)定實(shí)現(xiàn)其確定性。本文關(guān)于知情不確定性的分析可能會(huì)讓一部分讀者感到,平臺(tái)的知情標(biāo)準(zhǔn)處在高度不確定性狀態(tài),無(wú)論是個(gè)案特定型侵權(quán)還是治理型侵權(quán)都面臨不確定性。對(duì)于孤立與特定型侵權(quán),平臺(tái)在個(gè)案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很難統(tǒng)一判斷。對(duì)于治理型侵權(quán),綜合考慮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代價(jià)、治理難度、治理的比較優(yōu)勢(shì)等因素,也同樣無(wú)法避免知情標(biāo)準(zhǔn)不確定的問(wèn)題。上述擔(dān)憂不無(wú)道理。不過(guò)需要指出,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中的間接侵權(quán)形態(tài)雖然千變?nèi)f化,但法律通過(guò)案例仍然可以形成較為確定的規(guī)則。尤其是一些典型案例,例如涉及網(wǎng)站分享軟件侵權(quán)的案例、涉及用戶公開(kāi)共享型平臺(tái)的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案例,這些案例可以為判斷平臺(tái)注意義務(wù)提供基準(zhǔn)。當(dāng)這些典型案例被法律實(shí)踐與社會(huì)廣泛接受后,由案例所創(chuàng)造的規(guī)則也可以進(jìn)一步凝練為司法解釋或成文法。
從上述進(jìn)路出發(fā),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知情分析的不確定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以本文開(kāi)篇所提到的算法推薦問(wèn)題為例,算法推薦本身并不能作為判斷平臺(tái)是否對(duì)個(gè)案知情的標(biāo)準(zhǔn),但是算法也并非天然中立,算法仍然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大規(guī)模治理意義上的注意義務(wù)。此外,算法推薦中的平臺(tái)責(zé)任也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不同領(lǐng)域與類型,并通過(guò)案例來(lái)確定平臺(tái)的治理責(zé)任。例如對(duì)于《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服務(wù)管理辦法》第15條第(一)至(七)款規(guī)定的嚴(yán)重違法型言論,平臺(tái)應(yīng)當(dāng)具有更高的算法治理責(zé)任;對(duì)于第15條第(八)款規(guī)定的“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quán)益的”,平臺(tái)的算法治理責(zé)任相對(duì)較低。總之,算法推薦雖然是新技術(shù),但并未改變其基本原理,其治理義務(wù)也應(yīng)當(dāng)綜合考慮本文所歸納的若干因素進(jìn)行判斷。
(三)破解平臺(tái)作為的悖論
就知情悖論而言,按照本文所區(qū)分的個(gè)案與特定型侵權(quán)與治理型侵權(quán)進(jìn)行分析,相關(guān)問(wèn)題就將不復(fù)存在。就個(gè)案特定型侵權(quán)而言,“不做不錯(cuò)”“做多錯(cuò)多”的推理并不存在問(wèn)題。由于平臺(tái)在個(gè)案中具有較為顯著和可以辨析的主觀意志,利用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中的知情與過(guò)錯(cuò)概念對(duì)平臺(tái)責(zé)任進(jìn)行判斷具有合理性。就像在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中,幫助侵權(quán)或教唆侵權(quán)者在共同侵權(quán)案件中知道的越少、介入越少,其承擔(dān)連帶侵權(quán)責(zé)任的可能性就越少。
在治理型侵權(quán)中,無(wú)論是“不做不錯(cuò)”“做多錯(cuò)多”,還是“不做就錯(cuò)”“做了免責(zé)”都不合理。判斷平臺(tái)是否存在治理上的注意義務(wù),關(guān)鍵是判斷平臺(tái)在治理意義上作為的合理性,而不是判斷平臺(tái)是否作為,是否對(duì)個(gè)案或一般侵權(quán)知情。就平臺(tái)不作為而言,如果平臺(tái)內(nèi)存在大量侵權(quán),而且平臺(tái)主要用于侵權(quán)用途、平臺(tái)本可以以較小成本阻止侵權(quán)卻不作為,那么即使平臺(tái)對(duì)個(gè)案侵權(quán)不知情,平臺(tái)也需要承擔(dān)責(zé)任。這正是美國(guó)法院在Napster案等P2P軟件侵權(quán)案件中所采取的立場(chǎng),也是我國(guó)司法所采取的立場(chǎng)。而當(dāng)平臺(tái)可以被用于大量非侵權(quán)用途,例如面向公眾(public-facing)的視頻分享網(wǎng)站可以被用于普通用戶創(chuàng)造、交流與公共空間建構(gòu),那么即使平臺(tái)不作為或采取與P2P類軟件案件中同等的審查過(guò)濾措施,平臺(tái)也可能被認(rèn)定不需要承擔(dān)責(zé)任。這正是美國(guó)在維亞康姆公司訴油管案中的立場(chǎng),也是我國(guó)司法所采取的立場(chǎng)。各國(guó)司法之所以在P2P類軟件案件中與面向公眾的視頻中采取不同立場(chǎng),表面原因在于二者的法律分析框架與適用不同,但深層原因在于前者主要用于侵權(quán)活動(dòng),而后者則具有廣泛的社會(huì)合法用途,因此法律對(duì)于后者的注意義務(wù)要求更低。在Napster案中,Napster公司曾經(jīng)提出愿意采取積極審查措施,將其軟件中的侵權(quán)率降至很低,但法院仍然宣布Napster應(yīng)當(dāng)對(duì)平臺(tái)內(nèi)侵權(quán)承擔(dān)責(zé)任。
另一方面,平臺(tái)作為也應(yīng)根據(jù)治理意義上的注意義務(wù)進(jìn)行判斷。平臺(tái)作為無(wú)疑會(huì)提高平臺(tái)對(duì)于間接侵權(quán)的知情程度,但知情程度并不意味著平臺(tái)就一定需要承擔(dān)責(zé)任。如果平臺(tái)越知情,就越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治理責(zé)任,則此類制度設(shè)計(jì)將會(huì)導(dǎo)致平臺(tái)對(duì)間接侵權(quán)行為的消極應(yīng)對(duì)或過(guò)度規(guī)制。一方面,平臺(tái)可能會(huì)取消本來(lái)已有的審查措施,以證明自己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間接侵權(quán)并不知情。另一方面,平臺(tái)也可能會(huì)采取嚴(yán)厲的審查措施,過(guò)濾很多本來(lái)合法的用戶內(nèi)容與用戶活動(dòng),以防止自己承擔(dān)間接侵權(quán)責(zé)任。對(duì)于平臺(tái)作為,更為合理的制度應(yīng)當(dāng)是看平臺(tái)的作為是否符合其治理義務(wù)。如果平臺(tái)的積極作為或積極審查從其合理治理出發(fā),則無(wú)論這種積極作為是屬于自我規(guī)制還是法定審查義務(wù),則平臺(tái)都應(yīng)基于其積極作為而免責(zé)。相反,如果平臺(tái)未從治理出發(fā)進(jìn)行積極作為,則其積極作為是武斷和非理性的,那么平臺(tái)的積極作為或積極審查可能傷及平臺(tái)內(nèi)的正常活動(dòng)。此時(shí),平臺(tái)反而可能需要因?yàn)槠浞e極作為而對(duì)本文所提及的“附帶傷害”承擔(dān)責(zé)任。
結(jié)語(yǔ)
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中的知情問(wèn)題是一個(gè)困擾法律實(shí)踐與法學(xué)學(xué)術(shù)的老大難問(wèn)題。本文研究指出,造成這一問(wèn)題的根源在于典型的平臺(tái)侵權(quán)具有與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非常不同的形態(tài)。在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中,共同侵權(quán)人具有平等、特定的關(guān)系,因此對(duì)間接侵權(quán)人適用知情分析與過(guò)錯(cuò)判斷具有合理性。但在典型的平臺(tái)侵權(quán)中,平臺(tái)所扮演的是大規(guī)模治理的角色,即使平臺(tái)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侵權(quán)個(gè)案,平臺(tái)所采取的行動(dòng)也會(huì)引起大規(guī)模的連鎖效應(yīng),具有整體性或一般性的意義。此外,平臺(tái)不僅導(dǎo)致第三方侵權(quán)事件的發(fā)生,而且?guī)?lái)了大量的合法活動(dòng),面對(duì)平臺(tái)內(nèi)的侵權(quán)活動(dòng)或權(quán)利人狀態(tài)不確定的通知投訴,平臺(tái)所采取的行動(dòng)需要考慮其治理意義上的合理性,而不能僅僅考慮預(yù)防侵權(quán)事件發(fā)生。
從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的特征出發(fā),本文指出在典型平臺(tái)侵權(quán)中,平臺(tái)知情狀態(tài)分析需要走出特定侵權(quán)個(gè)案的泥沼,轉(zhuǎn)而從大規(guī)模治理是否存在過(guò)錯(cuò)分析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具體而言,平臺(tái)在此類侵權(quán)中的注意義務(wù)與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綜合分析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代價(jià)、治理難度、治理的比較優(yōu)勢(shì)。首先,無(wú)論是傳統(tǒng)共同侵權(quán)制度中的“應(yīng)知”或“應(yīng)當(dāng)知道”,還是避風(fēng)港制度中的通知-刪除規(guī)則,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都必須按照大規(guī)模治理型侵權(quán)的原理進(jìn)行重構(gòu)。其次,平臺(tái)的注意義務(wù)超越個(gè)案知情分析和知情規(guī)定的語(yǔ)義分析,重點(diǎn)按照分領(lǐng)域、案例建構(gòu)的方式構(gòu)建相關(guān)規(guī)則。最后,平臺(tái)作為與不作為的責(zé)任也要超越個(gè)案知情判斷,既需要避免“不做不錯(cuò)”“做多錯(cuò)多”的悖論,也需要避免簡(jiǎn)單適用“不做就錯(cuò)”“做了免責(zé)”。綜合而言,在典型平臺(tái)侵權(quán)中,平臺(tái)間接侵權(quán)的制度需要按照大規(guī)模治理侵權(quán)的原則重新建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