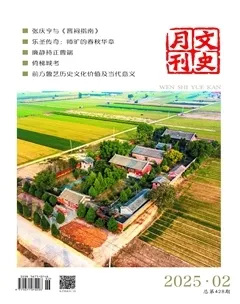樂圣傳奇:師曠的春秋華章
華夏文明長河,圣賢閃耀夜空,這其中有一位傳奇人物,被譽為“樂圣”。他以卓越的音樂才華、非凡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風范,在歷史的交響曲中留下了悠遠的回音。他的故事距今已近2600年,至今仍散發著其獨有的光輝,這個人就是師曠。

師曠,字子野,出生于晉國,因是晉人,又稱晉野。他是春秋時晉國羊舌食邑(今山西省洪洞縣師村)人,先秦著名音樂大師,被尊為樂圣。他曾擔任晉國太宰,也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最早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師曠的事跡,漢代班固撰《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小說家著錄《師曠》六篇,《兵書略》陰陽家另有《師曠》八篇。師曠的言行散見于《左傳》《史記》《周書》《國語》《說苑》《淮南子》《琴史》等諸多書籍之中;師曠聲名能傳于世,得益于莊周、孟子、韓非、季札、叔向、宋玉、桓譚、劉安、劉勰、韓愈、朱熹、王世貞等諸多名士之推許。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百家爭鳴。在這個動蕩的歷史時期,天下名家輩出,各陳雄思,不僅催發了不朽的思想,推動了歷史賡續的潮流,亦為文化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師曠憑著自身的聰慧和對音樂極高的天賦,鉆研音樂技藝,探索音樂的奧秘,從音樂的角度追求至高意境,同時弘揚仁德要義,論述治政之理,最終成為了一位集藝術造詣、思想德操和偉岸人格于一身而備受尊崇的音樂大師。
通樂律
《左傳》中記載,師曠之聰天下聞名。據說他并非天生眼盲,而是因為他覺得眼睛看到的東西太多而不能專注于音律,便用艾草熏瞎了自己的眼睛。而后,他便憑借著敏銳的聽力,在聲音的世界中自由騁懷。當他彈琴時,馬兒都會停止吃草,仰起頭側耳傾聽,覓食的鳥兒也會停止飛翔,翹首迷醉,掉落口中的食物。如此神乎其神的技藝,讓師曠名聲遠播。晉平公知道他有如此才能后,便命他為掌樂太師。

師曠的音樂成就極高,演奏技巧出神入化。他擅長演奏各種樂器,如琴、瑟、簫等,尤其以善彈古琴為最。師曠的古琴曲在古代音樂史上占據著極高的地位,備受古代文人雅士的推崇,是古代高雅音樂的典范。據《神奇秘譜》所載,《陽春》《白雪》《玄默》等曲目皆為師曠所作。“陽春白雪”一詞,便由此而來,后世常用它來形容藝術的高雅脫俗。《禮記·樂記》中所言:“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師曠的音樂,正是他內心世界的光影,是他以自己的心靈采擷世界的美妙而呈現出來的,是世界呈現給他的樣子。

師曠不僅是一位出色的音樂家,還是一位杰出的音樂理論家。他提出了“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于廣遠也”的音樂思想,強調音樂的社會功能和教育作用。他認為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凈化人的心靈,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其后孔子在《論語》中所倡導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思想與此不謀而合。師曠還創立了五音六律的音樂理論體系,為后世音樂理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朝人袁皓在他寫的《書師曠廟文》中感嘆“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郁郁。先生既生,斯音在律”。意思是說,上天將最美好的音樂寄托于八音之內,在師曠沒有精通音樂前,八音郁郁不可聽,師曠精通音理后,才將八音調和成優美的音律,賦予了它們全新的生命。

師曠的音樂造詣沒有停留在音樂本身的藝術層面上。他贊成“樂者,德之華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這樣的理念,將音樂視為關乎道德、社會和政治的重要事物,展現出了高深的洞察力和智慧之道。他認為中正之音陶冶性情,可以培養出仁愛、忠誠、謙遜等美德,進而遠離浮躁與邪惡。他堅決反對淫樂,認為那是對道德的褻瀆和對國家的危害。因此,師曠以樂資政,將音樂視為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希望通過好的音樂來啟發民眾溫良向善的秉性,實現社會和美、國家大治,這一理念將西周禮樂制度的精神內質延續了下來。
在晉平公新王宮落成的慶祝典禮上,衛靈公率樂工前來祝賀。宴會中,衛靈公命師涓演奏從濮水邊聽到的一支新奇的曲子。師涓剛彈到一半,師曠猛然起身,按住師涓的手,斷然喝止:“快停住!這是亡國之音啊!千萬彈不得!”原來,此曲是商朝末期樂師師延為商紂王所作的“靡靡之音”。師曠深知這類音樂乃非善樂,堅決阻止師涓繼續彈奏。師曠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堅定的藝術信仰,堅持用音樂演奏養德、養性、與政治相和諧的樂章,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藝術思想財富。
資政事
《淮南子》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太宰一職“總六官之事,事無所不統”,師曠幾乎參與了晉國內政、外交、軍事等一系列事務,悼公、平公每每請教于師曠時,他都能“因問盡言”,闡述出得當的治國論斷,足見其身份之重要,才能之出眾。
在政治方面,師曠最突出的見解和貢獻在于民本思想。師曠出身于窮困的庶民家庭,在堯舜精神的感召下形成了忠君護國的品性和價值衡量。他倡導清明政治,仁義為本,施德于民。一次,悼公問師曠怎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得更好,師曠只回答了一句:“惟仁義為本。”這就是師曠民本思想的實質。《孟子·盡心下》中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師曠作為春秋時期民本思想的重要倡導者,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雛形,認為“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良君應“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不能“肆于民上,以從其淫”。他還主張君主應施行“仁義”,做到“惠民”,《韓非子》中記載,齊國國君齊景公向師曠三次問政,師曠都回答:“君必惠民而已。”可見,愛民是師曠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推崇用仁君之道治理國家。
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凈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他的這些觀點,深受諸侯及民眾的贊同,對后世民本思想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古代那個命由天定、民如草芥的社會,這些觀點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政治家們的愛民治世之道。
諫君王
師曠竭忠盡責、正直無畏、敢于進諫的精神也是令人欽佩的。他秉性剛烈,胸懷坦蕩,正道直行,義不屈節,從不趨炎獻媚,遠非一般人所能比,實在是一位光明磊落的良臣。
西漢劉向編著的《新序》“雜事”中,記載著“師曠論五墨墨”的故事,雖然情節簡單,卻展示出了師曠匡正君主、竭忠盡責的情懷。一日,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師曠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心懷國家,以天下為己任,有膽有識,面對君主不卑不亢,敢于指出國家之隱患,以“五墨墨”之論直言時弊,透過問題直言要害,為君主和國家敲響警鐘,恪盡忠誠與擔當。
《韓非子》中還記載著“師曠援琴撞平公”的事跡。一天,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被衽而避,琴壞于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于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在那個封建等級制度森嚴的年代,臣子對君主的言行通常是極為謹慎的,稍有不慎可能就會釀成殺身之禍。師曠這一次不計后果的犯顏直諫,在歷史中可謂振聾發聵。他援琴而撞,不僅源于對君主的警醒,更是對正道的恪守和對國家未來命運的守護。
當晉平公說出“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這樣有悖于君主之道的話時,師曠沒有選擇沉默或阿諛奉承,而是懷著一心為國家、為君主著想的赤誠之心,以最激烈的方式指出君主之言的不當,讓君主明白作為一國之君應有的言行和德操。他也讓人們深刻體會到真正的臣子不只是唯命是聽的順從者,更是敢于指出君主過錯、為國家和百姓深謀遠慮的勇者。師曠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忠誠與擔當的真正含義,在諸侯爭霸的局勢中,他仿佛是晉國一道不可動搖的脊梁。
強外交
除了處理晉國內政,師曠還通過外交活動維護晉國的切實利益。《逸周書·太子晉解》篇記載:周靈王二十二年(前550年),晉平公遣叔向出使周王室,叔向與太子晉交談后,頓覺自己才疏學淺,而太子晉才智出眾人所不及,滿臉羞愧地回到晉國后對晉平公進言:“太子晉年僅十五歲,我卻無法與之交談。您應歸還聲就、復與這兩個地方。否則,待他日后擁有天下,必定會來討伐我們。”晉平公心中遲疑,欲歸還二邑。此時師曠挺身而出,向晉平公請纓道:“臣愿前往與太子晉一辯。若臣不能勝之,再論歸還之事亦不遲。”晉平公點頭應允。

師曠到了周王室,果然太子晉雖然年少,卻氣度非凡。師曠言辭精當:“吾聞王子言論高如泰山,吾夜不能寐,晝不得安,千里迢迢而來,只求與王子交談,以解心中疑惑。”太子晉道:“我聽太師要來,驚喜交加。我年紀尚小,才德淺薄,見到您深感畏懼,以至于失態。”隨后師曠向太子晉問君子之德,太子晉引經據典,贊揚舜帝如《尚書》所云:“德自舜明。”又言大禹“圣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與不好取,必度其正,是謂之圣”。師曠禁不住點頭稱贊,適時回應道:“王子見解,臣感佩至極。吾國君亦常以古之圣賢為范,推行仁德。”巧妙地傳達了晉國的治國理念。
師曠又問身份等級,太子晉詳述《周禮》所載之等級秩序,由胄子而至天子無一錯漏。師曠認真聆聽,不時提出獨到的見解,展現出對各國制度的深刻理解:“各國雖制度有別,但皆以維護天下安定為旨。吾國君亦深知此理,力求在諸侯之中樹立典范。”師曠再問可有溫和恭敬、敦厚敏捷,初處下位,后而能為帝臣、天子之人,太子晉以虞舜作答。繼而師曠唱《無射》,“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其聲悠揚。太子晉回以《嶠》歌,歌聲清脆。師曠贊嘆道:“王子之才,如明珠璀璨。若各國皆如王子這般賢明,天下必將太平。”借此表達了對天下大治的期望。
此次會面可知,太子晉確實知識淵博、口才出眾,但師曠也憑借其淵博的學識、卓越的口才和深沉的秉性,一直使太子晉面臨著巨大的思想和心理壓力,時時刻刻保持著對師曠的恭謹。師曠出使周朝,足以顯示出晉國人杰不凡,贏得了太子晉的尊重,去除了叔向形成的弱勢,重新平衡了晉國與周的關系,晉取周田之事也就因之不會再被刁難,達到了出使目的。這次出使不僅顯示了師曠的外交才干,維護了晉國利益,還擴大了師曠的影響,提高了師曠的名望。
立良言
師曠留下了許多經典的言論和故事,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師曠勸學”。據《說苑·建本》記載,晉平公問師曠:“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懇切地說:“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最后一句“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一語雙關,說得平公點頭稱是。這番話不僅激勵了晉平公,更成為了后世勸學的經典名言,提醒人們學習莫怕遲暮,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好學的心,學就比不學好。
除了散記下來的言論故事,實際上師曠在預知自己壽命將終之時,還著述了《寶符》一書,集中闡述自己的思想。據記載,這部書共一百卷,可惜的是到戰國時在戰亂中湮滅失傳了。關于《寶符》具體的內容和思想,由于書的失傳已無從知曉,但從師曠的身份以及所處的時代背景來推測,《寶符》可能會涉及到音樂理論、政治思想、哲學思考等方面的內容。師曠作為著名的音樂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或許是對自己一生的經驗、見解和感悟的總結與提煉。也有人猜測《寶符》中可能包含了對國家興衰、君主治理、社會秩序等方面的觀點和建議,以及對音樂與政治、社會、人生之間關系的探討。總之,《寶符》的失傳,無疑是文化長河中的一大遺憾,那百卷結晶的消散,仿佛一葉滿載智慧的舟船劃入了時間的深海。
雖然《寶符》失傳,人們再無法得窺師曠著作的至道之思,但師曠的精神依然如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火,照亮后人向學的心路。他所說的“炳燭之明”,已然像箴言一樣印刻在思想的經幡上,成為引人前行的一道光,告誡人們要珍惜年華、學習不怠。
去朝堂
師曠秉性剛烈,義不屈節,敢于直言進諫。他數次指斥君主之過,勸誡君主秉持仁德、勤勉政事、遠離佞臣。他本坦蕩無私,但朝堂之上,權力的爭斗暗流涌動,那些忌憚師曠的威望、心懷叵測之人,開始暗中謀劃,準備抓住機會將他排擠到權力之外。晉平公后期貪圖享樂、賞罰不明,師曠的直言不諱被權貴們利用,他們在君主面前進讒言,欲置師曠于死地而后快。君王在讒言的影響下,逐漸對師曠產生了恨意。
一日,平公在虎祁之臺設宴,為泄私憤,事先命人在臺階上布滿蒺藜,隨后召師曠前來伴奏。師曠著履上堂之際,平公怒責:“豈有人臣著鞋登主堂之理?”遂命師曠脫鞋襪拾級而上,致其足被刺傷。接著又逼師曠綰起褲腿跪地,使蒺藜刺其膝蓋。師曠強忍疼痛,仰天悲嘆。平公高居其上,大言不慚道:“今日不過與你開個玩笑,何必如此悲傷?”師曠憤懣而言:“肉自生蛆而自食,木自生蠹而自蛀,人自興妖而自殘。國君之殿堂,竟長出蒺藜,豈非妖魔作祟!”且斷言:“人生妖孽,必定自毀。下月初八日,整飭百官,確立太子,君將亡矣!”晉平公無言以對,頓失體面,遂氣急敗壞,心生殺機。未幾,稱師曠企圖犯上,即判罪問斬。心向師曠的大臣們紛紛跪于堂前,請求赦免師曠。晉平公氣怒難消,然自知理虧,但恐眾叛親離,不得不收回成命,免師曠死罪,削職為民。
最終,在激烈的政治斗爭后,師曠離開了朝堂回到故里。他雖年近古稀,卻壯心不泯。其言:“吾不可老朽無為,當于暮年之際,將己之技藝傳予鄉民,以了平生之愿。”于是,師曠教授百姓們音樂技藝,還創立鼓樂班,讓他們以吹打謀生。據傳,晉南之同樂會鼓樂班,便起源于此。因師曠首創鼓樂班,且洪洞乃其故里,故此地民間鼓樂藝人,皆尊師曠為吹鼓手的祖師爺。
安故里
師曠去世后葬于故鄉,人們為了表達對他的尊崇與敬仰,便在他的墳墓旁建造了祠廟。《大清一統志》《山西通志》《平陽府志》俱載:“師曠墓在洪洞東南二十里,近有祠。”

《洪洞縣志》載有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隱士張守大為整修師曠祠而撰寫的《師曠廟記》,文中說:“師曠生前為晉國賢臣,其言行有益于當時,又利于后世,有功于人民。”在古代,立廟是一種極高的榮譽,通常只有對國家和人民有重大貢獻的人才能享此殊榮。《禮記·王制》中記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這明確規定了不同身份的人在祭祀上的差異,也從側面反映出不是所有人死后都有資格立廟。師曠生為晉國主樂太師,以其卓越的音樂才華和正直的品德,對晉國的文化發展和政治穩定都作出了巨大貢獻,死后當受廟食之禮。
《洪洞縣志》載有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周樂師子野墓碑記》一文,從中看到師曠祠重建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從元代到清代,先后整修過五次。幾經修葺,增建了樂廳、花欄走廊,大門上書“晉國樂師廟”五個大字。師曠廟前,后來又建造了一座戲樓,高而不寬,上有楹聯:
上聯:恐矮子觀場故將樓臺高蓋起;
下聯:為癡人說夢始用鑼鼓鬧喧天。
對聯詼諧有趣,又耐人尋味。遺憾的是抗日戰爭期間,戲樓以及祠廟都被拆去建造防御工事了,對聯存入了記憶,鑼鼓之聲也就此沉寂,所幸師曠之墓尚在此地。

據說,師曠墓的兩旁曾經有石人四尊,分別操持著琴、箏、竽、笛四種樂器。師曠墓前,豎有石碑,高七尺五寸,上書“周樂師子野冢”。碑前設石幾、石鼎各一個,石觚兩個。石幾方四尺,厚七寸;鼎依照周朝百乳式,高四尺一寸;觚依照商朝四象式,高四尺一寸。古時,鼎為立國之重器,觚系王公貴族所用之禮器,庶民百姓不能享用。由此可見師曠的身份與威望。
師曠的一生,高潔、偉岸且充滿傳奇。他被尊為樂圣,豈止是因為他的音樂成就,更在于他的生命所散發出的遠超音樂的光輝。“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師曠的傳奇人生,是他樂得其道、以樂載道、以樂修德的深刻詮釋,是他高尚品德、過人智慧和卓越才華的結晶。
歲月如歌,人們對師曠的尊崇鐫刻在時間的丹青上,師曠的故事流淌在歷史的血脈里。他的音樂、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都成為了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他的故事,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