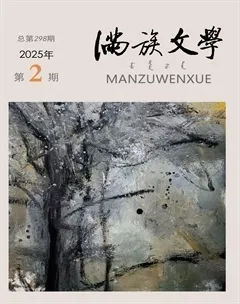歷史的尺度
我以為我是到過這里的。5月5日,傍晚五時,車子從吉安機場駛出,半小時的高速公路疾馳后,轉過一個岔路口,開始進入盤山公路。來接站的駕駛員說,現在要進入景區了。景區二字,讓我微怔了下。
剛下過雨,路面微濕。車子與柏油路面的摩擦發出令人感到踏實的沙沙聲。兩側山岡,換了新葉的樹,亦皆有葳蕤的濕意。路旁不時會閃過一些色彩鮮艷的雕塑。巨型的吹號手,巨型的拳頭,巨型的槍。這些革命年代遺留的符號,提示著我這座山晚近的歷史。然后出現了燈光,出現了市鎮。路邊走過成群結隊的男女,皆身著灰色的土布軍服,戴八角帽,這讓我有了些微的時間錯亂之感。
茨坪到了。
這個山間盆地在夜色中竟也有著都市的恢宏氣派,都是因為那些高大的酒店。那些燈飾,在漸漸濃重的夜色中越發的璀璨了。如許的繁華,總讓人疑心那些慘烈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在這里發生過。
行政區劃意義的井岡山市已遷到山下。城市的腹地,在山上生發不開,山下有交通之便利,自有更大發展空間。海拔千米之上的茨坪,現在真的成了一個景區。既然作了“景”,在時間的長河中它已固化,靜靜地向世人展示著什么,更多的是獨屬于它的記憶。
我記得是到過當時作為縣治的茨坪的,十年前,也或許二十年前。但觸眼之處,竟無一處識得,這讓我疑心或許那只是一個夢,我是在夢里造訪了這個著名的地方。個體的記憶,或者群體的意識,因為有無意識作祟,本來就不一定靠得住的。
井岡山自秦朝設郡縣,為九江郡廬陵縣屬地,這是我來的路上就知道了的。晚餐在中泰來國際大酒店一樓,文聯主席鄒巧逢先生帶來了廬陵產的名酒,名字起得好,叫堆花。我雖有許多江西朋友,慚愧的是對廬陵知道不多,席間都是聽鄒主席在說道。我只約略記得,我五百年前的同鄉王陽明,結束在貴州的流放,起復后的第一站即任廬陵知縣。他大概在廬陵的時間并不長,很快就巡撫贛南了,直到寧王在南昌舉起反幟,他匆忙帶兵平叛,遂致成就一生功業。廬陵那時是屬于吉安府的,王陽明后來去廣西平思田之亂,扶病北歸,翻過大庾嶺,就是死在贛江上青龍鋪碼頭的一艘船上。陪著他走過臨終之際的,就是他的一個學生、吉安府的推官王大用。只是不知道王陽明的臨終語“吾心光明,此復何言”,是不是王大用記錄的。終王陽明不長的一生,他與江西的緣分實在是難分難解。他一直執師禮的理學大師婁諒,也是江西人。
5月6日,各路作家陸續到齊,東道主怕我們旅途勞累,未安排出門。在酒店開會,談當下散文,談井岡山,談革命的文學化表達。東道主邀請了井岡山干部學院的教授講大革命歷史,還請了烈士袁文才的后代說家族往事。教授議論縱橫捭闔,自是一堂生動大課,袁氏后人談祖父之死及家族命運,也因其親歷者的視角,讓聽者頗為動容。我贊同一同來開會的蔣藍兄引述的敬澤先生的話,散文者,國之重器也,如何用散文的形式去書寫、反思這場革命及革命留給今天的遺產,的確對作家而言是個大命題。也不一定所有作家都有勇氣來接受這樣一個大命題的挑戰。
講課的教授專修馬列,主持有重點社科項目,對中國近代史和革命史了如指掌,言語親和,又充滿自信。要作家們運用文學的手段書寫革命歷史,也屬時代之音。我只做了一個小小補充,歷史的文學化敘述固然是一種手段,歷史更需要的是科學化的敘述,一種面朝著歷史本相的敘述。竟引得會議主持人江子兄一番哂笑。或許在眾人眼里,我就是個靠“文學化”吃飯的。慚愧則個,我當自省。我這一番胡言亂語的“去文學化”,會不會讓我成為作家公敵?
江西的作家自是極好相與的。江子、傅菲、陳蔚文,皆是十年前上三清山就識得的舊友。這些年他們在小說、散文疆域里或寫都市,或寫傳統中國,無一有歷史負荷之重態,皆蓬勃而有朝氣,這正是我無論為文還是為人都極看重的。他們自然不會真的笑我孤陋。新識的蔣藍、謝宗玉、王瑢,老友馬敘、龐培、鄭驍鋒,亦皆英特不凡之士,即使心下不甚同意我之所說,怕也不會怪我唐突。
心下卻還是在辯駁,自己跟自己較著勁。設若我是1920年代的一個小知識分子、教書匠或者報館記者,1927年秋天正好在江西,我會不會就上了井岡山?那時二次北伐正在開展,全國矚目津浦線南北大戰,我或許會是革命軍中一馬前卒,卻斷斷不會在此地出現。又設若到了北伐告成,以寧岡為中心的革命之火也愈燃愈烈之際,有農民兄弟動員我去參加革命,又有當局以征詢國家建設大計為由請我去廬山喝茶,我又將作何選擇?
南昌、武漢、上海、北平。一個多么波瀾壯闊的年代,革命是時代主音,壓倒一切,人人都企盼著一個完整的、不受外侮的新中國的出現,我的胸中也涌動著正義者的火氣。而我拿之作革命的對象,很可能只是舊的文法,我的“火氣”,很可能是沖著舊秩序舊禮法。我需要一次覺悟,一次讓我心悅誠服的洗禮。這是一個無解的假設,眾聲喧嘩中,我抄錄了一段王國維的話以作這番自我辯駁的總結:“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入理上。”
唯一不需要假設的,是我于2017年5月的一天來到了井岡山。這是一個事實。不布其因,不得其果。這因,既是江子兄的盛情邀請,也是我對井岡山的一份探究之心,說得更遠一點兒,是肇始于這塊土地的一場最終成功了的革命吸引著我。
第二日,是個南方俗稱的“黃胖天”,陽光透過云層籠著這方崇山之間的小盆地,無風,燠熱。從茨坪中心出發,去看了博物館、紀念塔。號稱五大哨口之一的黃洋界離茨坪不遠,有五哨公路通達。當年工事及上山小路還依稀可見,營房則保存完好。此處海拔1343米,扼居山口,形勢險要,當地人稱摩天嶺確非言過其實。山頂有碑,碑上大字,自是看景者必到處。東道主安排很是盡心,還安排了幾處新農村建設的樣板點,農業皆如盆景,收入全賴旅游,當年戰場地,今日旅游點,景區之說,原是一點兒沒錯的。
象山庵是停留較多的一站。庵前無人,門口兩把木椅,像在寂然中說著無盡往事。五月的山間,蒼翠日深,此處的庵堂、樓梯、天井,也似乎在時光的陰影里。南方習俗,庵里是忌行夫妻大禮的。九十年前此地舉行的那場婚禮(墻上還貼著該日酒宴的菜單),和男女主人公隨后的命運,只添人無盡唏噓。出了庵,又去看了袁文才墓地。烈士的墓已經修繕,雖不氣派,也是個經常有人祭掃的模樣。墓前雜草,原是有個名的,蔣藍兄博識,與我說過,倉促無以記下。
這個季節,正趕上井岡山上杜鵑花的花期。聞名遐邇的“井岡山杜鵑”,據說其色是“漸變”的,初時粉紅,爾后漸成紫紅,雖然此次沒來得及去賞花的最佳處筆架山,看不到高峻的山崖間的十里杜鵑長廊,但沿途處處,山崖下、橋堍下,皆有一枝兩枝杜鵑花零星地冒出來,也足堪令人驚喜了。在童年時代就看過、聽過的《閃閃的紅星》《十送紅軍》這些經典的革命電影和歌曲里,杜鵑花是種多么神奇的革命花卉。當它漫山遍野開遍時,那如火般絢麗的花色,單瓣的、簡約的姿態,曾喚起一個少年素樸的革命情懷。
在這里我想到了另一種南方的杜鵑。那杜鵑是開在浙西的莫干山上。莫干山的氣候、植被,與井岡山相近,一過四月,遍山是花,杜鵑花尤盛。1928年初,幾乎就在井岡山的革命之火燎原之際,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因辦理對日外交失敗,心灰意冷中于莫干山上筑“白云山館”,準備在此隱居,打發余生。他在那里教村民識字,養蠶,開辦學校,發起農村改良運動。那時,去莫干山最慣常的是走水路——坐船從京杭運河過塘棲,再經武康鎮,由避暑灣上岸至三橋埠,再雇一頂轎走不了多少路就可以到達山下的庾村。等到上海與杭州的火車通了之后,又多了個選擇,坐火車到杭州,再坐夜航船到三橋埠,再陸行到庾村。從杭州拱宸橋到三橋埠,每天都有對開的小火輪。杭州人上莫干山,尤其是上了年紀的,都喜歡坐小火輪。黃郛上山的1928年春天,庾村剛通公路,鎮口的莫干山車站也剛剛落成不久。
黃郛后來又數次出山,其人雖抱大志,但國事日凋,一己之力無以挽回,最后赍志以殞。當他在山上將養病體時,日以侍弄“春園”自娛,春天到來時滿山的紅杜鵑,也曾點燃起他的生命意志。待他肝病稍有起色,妻子沈亦云約妹妹沈性仁來山陪護,亦云知二妹性仁是個愛花人,亦愛昆曲,就用《牡丹亭》中的曲語發去一信:“此地遍青山啼紅了杜鵑。”
這革命的花卉,到此際竟也有了一種人倫之美。
歷史的河流浩浩湯湯,革命是偶然,也是必然。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年,也是血與火中的一百年,革命年代已經遠去,所有的沉重,終抵不過消費文化的消磨。時代的積習就是這樣。今天的井岡山,街道整潔,城郭如新,皆是國家安泰之征象。躺在地底下的革命者,他們當年的夢想里或許正有此一景。
而浙西的莫干山,許多年后,黃郛夫婦發起農村改進運動時種下的梧桐,都已大可合抱,他們在莫干山下開辦的學校已難覓蹤影,當年的藏書樓,也看不到一本書了。蠶繭場已成廢園,一幫年輕的設計師把它搞成了一個青年旅舍“繭舍”。紅色鐵皮的樓梯,屋檐下縱橫的老式電線,高挺的梧桐樹下的木地坪,革命年代的標語殘留,進入此地還是會有一種被舊時光包圍的感覺。
于此我想到,在所有的一切之上還高懸著一個歷史的尺度。就像當年黃郛的妻子亦云在自敘傳里所說:“有人以為記著歷史是自沉于過去,我不敢。有人以為表彰身后,我亦不盡然。歷史并非僅英雄豪杰之事,是成此歷史的民族生活記錄。亡國不能有歷史,草昧難有記錄,貢獻一點事實,即貢獻一點歷史;歷史的尺度,可能為人道的尺度。”
歷史的尺度,即人道的尺度。誠哉斯言。
井岡山的那幾日,我帶了電子版的《想象的動物》在看。這是博爾赫斯的一本小書,大陸無譯,我看的是臺灣新知文庫版的譯本。和蔣藍兄說到此書,他說他的朋友、詩人鐘鳴早年有一打印本,如武功秘籍般,藏書于懷,至無人處,就拿出來看一眼。蔣藍說鐘鳴,是《山海經》加《爾雅》。然說到方法論,我看他還是博爾赫斯作底色,寫的還是想象中的動物和世界。一日酒后,和蔣藍說到,我們兩人都很想由井岡山的杜鵑花發凡,來做一本井岡山的植物志。我們都喜歡的布羅代爾說過,氣候、地理、飲食、習俗,這些東西塑造了一方生民的性格,它們是更本質的歷史。習慣于對歷史作長時段考量的我們,已經按捺不住要再作一次井岡山之行了。
【責任編輯】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