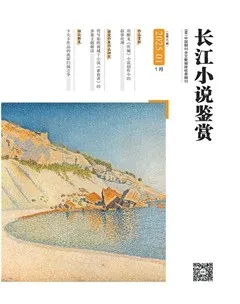劉醒龍《聽漏》小說創作中的敘事倫理
[摘要]劉醒龍的小說《聽漏》不僅是一部楚文化考古題材的文學佳作,更深刻反映了人性、歷史與現實交織的倫理關系。劉醒龍以其獨特的敘事手法,將人物的命運、文化的傳承以及歷史的演變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不僅反映了楚國青銅文化,更折射出復雜的社會倫理關系。本文從歷史倫理、科學倫理、人際倫理三個方面對《聽漏》的敘事倫理問題展開深入探索。
[關鍵詞]青銅重器" "敘事倫理" "小說創作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1-0013-06
我們面對青銅器,往往是在銅銹斑斑中尋找歷史的痕跡與王朝的秘密,在冰冷的器物中感受人文的溫度與先民的氣息。劉醒龍的“青銅重器”系列在人與物之間所構建的敘事線索,讓博物館展柜玻璃背后靜穆、沉睡的器物鮮活起來,蘇醒過來。器物因人而活,人因社會而存,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最密切關系便是人倫規則,小說所說的不僅是青銅重器,更是社會人倫關系,正如作品封面上寫的三句話,“揭開重器的千古之謎,叩問情義的百年交集,探討文化的歷史倫理”,本文所探討的正是這種敘事倫理線索。
一
第一條敘事線索是青銅器物所承載的歷史倫理。歷史倫理是一個涉及歷史進程中的道德、價值和倫理觀念的廣泛領域,它探討的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行為、社會制度、文化變遷等方面所體現的倫理規范和道德標準。周王朝以青銅器為主,漢代以漆器玉石為主,唐宋以后陶瓷珍寶為最,明清以金銀器物為多。周自夏商基礎上建國,傳承了“九鼎天下”的理念,在商鼎的基礎上發展了食器、樂器、禮器的系列規制,這些青銅重器所傳達的歷史倫理,首先是等級制度,體現了天子諸侯、尊卑貴賤、嫡庶長幼、親疏遠近的秩序。作品中最大的謎團圍繞“九鼎八簋”和“九鼎七簋”而展開,因為它們代表著歷史身份地位上的尊卑貴賤。在楚學界,青銅重器的嫡庶之分,集中在“簋”的數量上,西周的秋家壟僅出土七只,而東周的曾侯乙卻有八只,這才引出作者探秘的故事線索——“在楚學界,青銅重器的嫡庶之分,集中在曾侯乙大墓出土的九鼎八簋與秋家壟出土的九鼎七簋身上。……至于誰誰是嫡?誰誰是庶?只有曾本之和馬躍之有資格成為大家的談資。”[1]周代歷史中禮樂制度是極其嚴格的,什么身份配享什么器物,否則便是德不配位,超過規定的數量和規制就是“僭越”。楚學院兩大專家的研究重心一直是秋家壟大墓中“丟失”的那個“簋”,因為按照曾家為“姬姓”子孫的身份配享了九只“列鼎”,然而“簋”卻只有七只,這缺少的一只“簋”,是后來因故丟失,還是根本就不曾有過?這既是歷史的千古懸念,也是小說敘事的神來之筆,為故事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歷史倫理還表現在制度更迭方面。由于時間的變動不居,它不會因誰而停留,因此唯物史觀強調歷史發展的客觀性和規律性,認為歷史倫理是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遷而演變的,沒有一成不變的規章制度。小說中還提到一個重要線索,那就是青銅方壺,這個被盜取、收藏、轉手的器物,為小說情節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揭秘線索。在青銅方壺的壺蓋上,曾篆刻著“曾仲游父,子孫永寶”八個字,意思是父親將傳家寶交給了兒子,曾姓家族的子孫要永保這份榮華富貴。從周王朝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青銅器物上所銘刻的“子孫永寶”不過是一種美好的祝愿,其背后所代表的禮樂制度因西周建禮制樂而興盛,讓周王朝成為中原地帶最文明、先進的國家,也因東周時期“禮崩樂壞”而亡,成為諸侯僭越、逐鹿中原的犧牲品。本應“子孫永寶”的那幫子孫卻成為“問鼎之輕重”的掘墓人。曾侯乙作為東周時期一個小小曾國的君主,在諸侯大國環伺的環境下,下葬規制竟配享“九鼎八簋”(其祖先也不敢過于僭越,只敢配享九鼎七簋),自認為與周天子同一級別。所謂“時也勢也”,周天子對眾多諸侯國失去了約束力,以至于各諸侯敢于“平起平坐”,嫡庶無序、尊卑倒置,因此曾侯乙的所作所為不過是歷史變動、制度更迭的一個縮影。
周王朝所代表的歷史倫理核心是“為政以德”的理念。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2]德與政是一貫相連的,政是德所依附的力量,德是達到政的目標要求的手法。當然,以德治國并不是全面施以仁政,所謂的仁政更多地表現為對商遺民的寬容和分封諸侯的朝貢制度上,社會治理的德性主要表現為制度上的長幼有序、尊卑有別、主從有矩。西周在實力強盛時同樣也有“鐵腕手段”——對外施行“攘夷”與“膺服”政策,對內則對諸侯的“僭越”行為“嚴懲”與“共讎”。小說結尾處揭示了這種“德政”所帶來的威壓與逼迫感,“周天子敕令七簋之外的八號簋上,須有銘文‘天子不滅天滅’,這是這位曾姓王侯不愿意做,又不得不做的事。到頭來,唯有用拖字訣,拖到一命嗚呼,將做好的陶范一起下葬”[1]。如今,時隔千年,在小說的探秘中,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墓主人的悲憤與不甘,或許這便是周王朝等級倫理所帶來的沉重感,雖然這些青銅重器如今都靜靜地放置在展臺上,但是那些制作精良、美輪美奐、高大威猛、精致典雅的青銅重器,仍然透露出那個年代森嚴莊重的強大氣息。耐人尋味的是,在面對青銅重器的時候,人們談的最多的便是“僭越”,而這又是“德治”所嚴令禁止的,作家有意無意地增加了這種“禁令”的神秘性。如同“法老的詛咒”一樣,馬躍之因為手不潔觸摸青銅重器而在生活中被燙傷;某島國的王子與“九鼎七簋”合影,卻接到老國王的一紙御令而成為“廢太子”;楚學院某任領導,曾拿著越王勾踐劍顛來倒去而被一紙紅頭文件免職。凡此種種,都讓小說中的青銅重器籠罩著一種神秘的氣息,其實,作者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對現代人進行警示,今天的人面對歷史、文化、祖先的遺物不能褻瀆,而要始終保持一顆敬畏之心。
二
第二條線索是考古專業所蘊含的科學倫理。小說中除了青銅重器,主要的故事線索都發生在歷史研究的權威機構——楚學院。在這個機構之中,既有楚史研究也有以田野考古為主的青銅重器學會,在這二者之間,作者明顯是帶有傾向性的,“楚史研究與田野考古不太一樣,前者很容易被不懂行的人形容成自說自話,后者因為有充滿底氣的器物擺在面前,容易受到顯而易見的崇拜”[1]。小說在典型環境設置上,也讓楚學院充滿了人情世故、明爭暗斗,在讀者心中不僅沒有學術研究的氛圍,反而充滿了“鉆營”與“算計”。別有意味的是,楚學院辦公室門口充滿“文化氣息”的門牌名稱,如“秦樓楚館”“楚弓楚得”“楚楚動人”“朝秦暮楚”“楚囚對泣”,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楚學院內部的門門道道、蠅營狗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篇小說是具有一定諷刺意味的,尤其是對于人文主義知識分子而言,學術研究同樣是空談為虛,實證為要,通過這種傾向性的描述,作者自然而然地將那些具有考古精神的知識分子區分了出來。像楚學院的老前輩周老爺子、學術專家曾本之、后起之秀馬躍之,還有一個非考古專業卻具有專業精神的“聽漏人”,作者在這些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傾注了大量精力,其實是想高揚考古專業所蘊含的科學倫理精神。
考古學是歷史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人文學科。簡單地說,考古學就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相比較歷史研究,考古學更講求實證性和科學性,絕不能虛構與杜撰。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曾經比較過“文獻歷史”與“歷史考古”的區別,他認為“歷史從事于記錄過去的重大遺跡,把它們轉變為文獻,……它們無聲地講述著與它們所講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考古學作為一門探究無聲的古跡、無生氣的印跡、無前后關聯之物和過去遺留之物的學科,只有重建某一歷史話語才具有意義。考古學是對歷史重大遺跡作本質的描述”[3]。在哲學家眼中,這種通過蛛絲馬跡還原歷史現場的“考古學”才是知識探索的正確方式,往往會帶來歷史研究的新突破,或許知識的發現本來就是不斷地突破與驚喜。
這種考古專業所蘊含的科學倫理首先便是講求實證性,正如小說中談道:“考古這行也就是通過實物證明加上典籍研究,闡明包含在各種資料中的因果關系,提取存在于古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1]曾本之退休前將“九鼎七簋”的探索作為楚學院的一個重要課題遺留了下來,他希望通過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找到缺一“簋”的歷史原因與實物證據。這種實證除了努力之外也是需要機緣的,如果不是竹筒墓的發掘,如果沒有那只制作青銅簋的陶范,如果沒有《楚湫時地記》的印證,如果沒有馬躍之的研究……太多的“如果”令這種實證研究難如登天,這也側面反映了科學研究的難度與挑戰。其次是講求實踐性,考古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田野調查與發掘,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跡和遺物,多埋藏在地下,通過發掘、鑒定、分類等復雜的工作,這些實物資料才能被系統、完整地收集起來。正如小說中馬躍之面對鄭雄“吹捧”之語的回復:“考古研究,最有效的方式是拿起鐵鍬和鋤頭,找準一塊地方,挖一個底朝天,是爛泥黃土,還是青銅重器,用不得半個虛詞,事情就這么定了!”[1]馬躍之想表達的便是科學研究還是要多些實干,少些空談,要在歷史現場找證據,要在文物遺跡中找線索,這些都無法紙上談兵,這也是馬躍之在多年不從事青銅研究之后,面對周老先生“曾隨一家”的設想與曾本之“九鼎七簋”的課題而作出的一個重大選擇,他要通過實踐的方式來找到歷史的依據。最后是講求“坐冷板凳”。范文瀾在1956年北大演講時說過做學問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意思是研究者要專心致志做學問,不追求名利,甘于寂寞,同時也包括做學問當中不去追隨時尚,隨風倒,而是要堅持自己的學術方向,不怕別人不重視。小說中的曾聽長在“聽漏”這一行業有一個奇異的規矩,那就是一天不能超過十句話,否則“聽漏”的功力就會減退一截,行業規矩雖然神奇,其實這也象征著探究學問就要話少實干,逆風而行,甘于寂寞,善于探究,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成為行業的翹楚,正如聽漏工在水務局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馬躍之在青銅研究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專家,都有這種“坐冷板凳”精神。作者對這種精神推崇備至:“獨守空室,不聞世風,眼界只有一物,唯有用身心與之交合。這種工作,在這種城市里,能做到盡職盡責,盡善盡美,除了馬躍之,真的不清楚還有幾人。”[1]
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在今天浮躁的現代社會日益成為稀缺的品質。在充滿利誘、欲求的商品社會,人們往往追求快速成功和即時滿足,卻往往忽視了踏實努力、持續積累的重要性。在快節奏、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也容易盲目跟風、隨波逐流,卻往往忘記了保持冷靜和理性,學會認真分析問題尋找解決之道。古人云“道德文章”,作為道德說理的小說創作同樣是有倫理傾向的,去偽存真也好,祛惡揚善也罷,文學創作同樣承載倫理之道、教化之意,小說名為“聽漏”,作為創作者,何嘗不是一種具有考古敬業精神的“聽漏人”?既為我們的現實生活指出“遺漏”(問題)所在,同時也試圖在人文知識界建立起一種科學倫理的解決思路。
三
第三種線索是人情社會所體現的交際倫理。人情社會,是一種以人際關系和人情交往為基礎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基于法律和規則的約束,更多的是基于情感、信任和互惠互利的考慮,這種關系網絡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這部小說中,人情戲、爭斗戲、尋親戲、愛情戲、家庭戲、官場戲等占據了絕大多數的篇幅,反而歷史與考古的敘事內容主要是起到了穿針引線的功能,當然,這也可能符合作者的設定,那就是通過歷史來映照現實。小說中,曾本之、萬乙、玉帛、小玉仿佛是曾侯乙墓葬中的器物在現實中醒來,還有周、田、魯、陳、姜、王等兩周姓氏,仿佛春秋歷史中的人物重生今朝,繼續攪動風雨,濺起浪花,這種敘事模式其實顯示出人情社會交際倫理的復雜性、多元性、利益性,他們因怨重生、因情而聚、因利而別、因怨生恨,其中的緣起緣滅、因果關系,恐怕只有局中人、現代人、社會人才能深刻理解。那么,在這部小說中,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交際倫理呢?
一是利益交換。小說一開頭便顯現了楚學院并不那么和諧的氛圍,從學習鄭雄會長帶來的文件到鄭雄會長“職位”的獲得,人們內心仿佛是頗有腹誹的,主要原因是“德不配位”——以往青銅重器學會會長都是學高身正的專業人員擔任,而馬躍之對青銅重器研究的刻意回避,讓鄭雄在“老省長”的影響下“鉆了空子”成為青銅學會的會長。與此同時,鄭雄還是楚學院的前書記、前會長曾本之的前女婿,這些身份都代表著鄭雄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與急功近利的仕途追求。可惜的是,鄭會長獲得身份的方式不是在學術之路上更進一步,而是為獲得“晉升之階”搞關系、拉資源、博名聲,讓原本是研究機構的楚學院成為職場表演的重要場所。有利益的交換就有利益爭斗,鄭會長“楚越之急”的求利思想很快影響了楚學院的風氣,從“不爭”到爭辦公室,到爭座位,再到爭各種排名和職級,到后來甚至連乘電梯、上衛生間都要排先后順序。所謂“上有所好下必其效”,半年時間不到,這類操作儼然成為楚學院的“社會文化”。人情社會中,人們之間的互動往往伴隨著利益的交換。然而,當這種交換變得扭曲時,就可能形成不健康的倫理關系。
二是情感介入。小說中的情感戲非常豐沛,像馬躍之與柳琴、曾小安與鄭雄、萬乙與沙璐等,有些情感是男女婚戀,其中的分分合合、纏繞糾葛自不必多論,而有些情感卻是過度介入,“姜部”與“班長”那隱晦的婚外情耐人尋味,鄭雄帶著七八位領導參觀省博物館,這幾人都身居高位且都是同學關系,其中的“班長”更是大家巴結吹捧的對象,而在鄭雄講解“九鼎八簋”與“九鼎七簋”的嫡庶關系時,或許是觸動了“姜部”的神經,她狠狠地拍打了“九鼎七簋”的防護玻璃以至于引發了報警系統,“班長”的勸告不起作用,反而引來了“姜部”的咆哮:“庶出!庶出!你老娘才是庶出!”其中的曖昧關系昭然若揭。這種情感上的過度介入也會導致家庭關系危機重重,就像秋老太太與陸達仁的婚姻關系,為血脈留存而與寡婦情人出軌的情感狀態直接改變了幾代人的身世命運,這何嘗不是情感過度帶來的因果關系。
三是潛在規則。小說中馬躍之由于是青銅研究方面的專家,經常被紀委請去鑒定文物真假,因為官場、職場的人情往來與利益交換,會將一些玉石、字畫甚至青銅器物作為“禮物”來進行賄賂,當人際關系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時,人們可能會傾向于通過私下的關系網來尋求利益,而不是通過正當途徑。這種傾向不僅破壞了社會規則的權威性和公信力,也助長了腐敗和違法行為的滋生。如同小說中那個關鍵的線索——青銅方壺,便是幾經轉手,自秋風發現后,兜兜轉轉到了管監獄的沙局長手中,又從沙局長轉到水務局的陸少林,陸少林則因為一場“無妄之災”,將以為假貨的青銅方壺交給了紀委,其中的潛在規則耐人尋味,為什么會到他們手中,他們之間為何轉手,其中的奧秘只有自己知曉。當然,這種人情往來也可能導致禍事,一旦東窗事發,這些文物的價值都會成為收受者的罪證,就像馬躍之在監獄中看到的汪副秘書長,他因為貪污受賄而入獄,當年請馬躍之鑒定過的玉蟬終究給他帶來了牢獄之災。小說中沒有明說其中是怎樣的利益交換,但至少給我們揭開了文物倒賣與官場往來的神秘一角。
以上只是深深根植于我們文化之中的人情社會所體現的交際倫理的部分面相,小說中還有一些其他內容的描寫,它們如同一張錯綜復雜的網絡,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緊密相連。在這個網絡里,禮尚往來、互相關照甚至情感交換都成為不成文的規則,每一次的幫助與回饋,都是對這張網絡的一次加固,每一次的交往與勾結,也可能帶來魚死網破的結局。這種基于情感與利益的交際倫理,是我們生活中的普遍現象,不僅主導了我們的社交行為,更在無形中影響著命運的決策與選擇。因此,在探討小說的敘事倫理線索時,我們不可忽視這一重要的社會因素。
四
歷史倫理、科學倫理、交際倫理三條敘事線索明暗交織,錯綜復雜,顯示了作者強大的駕馭敘事的能力,同時也為我們揭示了當今社會文化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作者是“聽漏人”,此時閱讀這部作品的讀者何嘗不是“聽漏人”?讓我們一起靜心感受這篇小說給我們提供的深刻的思考空間。
一種思考是青銅時代求“德”的歷史倫理在今天是否還有遺存?圍繞著青銅禮器,“僭越”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高頻詞匯。“九鼎八簋”和“九鼎七簋”是否“僭越”?部分考古研究者對古代器物不敬是否“僭越”?盜墓挖掘古代墓葬是否“僭越”?文物被倒賣和送禮是否“僭越”?今人對先祖的規矩制度不屑一顧是否“僭越”?這些疑問,實際上觸及了歷史倫理在現代社會的延續與反思。在青銅時代,禮器不僅僅是物質文化的象征,更是社會秩序、等級制度和道德規范的載體。時至今日,雖然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份對傳統的尊重與敬畏之心,卻不應完全消失。這些行為在某種意義上,都觸及了某種“僭越”的邊界——對歷史和文化的輕視與褻瀆。
小說中所揭示的那些細節都在提醒現代人要有敬畏之心,甚至用受到詛咒和懲罰而走背運的描寫來試圖恢復我們的恭敬之心。小說中的敘事處理,雖帶有超自然的色彩,卻深刻地傳達了這樣一種警示: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都應當保持對過往的敬畏、對文化的尊重、對規則的遵守。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未來負責的表現。因為,唯有在尊重與敬畏中,我們才能更好地吸取教訓和智慧,將其融入現代社會的道德建設中,讓每個人都成為歷史的守護者、文化的傳承者、規則的遵循者。如此,我們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共同構建一個更加文明、和諧的世界。
另一種思考是考古專業求“真”的知識品格是否得到我們的尊重?小說創作過程中,作者對周老爺子的學問、曾本之的專業和馬躍之的能力都有一些“傾向性”的寫作,這是作者試圖高揚的倫理品格,主要是因為在今天的社會特別是浮躁的文化研究圈子中過于“稀少”而顯得尤為珍貴。在學術研究領域,人們往往忙于追求名利、地位,卻忽視了最基本的專業能力。課題研究也好,會長職務也罷,都是大家追求的“晉身之階”,考古過程可能因為迎合某種理論或觀點而扭曲事實,上級決策也可能因為個人喜好或利益而偏離公正。這些現象無疑是對“求真”品格的漠視和侵蝕。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并尊重考古專業的“求真”品格。它不僅是考古工作者的職業操守,更是社會文化傳承的基石。當我們看到小說中那些對業務專家、埋頭苦干者的贊美時,實際上是在呼喚一個更加純粹、更加真實的人文環境。我們需要的是,無論是在小說創作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都能保持對“求真”品格的敬畏之心。在學術研究中,我們應當摒棄浮躁的心態,專注于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以嚴謹的態度去追求真理。在考古工作中,更要堅守原則,不受任何理論或觀點的影響,只忠于歷史事實,還原真相,這種品格不僅是對歷史負責,更是對未來負責。
還有一種思考是人情社會求“利”的交際倫理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夠減少一些?相對于前兩種倫理類型,交際倫理更加復雜、多元,它觸及了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觀以及個人行為方式的多個層面。傳統的人情社會,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和相互幫助,而“利”的交換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在現代社會中,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和法律法規的健全,人們開始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和效率,這使得“利”的交換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更為透明和規范化。
雖然在小說中,同樣存在著利益交換、情感介入的情況,但畢竟不是主流,特別是對于幾代專家的文物研究來說,無論是政策支持、經費撥付還是人員配備,都得到了大力保障,馬躍之“九鼎七簋”的課題在研究過程中也沒有太大的工作阻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可以說人情社會求“利”的交際倫理在日常生活中確實有所減少。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過分依賴人情關系來獲取利益,而是更多地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實力來爭取機會和資源,即使鄭雄在內心渴望通過課題達到他進步的目的,但他在馬躍之面前仍然信誓旦旦地表示大力支持其研究工作。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人情社會在現代社會中的持續影響。雖然“利”的交換方式發生了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系和相互幫助仍然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是這種種利益關系,像小說中的陸永林、梅玉帛、曾聽長這幾位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人物也不會遇到一起。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人情社會求“利”的交際倫理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減少了一些。相反,我們應該看到這種變化背后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并努力在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同時,促進社會的公平競爭和良性發展。
五
在深入探討了劉醒龍《聽漏》小說創作中的敘事倫理后,我們不難發現,這部作品不僅是一部楚文化考古題材的文學佳作,更深刻反映了人性、歷史與現實交織的倫理關系。劉醒龍以獨特的敘事手法,將人物的命運、文化的傳承以及歷史的演變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激發讀者對于倫理道德問題的深入思考和自我反思。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并沒有簡單地給出對或錯的答案,而是將各種倫理困境和道德選擇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在跟隨故事情節發展的過程中,自行思考、判斷并作出選擇。這種開放性的敘事方式,不僅增強了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更促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在求“德”的歷史倫理、求“真”的科學倫理和求“利”的交際倫理面前,我們又會呈現出哪一種面相?抑或都存在于我們自身?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劉醒龍.聽漏[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4.
[2] 論語[M].賈豐臻,選注.劉藝,校訂.武漢:崇文書局,2014.
[3] 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馬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責任編輯" 夏"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