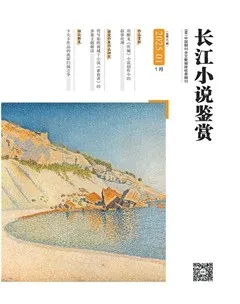論汪曾祺短篇小說中的兒童書寫
[摘要]兒童作為現代化進程中被發現和建構的文化概念,自“五四”始就被作家們納入文本當中,參與塑造著特定時期童年文化的整體面貌。縱觀汪曾祺的創作生涯,從早期“街上的孩子”到20世紀80年代詩意綿綿的少男少女,兒童一直是其關注和表現的對象,被其賦予豐富的文化內涵。汪曾祺的兒童書寫,通常從自身童年中攝取直接的敘述資源,以“寂寞”和“溫暖”作為書寫兒童的主要基調,既包含了對鄉村烏托邦的浪漫描繪,也展現了對成長夢魘的深刻反思,在平凡中見真摯,以文字落成一個充滿童真童趣和人性美的世界。
[關鍵詞]汪曾祺" "兒童書寫" "童年經驗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1-0109-04
汪曾祺從進入西南聯大讀書起開始創作,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擱筆。總覽其小說創作,書寫兒童、講述兒童故事主要集中在創作中后期。汪曾祺筆下的兒童形象并不多,但每一個兒童形象均被作者賦予獨特魅力,體現了作者對兒童情感的深入體察,對兒童生活的詩意表現,對兒童天真的贊揚歌頌。
一、蕩漾在筆端的童年敘事資源
“童年經驗,指的是一個人在童年(包括從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經歷中所獲得的心理體驗的總和,包括童年時的各種感受、印象、記憶、情感、知識、意志等”[1],汪曾祺是擅于將童年經驗浸潤在作品中的作家,記憶的復寫是他創作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汪曾祺少年時期離開高郵后并未回鄉久居,但他仍然不斷地從故鄉和童年的記憶中攝取敘事資源,故鄉的民間風情、市井生活是他作品中最常見的背景,也奠定了其獨具風格的寫作基調。正如他自己所說,寫小說“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說”[2]。
汪曾祺的兒童書寫,往往直接或間接取材于童年的生活經歷。1920年春,汪曾祺出生于江蘇高郵一個舊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勛是清朝末科的“拔貢”,父親汪菊生是當地有名的畫家。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從小就展現出對文藝的興趣和文學天賦。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談到自己的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家庭氛圍溫暖和諧。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汪曾祺的童年無疑是自在的,是美的。美好的童年塑造了汪曾祺,使他常懷一雙抒情的眼光打量世界,并著意將生活譜寫成一曲溫暖的人間小調。于是,童年自然而然成為他最直接的敘事資源,始于童年的人生經驗不斷在其筆端延續。
《晚飯花自序》中,汪曾祺強調,李小龍就是上初中時的自己:
我就像李小龍一樣,喜歡隨處留連,東張西望。我所寫的人物都像王玉英一樣,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畫。這些畫幅吸引著我,使我對生活產生興趣,使我的心柔軟而充實。而當我所傾心的畫中人遭到命運的不公平的簸弄時,我也像李小龍那樣覺得很氣憤。[3]
《曇花、鶴和鬼火》寫的是中學生李小龍的放學路,實際上可以算作汪曾祺對高郵的“回憶路”。全篇沒有連貫的故事情節,視點散漫。文字隨著李小龍的腳步走走停停,越塘、菜地、傅公橋、貞節牌坊……李小龍養曇花,在放學的路上遇見一只鶴——這令他很難忘,“世界上的任何詩人都找不到李小龍的那只鶴”,在小說的最后,李小龍看見了鬼火,又長大了一歲。小說的敘述散漫閑逸,讀者甚至無法從中歸納出一個完整的故事,跟隨李小龍的目光,一幅存在于作家腦海中的故鄉高郵圖景徐徐鋪陳展開,借助李小龍的足跡,作家得以回顧故鄉的一草一木。從這個意義上,這篇小說中的李小龍同樣是作家自己,李小龍的所見所感,皆是汪曾祺在高郵足跡的再現。
1962年出版的《看水》,實際上是一篇指涉作家精神成長的小說,講述的是在集體勞動體制下果園小工小呂獨自完成“看水”任務的故事。小呂在獨自經歷了“看水”的驚險一夜后,正式成長為能夠在集體勞動中獨當一面的“男子漢”,加入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序列,文本中洋溢的滿是歡快的調子。小說的結尾,小呂躺在葡萄樹下,葡萄和小呂都是鮮嫩清新的,共同享受著社會主義新鮮空氣的滋養。汪曾祺曾明確說:“《看水》那篇東西里的小孩實際上就是我。”顯然,這種自比是指作家與作品中主人公精神上的同步。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汪曾祺剛剛經歷被劃為右派、“摘帽”回京的驚險“變故”,迫切需要證明自己對集體的忠貞,同時也渴望集體的接納。而《看水》即代表著社會主義的少年在集體勞動的訓練下終于成長為可以真正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的一分子,文本背后的深意與作家本人的期待不謀而合。
《看水》中的童年復現傾向于一種精神指涉意義,《晚飯花》和《曇花、鶴和鬼火》中李小龍的日常則是作者將真實童年經驗升格審美化了的文學表達。前者是在表現童年中汲取積極的精神資源,后者則是在書寫童趣中實現對童年情景的再現。
二、成長的夢魘與掙扎
傳遞溫暖、抒寫詩情并非汪曾祺作品唯一的表征,表現生的寂寞在汪曾祺作品中幾乎隨處可見,其對普通人生苦難的深沉悲憫與寫作時冷靜細致的流程描述,還有不做評價的中立態度,織構出“寂寞”的小說基調[4]。在展現鄉村烏托邦的同時,汪曾祺的作品也隱含著對成長的深刻反思和憂慮。兒童的世界雖然純真美好,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不得不面對現實世界的復雜與殘酷。在汪曾祺的筆下,有一類兒童的成長往往伴隨著夢魘般的體驗。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逐漸意識到,這個世界并不完全似他們想象的那般美好,而是充滿挑戰和困難。成長過程中的痛苦與掙扎,構成汪曾祺短篇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黃油烙餅》中,蕭勝的生活伴隨著沉重的悲哀。祖母的逝去和社會環境的殘酷壓抑,構成綿延在蕭勝成長過程中深重的痛苦。緩慢的痛苦可以視作汪曾祺對成長的理解。縱觀汪曾祺的一生,年幼喪母,少年離家外出求學,畢業后因戰爭爆發與家人失去聯系,生活的壓力使得他一度抑郁。成年后歷經磨難,命運一波三折,汪曾祺對成長的理解逐漸增添了許多深刻的元素。作家作品中往往內隱著作家自己的思想,帶有個體生命意識的內隱與表達。例如,20世紀90年代的“衰年變法”對死亡與葬禮描述日益增多,可見汪曾祺垂垂暮年業已積淀與升華的生命感悟[5]。
《虐貓》講述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幾個孩子以虐貓為樂的故事,據201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載,1986年汪曾祺共發表四篇小說,分別為《虐貓》《八月驕陽》《安樂居》和《毋忘我》。前兩篇都以“文革”為背景,控訴“文革”對人、人性、人的成長的毀壞。虐貓中的孩子們之所以樂于殘酷的游戲,一方面來自成人對兒童教育的忽略,另一方面也來自殘酷混亂的時代對兒童的影響。正如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在《兒童教育心理學》中所說,外界環境的影響會沖擊兒童的心理,并直接或間接地塑造了他[6]。由于時代的原因,理性缺席兒童的成長,兒童處于被拋棄和被損害的境地,進而導致小說中悲劇的發生。
《曇花、鶴和鬼火》中的李小龍始終是寂寞的,他一個人走在放學上學的路上,一個人靜靜地在夜晚欣賞曇花。小說的結尾,李小龍在看見鬼火后長大了,孑然而立,成長被描寫得如此自由美好,卻又滲著凄涼——李小龍的成長是一首寂寞的詩。在汪曾祺的小說中,兒童生活常常與成人世界明顯分割開來,兒童處在一個相對純凈的敘事環境中,與外界的喧囂和復雜保持一定的距離。兒童通常懷著一雙溫潤的眼睛打量外面的世界,在“一個人”的觀察與探索中展現對外界的渴望。即便是《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在他們無憂無慮的童真之下,同樣可以發現潛藏在他們生活中的深深孤獨和無奈——明海因為家境窮困不得已剃了頭當和尚,盡管年紀尚幼的明海并不懂當和尚意味著什么,依舊每天無憂無慮,和其他孩子一樣愛玩愛鬧,可如果將明海的經歷放置在成人視角下,可以發現蘊藏在明海生命中的深刻悲哀。明海和小英子之間的自由戀愛,與其說是堅定的彼此選擇,毋寧說是兩個孤獨的孩子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中單純生發出的純凈美好的情愫。作者有意避免對現實進行抽絲剝繭般的描繪,卻無意間使現實的寂寞成為作品中難以被忽略的底色。
作家運用兒童視角寫作是一個不斷回溯童年的過程,80年代的汪曾祺走過了并不輕松的歲月,寫作上脫離了外部意識形態的限制,自然在文本中展露出更多對于成長嚴肅沉重的思考,這是一種建立在深刻底色之上的成長。
三、詩意景觀呈現:兒童與鄉村烏托邦
汪曾祺的短篇小說中,經常構建一個充滿田園牧歌情調的鄉村烏托邦世界。這個世界遠離塵囂,沒有世事的紛擾,充滿純美的人性和人情。通過兒童的視角,鄉村世界顯得更加純凈無邪。如《受戒》中小英子與明海之間的純真情感,沒有世俗的束縛和雜念,展現了人性中最本真、最美好的一面。這種書寫方式,不僅讓讀者感受到一種超脫塵世的寧靜與美好,也寄托了汪曾祺對于理想社會和人性的向往。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嚴格說來分為三個時期。20世紀40年代是他創作的第一個時期,也就是創作前期。這一時期的汪曾祺是帶著其師沈從文的寫作特色和西方意識流的強烈特征出現在文學界的,《復仇》《小學校的鐘聲》《邂逅》等作品,熱衷于追求小說的詩化與散文化。第二個時期是20世紀60年代初,即1961和1962這兩年。1961年,汪曾祺創作了《羊舍一夕——又名: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1962年,創作了《王全》和《看水》。這是作者首次嘗試創作兒童小說,文本中的意識流特征已經不再那么明顯,現實主義的筆法更加鮮明。第三個時期從1979年開始,是其創作的又一個高峰階段,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記事》等。從寫法上看,后兩個時期的創作風格差異不大,可以說,汪曾祺的創作越來越趨于現實,趨于樸素,摒棄此前對于先鋒藝術形式的沉醉轉而向內求索。
創作風格轉變帶來的另一個變化是作家對人性的領悟與表現越來越深刻明晰,甚至可以說,對人性思考的不斷深入成為汪曾祺創作風格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說,他是“中國式人道主義抒情者”,對于歷史和人性,他有著自覺的責任。
在談到自己的創作經歷時汪曾祺曾經回憶:
有一次,我和一個同學,走出西南聯大的校門。門外白楊樹叢里躺著一個人。這是一個壯丁,被隊伍遺棄了。他極端衰弱,就要死了。像奧登《戰時在中國作》里所說的那樣,就要“離開他的將軍和身上的虱子”了。但是他還沒有死,他的頭轉來轉去。我的同學對我說:“你們搞寫作的人,應該對這種事負責任。”我當時說不出什么,只是想起里爾克的一句詩:“他眼睛里有些東西,絕非天空。”
此番話可以作為汪曾祺的創作風格由浪漫向現實轉變的源頭,汪曾祺自己也坦言,“以后我的作品里表現了較多的對人的關懷”[7]。20世紀40年代末擱筆,一直到60年代重新開始創作的汪曾祺,作品風格有了顯著變化。方星霞指出,到了《羊舍一夕》,汪曾祺在創作上做出了一個選擇——平實為主,空靈為賓[8]。
《看水》中,小呂從恐懼“看水”到完成任務,在“看水”的過程中想象自己如何應對狼的出現,直至通過“看水”的經歷悟出“許多事都不像想象起來那么可怕”的道理,這一發展變化就如前文提到小呂最愛看的《水滸傳》中的英雄一樣,他正式通過一次獨特的經歷成長起來,做了“好漢”。小說當然可以解讀為個體如何融入集體、一個少年如何正式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故事,正如陳曉明在《表意的焦慮》中所寫,“在民族—國家的宏大意義占據絕對領導權地位時,作家的寫作總是由時代的總體性意義決定的”[9]。然而細讀文本可發現,小說中一些片段不能不讓人忘記宏大的政治背景:深夜,小呂躺在樹上,望著高高的月亮,心里唱起了情歌。四周安靜如水,蔚藍的天空淵深溫柔,像一塊大水晶。汪曾祺將極度浪漫化的話語置于強調“方向正確”文本中,更增加其故事的傳奇性與浪漫色彩,使讀者心中升騰出最純粹的對于美的感動,顯示出在主流強勢話語的壓制下,作家寫作中依然保留了對于人性美的追求。同樣,《羊舍一夕》中,農場里的四個孩子天真爛漫,既不參與政治斗爭,也不立志于做革命英雄,他們只是為自己的明天快樂或擔憂。作家用“人情”的眼光發現四個農場少年內在的優良品性,全篇摒棄說教,洋溢著生活的情趣,是勞動者人性的自然流露。《羊舍一夕》蘊含的平淡審美內涵,與同時期其他兒童小說如《小兵張嘎》等強調大歷史、強主體的作品不同,這種注重日常的平淡敘事,可以看作是對“十七年文學”宏大敘事的一種反撥。
《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都是14歲左右的兒童,他們之間的情感朦朦朧朧,每天的活動不過是一同洗衣砍柴,但從他們的生活中可以看到一種屬于人的蓬勃向上的健康活力。關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及人性和人道主義的討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構成理論界的核心主題。而《受戒》一經問世,便以一種與眾不同的靈動姿態迅速被文壇捕捉,其遠離政治、回歸純粹,被逐漸推向一種美的經典。小說語言淡雅自然,風格樸素曠達,人物靈動活潑,充滿人性美,充滿兒童原始天真的生命樣態。與《羊舍一夕》相比,《受戒》是一種基于意識形態的成長向人性成長的復歸。
兒童視角是一種敘事策略,一種有意味的話語表達方式。在汪曾祺的作品里,文本中的兒童與現實的兒童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作家習慣于提取兒童生命、生活中最美好純良的部分延展開去,兒童成為抒寫美好的理想符號,與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一起,構成一首首散落在筆端的溫暖的歌。
四、結語
汪曾祺的兒童書寫,不僅展現了一個理想化的鄉村烏托邦世界,也深刻揭示了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夢魘與困境。寂寞與溫暖是汪曾祺的兩種主要創作基調,這兩種風格既反映了作家對過往的沉思,也傳達出作家對未來的希望。汪曾祺寫兒童,除了汲取自身的童年敘事資源以外,還通過不同時代少年的成長歷程反映不同時代的歷史內容,并內隱作家本身在不同時代對社會和人生的不同理解。汪曾祺在《關于作家和創作》中談到,人的生活是復雜的、人性是淵深的,對人的尊重使汪曾祺的兒童書寫交織了“寂寞”與“溫暖”,從而達到表現的真實,成功地描繪出兒童生活的復雜性和不亞于成人生活的深刻。同時,作者時刻保持對藝術詩意的追求,使其筆下的兒童閃耀著詩意的光輝和純粹,凸顯一種獨特的審美意境,構成現當代文學中別具一格的兒童書寫風格。
參考文獻
[1] 童慶炳,程正民.文藝心理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 汪曾祺.橋邊小說三篇后記[M]//陸建華.汪曾祺全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
[3] 汪曾祺.晚飯花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4] 王雅鳴.民間之維:汪曾祺小說創作論[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3.
[5] 阿德勒.兒童教育心理學[M].王童童,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7.
[6]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7] 方星霞.京派的傳承與超越:汪曾祺小說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8] 陳曉明.表意的焦慮:歷史怯魅與當代文學變革[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9] 崔榮.京派作家敘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特約編輯" 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