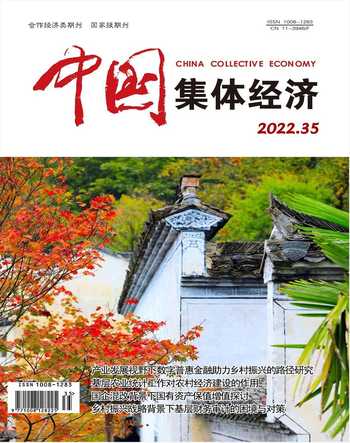媒體企業資產管理的建設與發展
胡曉蕾
摘要:我國的媒體企業在進入21世紀以來,在互聯網技術的變革推動下,無論從業務形態還是企業本身的發展模式都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與刺激,而與之相對應的企業資產觀念與資產管理意識也在發生變化。固守傳統的資產管理觀念,片面強調固定資產的重要性,不符合媒體企業的現實與特性,也無法促進媒體企業的變革與發展。積極進行制度問題和無形資產認識方面的完善,建立健全內控與監督體系,讓企業資產管理的鏈條責權清晰,堵上制度漏洞,強化企業人員對無形資產的認識,積極拓展企業資產優化組合的路徑,才是幫助媒體企業插上高速發展翅膀,進入新世紀媒體企業發展新階段的明智之選。
關鍵詞:媒體企業;資產管理;建設;發展;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信息傳輸水平的提高,將各行各業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水平。而對于越來越多的媒體企業而言,時代進步、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不光是媒體技術的演變與進步,同時,企業發展尤其是資產管理方面的理論與方法也越發成熟,對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水平和衡量標準也在變得越來越高,加強企業資產管理,全面整合企業資產資源,對資源設備進行合理利用和調配,通過企業資產管理的方式,使各種資源得到合理使用,帶來企業整體運營成本的降低,提高企業運轉效率效能。因而,做好媒體企業資產管理的建設與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新時期媒體企業資產管理的現實狀況與發展趨勢
(一)資產管理的信息化為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帶來了極大的便利與促進作用
隨著信息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企業資產管理的自動化水平也是與日俱增,這種情況下,企業資產管理的效率被有效提高,相對應的管理成本也呈現出非常明顯的下降趨勢,這種變化促進了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也為媒體企業的發展與進步提供了充分的財務與管理支持。與過去的資產管理相比,過于繁瑣的資產盤點與登記清算工作被自動化的辦公程序取代,與之相伴的是在各種資產清單與量表方面的易調易用,這都為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和調度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尤其是從資產評估與決策上,提供了各種基于媒體企業發展的可能性的組合方案。同時,對于資產的盤點,也更加方便完成,各種資產內容條目清晰,從形式到實質上做到了賬實相符,有效反映當期企業經營狀態,為及時發現問題并解決提供了料敵先機的保障,進而促進了企業資產的不斷優化,提高了企業資產的回報率,為企業的持續發展與增長提供了巨大的管理支持。
(二)企業無形資產的管理與評估被高度重視,改變了傳統資產管理的方式與格局
不同于傳統企業的資產管理內容與方式,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對象,除了傳統企業的重點管理對象——固定資產之外,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對于無形資產的管理也是企業資產管理業務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固定資產的管理與增值。
無形資產的管理,對于媒體企業而言,是對于企業持續積累以及今后長遠發展所需要高度關注的資產管理內容,是媒體企業在長期的競爭與發展中的神兵利器,無形資產是在同等條件下或者近似條件下,媒體企業之間競爭的主要戰場,也是媒體業務得以再擴大再發展的穩固階梯。因此,無論從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和決策者,還是企業的專業財務人員以及資產管理相關的經營者,都應當具備高度的企業無形資產管理意識,首先從思想格局與高度上就應當具有無形資產管理的敏感性,這樣才能有效避免企業資產的浪費與流失,從而贏得企業在資產管理與升值上的有利一步。
(三)媒體企業的固定資產應當隨著無形資產的變化而變化
媒體企業的產品大都為無形產品,通過將資訊、娛樂和其他各類生活信息、商業信息等傳達給公眾,并以此為企業的產品進而實現企業的價值,那么無形資產也就對應包括了構筑媒體公信力的著力點——媒體名稱、商標以及各種媒體無形產品的使用權、特許經營權等。
與之相伴隨的是無形資產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附著于固定資產之上,但無形資產的變化與成長又主導了固定資產的投入與增長。比如伴隨著媒體技術和互聯網信息技術的變革與進步,能夠服務于媒體企業產品的技術在進步,同時產品本身的進步也帶動了對于技術和硬件設施設備的需求,從而促進了各級媒體企業在固定資產上的投入,為企業的資產積累與進步帶來了無限的動力。因此,對于媒體企業而言,無形資產的變化與發展主導了企業的進步方向,也主導了固定資產的投入與升級。
二、當前媒體企業資產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與媒體企業資產管理趨勢發展相背離的是當前媒體企業仍然存在大量資產管理上的漏洞與問題,從而影響了媒體企業資產管理建設與發展的良性開展。
(一)固定資產管理不規范,從資產減值折舊上存在財務漏洞
媒體企業中的業務開展與企業經營,雖然是資訊和信息的運營與使用,但更為關鍵的是人的參與,尤其是以人為核心的創意思想所主導的業務,才是真正促進企業持續發展的主要業務。然而這一業務的開展不光是人的無形腦力的投入,還離不開專業設施與設備的輔助,兩相結合才能圓滿完成相關產品與業務。但同時也帶來了關于專業設備的資產計算與折舊問題。專業設備的折舊過程不同于桌椅板凳等常規耐用品,專業設備的更新換代與媒體行業的發展息息相關,也與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發展緊密結合,這種技術爆炸式的發展速度,帶來的是專業設備上的技術迭代不可預估,導致了對于專業設備的折舊、減值等工作沒有一以貫之的恒定標準,資產的統計和計算中就會出現數據和信息的不準確。
由于企業的審批手續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存在制度層面的漏洞,對于相應資產的采購存在隨意性,沒有對應的審批與監管伴隨,造成了對于采購進來的資產使用情況不明,發生長期閑置、不能物盡其用的情況。對于一些固定資產的調撥手續不夠健全也會造成資產的使用浪費和流失,比如對于一些固定資產因為登記、維修、報廢等情況的記錄落后不全,導致了賬實不符情況的出現,加之監管人員不到位,權責不分,直接造成了資產管理的混亂。而對于這些情況,如果財務人員仍然按照既有方式進行管理操作,就很容易對資產減值折舊等情況進行精確把握,甚至出現減值與累積折舊混淆處理的情況,進而產生資產管理的財務漏洞與不良影響。
(二)無形資產管理不規范
對于媒體企業無形資產的管理,并非一直就有的經驗和做法,而是近二十多年來,隨著知識產權意識的覺醒以及通過媒體企業無形資產實現增值獲利的情況下,才開始被各大媒體企業逐漸重視起來。但對于媒體企業而言,這種意識的覺醒并不意味著無形資產管理就已經非常成熟到位,相反,受到傳統企業資產管理思想的影響,媒體企業還存在相對看重固定資產的管理思想,缺乏對于無形資產管理的充分認識,品牌保護意識淡薄,對侵權行為和事件的發生不敏感,造成了對企業無形資產保護的不完善,從而導致了無形資產的流失,無法實現有效增值,從宏觀上看也直接影響了媒體企業資產管理與發展的進行。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不只是信息傳輸方式的改變,同時也造成了媒體形式的變革,基于互聯網的技術優勢與特點,各媒體企業在進行相關業務規劃中不可避免地面臨數字化和融媒體建設,開始設置與之相關的各類新媒體業務,實現對自身媒體業務的整合,重新標定品牌形象。當此時機,對于企業無形資產的產權保護應當提上日程,被高度重視,避免出現企業無形資產的浪費與流失,比如對品牌管理的混亂造成企業品牌被亂用,卻無人監管的情況時有發生。
(三)企業內部監督控制體系薄弱
企業資產管理的建設與發展離不開對于內部監督控制體系的建立,在媒體企業這一情況同樣適用。然而,我們在各種媒體企業重組并購以及機構改革的影響下,看到的是在媒體企業不斷變化中,企業內部監督控制體系的被不斷打散重組,然后重新適應重新彌合,這種情況直接致使企業內部監督控制體系出現各種漏洞與缺失。比如在企業收購兼并的過程中,在進行新的管理機制整合下,無形資產的管理與利用往往被忽視,優質的無形資產因為機構的重組被無畏閑置,甚至因為整合后的業務歸屬造成其價值的消耗殆盡而不被重視。這種情況的產生,一方面是企業內部管理監督控制體系本身不健全,另一方面則是內控的開展跟不上企業業務的變革與發展。同樣容易造成企業無形資產流失的另一大缺口則是人員流動造成的,很多無形資產如技術、流程、工藝等,往往掌握在個別的技術人才或者專門人員手中,這些作為企業無形資產的財富在人員跳槽、辭職、轉崗等人事關系變動下,直接造成了無形資產的流失,這是企業在內控機制方面的制度和流程缺陷造成的,也是由于內控體系與企業管理決策不相銜接造成的,應當予以關注和避免。
三、如何加強媒體企業資產管理的建設與發展
(一)優化內部管理機制加強有效管理
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亟待加強建設與發展,應當做好對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有效管理。建立健全資產的采購和審批制度,尤其是對于具有一定技術含量和資金量占用較大的項目做好購建審批的把關,各項資產的投入應當與市場前景、預期收益相聯系,項目負責部門、財務部門以及相關業務部門都應當合理有序地參與到相關審計監督當中,真正做好對于企業資產管理的有效管理與運用。
(二)改進完善資產的會計核算方法
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建設與發展離不開財務部門和財務制度的完善和加強。優化完善企業的會計準則和相關的資產管理制度,使企業的財務工作和稅務工作處于合理合法的情況之下。積極優化資產使用與后續支出的核算問題,有效規避企業的稅務風險。對于企業開展的各類業務與項目,應指定專人進行資產信息的收集與核實,定期進行資產減值的測算,嚴格規避故意混淆資產減值與計提折舊的核算方法。
(三)加強企業的財務人員隊伍建設
媒體企業的財務人員隊伍建設,不能停留于財務專業領域,應當結合媒體企業的行業屬性,做好財務人員專業素質提高的基礎上,強化財務人員對于媒體行業的認知,提高財務人員的綜合素質與業務水平。資產管理非小事,財務人員對于媒體企業的業務認知越深刻,在資產管理過程中,所給出的判斷才能更加切實地符合媒體企業發展的需要,所做的財務報告也才能更加符合企業資產管理和企業發展的需要。因此,對于媒體企業的財務人員隊伍建設,應當積極提高財務人員的職業素養,規范財務人員內部制度與準則,強化財務人員對媒體行業知識的認知與學習,讓財務人員更好地服務于媒體企業的發展,做好相應的資產管理工作。
(四)完善企業內部控制與監督體系
完善的企業內控和監督體系,能夠將企業的決策與發展推向科學有序的決策發展之路,圍繞媒體企業的內控監督,建立一套加強企業法人監督、完善重大項目審批的內控監督制度,從審核流程和監督流程上做好各部門各崗位應盡職責與義務,是杜絕經營者瀆職造成企業資產流失和損失的有效降低企業風險的堅實保障。規范企業資產的審計和管理責任制度,將媒體企業的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的管理工作落實到崗位責任當中,定期開展內部審計工作,強化崗位與崗位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的監督關系,時刻關注媒體企業的資產變化,并將之服務于企業的決策與管理當中。
(五)探索媒體企業資產增值路徑
對媒體企業資產的管理內容與管理辦法進行深刻變革,做好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的運營工作。各大媒體企業本身的固定資產具有極大的開發價值,是媒體企業做好企業運營的基礎,也是進行企業產品開發與創建的依托,利用好企業已有的固定資產,強化市場觀念,將固定資產的價值加以盤活。媒體企業的無形資產管理則應該加強對自身知識產權和品牌形象的保護,積極擴大無形資產向企業效益轉化的路徑,注重相關專利技術的開發與推廣,提高企業內在技術含量與文化價值,為企業提供更加優秀的產品奠定基礎。
四、結語
隨著企業資產管理的信息化不斷推進,媒體企業的資產管理內容與范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信息技術的進步催生了業務內容與業務范圍的不斷擴大,對于資產管理的要求也越來越趨向于結合企業的市場行為與經營需要,改變傳統觀念和認知,努力構建新型的媒體企業資產管理模式,做好相關工作的制度保障和人員保障,充分利用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工具及信息化處理手段,進行企業資產的優化與運營,實現媒體企業的高速發展。
參考文獻:
[1]何適.基于DEVA模型的互聯網媒體企業估值研究——以芒果超媒為例[D].昆明:云南財經大學,2021.
[2]袁欣欣.財務視角下S傳媒集團的融合發展路徑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20.
[3]張世俊.無形資產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分析[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19.
[4]支庭榮.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與焦點問題[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03):6-14.
[5]周結.2019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R].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2019.
(作者單位:石家莊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