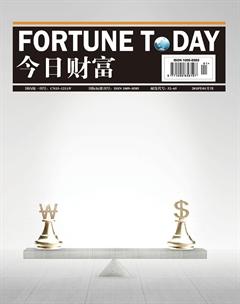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分析
梅淳
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競爭的日漸激烈,全面預算管理體系也逐漸地廣泛應用起來。EVA作為一種新的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綜合評價的指標,能夠更加真實地對企業的經濟效率以及企業自身的能力進行反應。本文對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進行分析,希望可以起到借鑒作用。
企業的全面預算管理體系是一種現代企業必須具有的管理工具,在企業的實際應用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自身所具有的全員性以及戰略性等都是其他管理系統所無法代替的。在經濟和科技都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企業只有不斷的協調自身的發展、增加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夠更好的發展下去,因此相關的工作人員必須要做好對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的相關工作。
一、EVA價值理論體系
(一)EVA的價值驅動因素
EVA是經濟增加值的簡稱,是在對債務資本成本以及權益資本成本進行扣除后的企業的實際利潤。EVA由稅后凈營業利潤(NOPAT)和資本總額(TC)以及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構成。其能夠通過EVA = NOPAT - WACC * TC來對企業的盈利以及企業的績效進行準確的計算。EVA價值管理體系中的4M為評價指標、管理體系和激勵制度以及理念體系,其將EVA價值管理體系中的本質進行了充分的展現,EVA價值管理體系是從企業管理者的角度出發,只有企業的價值發生了增加,EVA才會增加,股東才能夠得到相應的價值回報。
(二) EVA的財務驅動因素和非財務驅動因素
在EVA價值管理體系中,財務報表的數據能夠對其價值驅動因素進行直接的展現,但由于財務指標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指標,更加注重短期內的企業經營效果,這就不能夠將長期的發展以及創造性進行體現,因此要注重財務驅動因素和非財務驅動因素的平衡性,這樣才能夠更好的存進企業的發展。
二、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中的問題
(一)全面預算管理系統中的預算目標沒有價值創造性
在傳統的全面預算管理系統中是不具有戰略引導性的,這就導致相關工作人員進入到“數字游戲”的誤區當中,至注重短期的經濟效益,而忽視了企業的長期發展。在現代的企業發展中,企業最終的目標是創造價值,在很多企業的預算工作中,出現了預算目標變成了橫縱向管理層之間博弈的對象,對資源的分配以及預算的監督管理等工作的重視程度降低,這會造成企業的發展與戰略目標相背離的情況出現。
(二)全面預算管理中角色的定位矮化
在企業中,全面預算管理不但是一種管理方式,更是一種管理的機制,其與每個部門都息息相關。全面預算管理不但能夠根據預算目標來對市場機制和政策機制等對企業的實際要求進行反應,更能夠對企業內部的權利也義務等進行反應。全面預算管理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在企業管理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企業對全面預算管理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將全面預算管理角色定位矮化,這就導致其權威性被降低,預算管理工作中的信息傳達不流暢、管理結構過于松散、與各個部門之間的聯系性較弱,全面預算管理如果不再具有規劃協調、溝通控制等能力,就不再具有應用的價值。
(三)全面預算管理系統中的預算考核與核算協調性差
預算編制和預算執行以及預算考核是全面預算的三個重要關節,這三個環節的實施不但能夠更好的對企業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更是對企業的預算目標的權利和責任的主體進行了確定。利潤和費用等財務指標最為預算編制的核心指標,與核算是息息相關的,在進行全面預算的管理過程當中,要做好對預算結果的分析和考核,讓預算考核與核算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實際的管理過程當中,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例如:預算考核與核算之間的協調性是較差的,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預算彈性與剛性之間的協調性較差,導致預算對外界環境的反應不夠敏捷;預算的管理監督體系不夠合理等等。
三、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的實施
(一)建立完善的基于EVA的企業求全面預算管理系統
企業想要更好的實施全面預算管理就要建立一個健全的管理系統。在管理系統中具有規劃職能和控制職能、協調職能以及評價職能。在企業管理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與每個部門以及環節都是密切相關的,因此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1.職能規劃。企業可以通過預算來對企業未來長期的發展進行預測,“預則立不預則廢”體現在全面預算管理系統當中。相關工作人員通過對預算進行分析,來對企業的戰略目標進行制定,在制定的過程中要注意將戰略目標具體化,符合企業的實際能力。
2.職能控制。職能控制與企業的每一環節都有關聯,同樣也是全面預算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對企業的職能規劃有著重要的影響。企業在進行評估工作的過程中是根據預算編制來進行相關的控制的,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是將創造價值進行反應,需要通過業務層面的動因以及相關的過程進行控制。對于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相關工作人員要對其進行仔細的分析,對責任歸屬進行明確。
3.協調職能。協調職能指的是企業想要達到預期的目標就要每個部門之間共同朝著目標努力。在進行基于EVA的全面預算管理中,要明確各部門的職責,避免因為職責不明而發生沖突,企業要根據全面預算管理來制定出共同的目標,并將企業的資源進行優化并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同時還要注意目標的分解,落實到各個部門中,促進企業各個部門間的協調性,讓企業成為一個整體。
(二)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的設計
企業要制定好其未來發展的計劃以及戰略目標,并將這些計劃轉變成EVA目標,指導企業的全面預算工作的進行。企業可以通過平衡計分方式把企業的流程等與EVA 融為一體。通過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的機制來對EVA進行優化。同時,企業要做好監督管理工作,對企業中各個部門責任進行監督,并將監督檢查結果與目標進行比較,做好反饋的記錄工作,對于其中存在的差異進行分析,這樣才能更好的促進目標的實現。每個部門在接到預算指標后要與EVA指標、與企業的生產供應銷售相結合,根據實際的情況以及自身的職責來進行相關的操作,讓EVA目標能夠進一步的細化。
四、結語
全面預算作為一種有效的管理手段,與傳統的預算不同,更能對企業的綜合管理能力進行體現。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在現代企業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不但能夠為企業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更是能夠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保證企業未來的良好發展。相關工作人員不但要對其進行分析,找出現階段中基于EVA的企業全面預算管理系統中存在的問題,更要做好相應解決的措施,避免問題的出現而對管理造成影響。在進行目標設計的過程當中,必須要與企業自身的實際能力相結合,制定出合理的EVA目標,并做好目標的細化,明確各部門的職能,讓各部門在協調合作的過程中帶動企業的發展。(作者單位為廣東省電信工程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