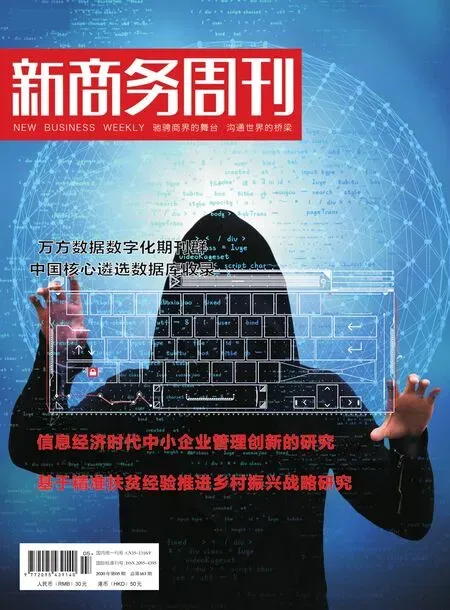結合財務共享系統的會計信息化發展探析
文/段俊鳳,中國石化集團共享服務有限公司東營分公司
1 引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經濟體系逐步趨于完善,企業對于財務會計的管理方式也日益科學。財務共享服務在企業運行中能夠很好的發揮助力作用,幫助企業財務管理、提升企業管理水平,近年來,隨著國內企業財務共享服務的不斷運用,財務會計的信息化管理不斷被更多企業推行,本文筆者就財務共享服務中的會計信息化管理策略進行了詳細闡述。
2 會計信息化在財務共享服務中的有效作用
2.1 優化管理會計信息化。隨著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形勢對于企業的職責要求不斷提高,企業對于會計工作的內容和對會計工作規范的要求也不斷提高,這種變革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化的進程,阻礙企業經濟形勢的發展。但是利用有效的會計信息化的策略可以實現在財務共享服務背景下提高會計信息化管理,有效的解決了上述難題。會計信息化管理步驟從財務數據收集、企業經濟決策和財務管理等過程都能夠運用到財務共享服務系統,一方面在數據收集過程中降低了數據獲取成本,提高了數據收集效率,另一方面提高了信息傳遞效率,加快了會計信息化管理的進程、提升了構建速度。在會計信息化管理進程中,盡管實際操作時會產生一些小問題,但是通過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能夠有效的優化管理方式,盡快滿足會計信息化對財務共享平臺的支持,有利于企業乃至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
2.2 促進企業長期健康發展。制定財務共享服務系統的依據是從企業實際運營的情況,發展符合企業經營發展方向的管理服務平臺。所以,企業運用這項系統能夠快速有效的提升財務管理的效率,降低財務管理成本,有效減少財務相關人員的數據收集整理的工作量,在實際工作中,將原有的數據核對時間更多的分配給了財務管理時間,有利于企業對管理制度的不斷健康發展。
2.3 提高財務會計的整體管理水平。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財務會計方面運用更多的信息技術手段才能滿足不斷發展的經濟要求。而且會計信息化發展還能促進企業新時代下企業對財務管理的要求。通過會計信息化發展,財務人員能力得到提升,不斷提升會計管理能力。同時在財務共享系統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國家財務會計的整體水平提升,符合我國信息化發展的需求。
3 有效實施財務共享服務下管理會計信息化的策略
3.1 完善財務系統。為了更好的完善財務共享服務系統,完成會計管理的信息化,企業應該制定符合企業運營情況的財務共享服務系統管理機制,以保證財務共享系統的健康運用和發展,保證數據的互聯互通。在管理財務共享系統的時候,企業應該參照自身企業運營現狀,將系統真正的運用到自身企業中。比如,運用自身企業的財務業務方式和財務報表的制作過程,這樣不僅能滿足企業對財務管理的要求,而且還能夠提升企業財務部門的業務效率。其次,在財務建設過程中,需要考慮各個方面因素,將財務共享系統集中運用到財務部門的業務和改革創新上,不能將其分散運用。最后,在建立財務共享系統之初,應該得到企業高層關注,將最新的財務信息傳輸到系統上,且在后期最好維護,確保能夠在財務共享系統上能夠查詢到企業最新的財務狀況,各財務部門能夠得到相應的數據標準,讓財務共享系統真正的發揮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的目標。
3.2 提高管理力度,科學發展財務共享系統。健康發展的財務管理系統是建立在科學、安全運營的管理體系和良好的財務和認識調動體系的基礎上的,只有在此之上,才能發展健康、科學的財務共享系統。企業應該關注財務共享系統的運行和發展,確保足夠人力支持和保障,在系統運行過程中避免出現信息孤島的現象,這樣能夠有效提高信息流通和交換的速率,促進會計信息化得到合理運用。另外,為了提高共享系統信息的準確度和時效性,要提高對財務部門的管理力度,確保系統是以企業運行和發展為目標。企業還應該在財務管理制度方面加強管理,不斷完善財務共享系統,推進企業和財務共享系統一體化發展。
3.3 提高財務人員的職業素養。如果要從根本上提高會計信息化發展水晶,那么首要關注的應該是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素養。現今我國多數的財務人員均是會計,簡單的數據核算和監管工作已經遠不能滿足會計信息化發展的需求。所以企業應該增加對人員的職業素養培訓,以緩解日益提高的工作轉型的速度。另外在企業會計招聘時,應該提高對人員綜合素質的門檻要求,如果企業具有一定的先進條件,應該鼓勵企業內員工去高校學習先進的財會方面的知識和財務管理技術。還要針對人員的實際工作情況,建立完善的獎懲制度,提高人員工作的積極性,激發員工會計信息化學習的熱情。
3.4 設定相關的信息安全管理機制。為了滿足企業實際發展和管理需求,當財務管理系統被逐漸運用之后,企業應該制定相應的信息安全管理機制,信息安全要包含所有的財務相關的數據資料。財務會計信息化之后,更多的資料被存儲在計算機之中,信息化提高了企業財務方面的工作效率,但是財務資料信息安全也得到了更大的關注。企業應該針對財務方面的信息進行加密,設定一定的權限,避免財務資料被盜用。構建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方案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管理的效率,而且還能保證企業財務數據的安全,對企業的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4 結束語
綜上所述,由于我國在財務共享信息化發展這方面的工作開始相對較晚,還有很多相關管理制度不夠完善,在實際的運用過程中會有很多的問題出現。隨著國家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相信更多的問題出現以后,結合上文提出的財務共享服務下管理會計信息化的實施策略,希望能夠為未來財務會計信息化發展提供經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