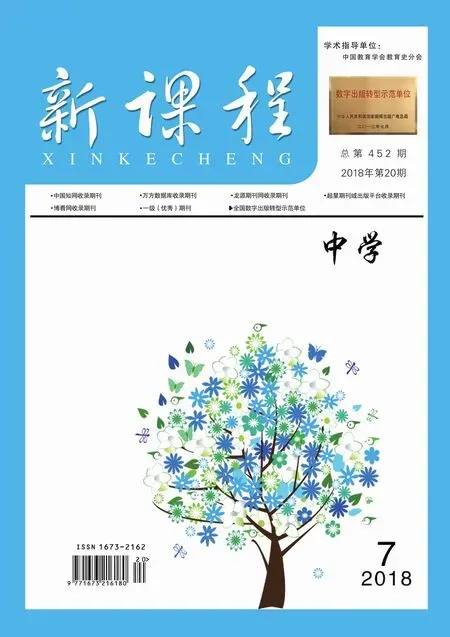淺談新時(shí)代教學(xué)改革對教師的挑戰(zhàn)
謝 冰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qū)新洲中學(xué),廣東 深圳)
《禮記》曾言“日日新,茍日新,又日新。”告誡世人每天都要自新,隨著新時(shí)代的發(fā)展,每天的情況都在改變,教育也是如此,教學(xué)改革需要順應(yīng)時(shí)代的發(fā)展,教育也需要順應(yīng)互聯(lián)網(wǎng)+的趨勢。因而老師也應(yīng)做到及時(shí)跟上發(fā)展的步伐,教學(xué)方法與理念也應(yīng)該及時(shí)更新,而更新中就難免出現(xiàn)諸多問題,如何分析并解決這些問題便成了很多老師想要探求的。
一、教學(xué)改革背景介紹
教育一直隨著經(jīng)濟(jì)不斷地發(fā)展著,從私塾到班級教學(xué),從黑板與粉筆到多媒體技術(shù)逐步應(yīng)用,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已經(jīng)不僅僅局限于課堂課本知識的獲取,微信公眾號、自媒體都為學(xué)生提供了諸多學(xué)習(xí)途徑,越來越多的學(xué)習(xí)軟件如:慕課、微課等網(wǎng)絡(luò)課程應(yīng)運(yùn)而生,里面的課程豐富且全面,老師相對水平也比較高,課程費(fèi)用負(fù)擔(dān)小且學(xué)習(xí)不受時(shí)間地點(diǎn)的限制,所以現(xiàn)在許多學(xué)生選擇依靠網(wǎng)絡(luò)課程學(xué)習(xí)而且呈現(xiàn)出越來越不相信老師、越來越不相信教科書的趨勢。
老師如何在新形勢下與網(wǎng)絡(luò)科技搶學(xué)生,讓學(xué)生相信老師,相信教科書成為困擾許多老師的問題。總的來說,新時(shí)代下老師與教科書面臨的問題如下:(1)老師能否將現(xiàn)實(shí)與教科書結(jié)合起來對教科書中的主要觀念進(jìn)行講解。(2)老師能否順應(yīng)時(shí)代提升技能,將多媒體應(yīng)用與教科書內(nèi)容相輔相成。(3)老師能否擺正心態(tài)正視網(wǎng)絡(luò)課程的優(yōu)點(diǎn)并借鑒。
二、教學(xué)改革對教師的挑戰(zhàn)
1.老師能否將現(xiàn)實(shí)與教科書結(jié)合
教科書編寫與出版的過程,就某種意義來說都是落后的,因而讓教科書與現(xiàn)實(shí)相連接就需要依靠老師的見識與學(xué)識。然而許多傳統(tǒng)觀念下的老師,無法擺脫教科書內(nèi)容的桎梏,不能滿足學(xué)生對新鮮事物的好奇感,從而丟失了課堂的把控力。試想,一位老師不能做到現(xiàn)實(shí)與理論的結(jié)合,勢必難以讓學(xué)生擁有學(xué)習(xí)課程的動(dòng)力,也讓課堂少了許多樂趣,同時(shí)也讓教科書丟失了應(yīng)有的魅力。
2.老師能否順應(yīng)時(shí)代提升技能
雖然多媒體的應(yīng)用已經(jīng)有所普及,但是多數(shù)教師僅僅會(huì)利用網(wǎng)絡(luò)查閱資料、圖片、影像,制作簡單的PPT,卻不具備開發(fā)數(shù)字化教育資源的能力。比如,現(xiàn)階段的數(shù)學(xué)教學(xué)中,許多函數(shù)曲線可以通過電腦軟件精確地畫出,然而目前會(huì)運(yùn)用這些軟件并且將其呈現(xiàn)于課堂的老師并不多。
3.老師能否擺正心態(tài)
新形勢下,網(wǎng)絡(luò)課程確實(shí)擁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點(diǎn),而許多傳統(tǒng)的老師不愿意正視網(wǎng)絡(luò)課程的優(yōu)勢,這樣,既不能鼓勵(lì)學(xué)生拓寬學(xué)習(xí)途徑,也無法讓自己在優(yōu)秀的網(wǎng)絡(luò)課程中學(xué)習(xí)進(jìn)步。
三、教師對教學(xué)改革的應(yīng)對措施
1.老師如何將現(xiàn)實(shí)與教科書相結(jié)合
老師將現(xiàn)實(shí)與教科書相結(jié)合的背后一定是深厚的學(xué)識與對時(shí)事的熱情,首先,學(xué)識是必不可少的,老師需要了解課程背后的真正內(nèi)涵,再加上當(dāng)前的熱點(diǎn)事件才可以幫助學(xué)生理解與充實(shí)課堂樂趣。這樣,既能讓學(xué)生理解課文中對和平的期盼,對人性之惡的批判,又可以讓學(xué)生對課堂內(nèi)容充滿興趣。這樣結(jié)合案例,可以在教科組討論時(shí),每位老師分享自己的看法,從而使每位老師都可以做到現(xiàn)實(shí)與教科書的結(jié)合。
2.如何順應(yīng)時(shí)代提升技能
當(dāng)前老師真正具備開發(fā)數(shù)字化資源的能力是不足的。因而,學(xué)校需要定期為老師們安排學(xué)習(xí)數(shù)字化資源的課程,既要教會(huì)老師們?nèi)绾螒?yīng)用,又要改變老師理念,讓其真正認(rèn)可并接受數(shù)字化資源對于課堂的幫助。此外,老師自身也需要通過看書、上網(wǎng)課、向其他老師學(xué)習(xí)等途徑提升自身技能。
3.如何擺正心態(tài)
網(wǎng)絡(luò)課程不是和老師“搶學(xué)生”,而是幫助老師一起“搶學(xué)生”的,首先,不論網(wǎng)絡(luò)課程如何發(fā)達(dá),學(xué)生的主要學(xué)習(xí)途徑還是班級授課。此外,如果學(xué)生可以真正運(yùn)用網(wǎng)絡(luò)課程、自媒體進(jìn)行學(xué)習(xí),對于老師的班級授課是很有幫助的,而老師需要做的正是指導(dǎo)學(xué)生爭取運(yùn)用網(wǎng)絡(luò)課程與自媒體,比如,老師可以選取優(yōu)秀的課程視頻推薦學(xué)生課下預(yù)習(xí)復(fù)習(xí)時(shí)使用。最后,老師本身也可以通過網(wǎng)絡(luò)課程與自媒體進(jìn)行自我學(xué)習(xí)增長見識。
綜上所述,老師在順應(yīng)時(shí)代變革中,教學(xué)理念與方法的落后是難免的,但是老師需要正視自己存在的問題,能不能將教科書與現(xiàn)實(shí)結(jié)合,有沒有緊跟網(wǎng)絡(luò)科技發(fā)展的步伐,能不能利用網(wǎng)絡(luò)科技幫助完成教學(xué)工作。當(dāng)問題出現(xiàn),就需要老師及時(shí)改變,從而更好地適應(yīng)教育教學(xu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