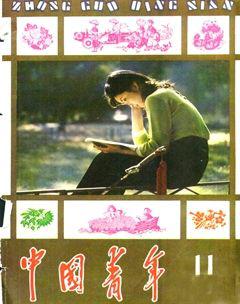不出國的留學經歷
張奔斗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南京大學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共同創辦的教學、研究機構.經過嚴格的考試,我有幸在這里學習了一年,充分感受了一段——
發言不需要舉手
從小學開始,我們接受的一直是“舉手發言”的教育。舉手成了發言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而且,要等到老師提問后才能舉起手。而在南京大學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上課,這一點就行不通了。
為中國學生授課的美國教授多數是第一次面對中國學生。他們對中國學生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們太安靜了,他們聽懂了嗎?可我分明看到一些表情疑惑的臉……”而中國同學之間在課后也常有這樣的對話:“喂,關于某某部分的內容,你聽懂了嗎?”“我也沒聽懂,我看你頻頻點頭,不時沖老師微笑,還以為你聽懂了呢!”
時隔不久,教授們了解到中國學生“上課打斷老師授課是不禮貌”的理論,幾位“不甘寂寞”的教授在課堂上表示:任何一位如遇到聽不懂的地方,請立刻向我提問。請相信你不是這個教室里最笨的人,如果你聽不懂某個問題,一定還會有別人也聽不懂的。你們渴望弄懂我教的東西是對我最大的尊重。
有了這樣的表示,同學們的膽子大了起來,我們或流利或不甚標準的英語在教室里漸漸多起來,而發言也從提問轉向對教師授課內容發表自己的觀點。特別是下半學期,我們仗著英語說得比較“溜”了,有時還就某個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教授呢?這時往往站在角落里笑瞇瞇地看著我們“吵”。在美國教授看來,上課不應是一個單向傳授的過程,而應是一個雙向、甚至多向交流的過程。到了期末,我們這幫原本被評為“過于安靜”的學生被一位教國際關系的教授說成是他“遇到過的思維最活躍的學生”。這話聽得我們很得意,想想這一年來提出過的那么多方方面面的問題和觀點,這些教授留在美國恐怕也沒機會聽到吧! “千萬別忘打引號”
大學4年,大大小小也算寫了不少論文。寫論文的記憶雖然算不上美好,可也不至于痛苦,因為事情來得挺容易:先找出一大堆別人的文章,搜刮出其中精髓,拼拼湊湊,再加上些自己的觀點,便成了一篇自己的論文。有時也會覺得不安,好像自己是頻頻“站在巨人的肩頭”,卻沒告訴老師這些巨人都是些誰。時間一長,這種不安也淡化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古時的秀才不是早就總結過嘛!
可這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就行不通了。“不得抄襲”被寫在中心《教學手冊》的顯著位置,每位美國教授也反復強調:偷竊別人的思想與偷竊別人的財富無異。我們那不茍言笑的歷史教授伸出兩只長長的胳膊,食指和中指作引號狀,聲音冷酷得能結成冰:“當你引用別人的觀點時,請永遠不要忘記打引號,偷竊別人的觀點比偷竊別人的錢更可恥!”
那么,什么情況下該加上那4個小點呢?首先,當你原封不動引用別人文中的話時,請打引號;另外,當你用自己的話敘述別人的觀點時,請打引號:還有當你使用某個學者發明的一個新詞匯時,也要專為這個詞打上引號。那么,何時可以省去引號呢?我們的國際關系教授說:“只有寫諸如《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的作品之類眾所周知的事實時,你才不用打引號。”歷史教授更絕,他的標準是:“當你不清楚某句或某段話是否該打上引號做注釋時,那就說明你該為它打上引號。”
打上引號,就得做注釋:注明引號里的話是誰說的。如果是摘自書籍,就要注明書名、出版社名、出版年代、第幾版、第幾頁;如果摘自報刊,還要注明是哪年哪月的哪份報刊。寫論文時,每位同學都在計算機上小心翼翼地頻繁敲打著雙引號鍵,造成的結果往往是:一篇15頁的論文常常是滿目引號,一般有60到70個注釋,文章末尾還拖著長長的一串參考
書目。引號多得讓我們都不好意思,教授們則很滿意。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引用別人的觀點和闡述自己的觀點并不矛盾,你可以引用別人的話證明自己的理論正確。在這樣的論文里,別人的觀點僅是論據,而論點和論證的過程都是自己的。這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是清楚地說明了這些“巨人”都是誰,無剽竊之嫌;二是要求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而哪些是你的,哪些是“巨人”的,涇渭分明,一目了然。 “坐法”里面有“說法”
在中國大學課堂,有一個普遍現象——學生愛從教室后面往前坐,往往教室的后幾排坐得滿滿的,前幾排卻空空如也。我們把這“遺風”帶到了中心。教授們被我們搞得大惑不解,指著前幾排空座位說:“這里聽得更清楚,為什么不坐在這兒?”我們互相看看,誰也不動。我們需要一個“安全”的位置,尤其是當我們還沒來得及看完教授布置的閱讀材料時。因為按照規律,坐得越靠前,被提問的可能性越大。
可時隔不久,我們就發現,不挪窩不行了。因為在教學大綱上,幾乎每門課的總評成績都有20%取決于課堂表現。想得到好成績,就必須“表現”,想“表現”,就得坐在教室的前面。我們得多提問、多發言,爭取讓教授多多注意我們,坐在前幾排無疑是很有效的方法。再說,教授講得投入時往往越說越快,坐在前面至少也能補救一下我們不太靈光的英語聽力。
隨著越來越多的同學坐位的前移,有人還對此作了哲學思考:愛坐后面是“防守型坐法”,坐在教室前面則顯得更有進攻性。
圖書館的坐法也很有意思。圖書館有兩種座位:一種是大桌子,可供4個人同時使用;一種是用木板隔開的小桌子,坐下來互不干擾。一般都認為美國人講個人主義,中國人信奉集體主義,可從中國同學和美國同學在圖書館的坐法看卻恰恰相反:中國同學喜歡選擇隔開的小桌子,各干各的;美國同學則喜歡坐在一張大桌子上,有良好的學習氛圍,遇到不懂的問題還可以相互討論。不過,如果討論聲音過大,就要受到別人的“注目禮”了。
最后期限沒商量
“最后期限”這個詞在英文里叫“deadline”,“dead”是歹亡之意,“line”是指線、界限。合在一起真是準確至極——過了期限你就死定啦!
在中心,很多事情都有個“dead一line”。中心組織學生外出游玩,每次的出發時間都是鐵板釘釘,不容更改。一次到了開車時間還有同學沒來,帶隊教師手一揮:“開車!”——自己不守時,責任只能由自己承擔。
少玩一次沒什么,有時要是不守時虧可就吃大了。中心的“deadline”要求最嚴的是交論文。每門課的教學大綱上,都寫著論文必須在哪月哪日幾點之前交,有時甚至精確到了半點鐘。準確而冷冰冰的數字里透出的是不容商量的意味。論文晚交了有什么后果?老師根本就不會看,而你這次論文也沒有成績。
我們的經濟學教授,一開始疏忽大意,在論文遞交的最后期限上只注明了哪一天,沒說明是幾點,立刻被我們抓住了機會:“夜里11點59分還應算是那一天啊!”教授愣了一下,立刻笑容滿面地說:“好,那我就那天晚上12點打開我的信箱收你們的論文,在這之后我可不再收你們的論文了。”
中心的機房,10臺IBM計算機24小時開放。每學期未的“論文旺季”,夜里3點機房里坐得滿滿的是常有的事。最緊張時,要一大早爬起來到機房在“計算機預約單”上預約,才能搶到一個機位。機房里經常有這樣的對話:“喂!你在寫哪一篇?”“美國經濟問題,星期五晚上12點前交。你呢?”“我在寫歷史論文,下星期一下午1點上課時交。”“唉,快打字吧……”
“deadline”改掉了我們不少人懶散的性格。想當初在大學寫學年論文,一些同學沒能按時完成,跟導師一說,一般都會獲準拿到暑假去寫,下個學期再交。在中心,可沒這等好事。
意志比聰明更重要
剛進中心時,中方主任的一席話引得臺下女生一片驚呼:“別看你們現在白白凈凈的,一學期下來,臉色可不會有現在這么好了。尤其是女同學,你們會變得很憔悴。”
主任說得沒錯。第一學期心里沒底,除了吃飯、睡覺、上課和少量的聊天外,其余時間幾乎都泡在圖書館和機房。倒不是自己多用功,而是不這樣的話,學習任務就完不成。教授布置的閱讀材料非常多,有時一天要看100多頁密密麻麻的英文原版書。加上很強的專業性,讀起來真是吃力。沒辦法,只有多花時間了。中心流行一種說法:這里1年的學習量,相當于中國的研究生院3年。
最慘的是期末,不僅有考試,還有幾篇大論文。這種情況下,什么樣的作息表都有。我第一學期未有段時間是這么過的:吃過晚飯歇一會兒,從7點開始寫到夜里1點過,吃點東西,再繼續寫到5點多。然后睡到中午12點起床,吃過午飯后繼續寫到下午4點多,鍛煉1小時,洗澡、吃晚飯。這在當時的中國同學中是一種比較流行的作息方法。在萬籟寂靜的夜晚,在桔黃色的臺燈下,孤獨地寫啊寫,似乎永遠寫不到盡頭,“為什么我要跑到這里來”的動搖會乘虛而入。但經歷過的人,都會說:“這一年受下來,以后就沒有吃不了的苦。”
學習已經很緊張了,很多同學還自己“找罪受”。上學期末,因為機房機位緊張,教授說論文不必打印出來。可仍有相當一批同學半夜里去占機位將文章打印了出來,因為這樣干凈、整潔。中心里十分聰明的學生并不多,我甚至覺得還沒有我中學的那個班多,但這樣做事認真、力求完美的人卻不少。我也常常想,一個堅強的意志要比一個聰明的大腦更是成功的必備品吧!尤其是當我們漸漸長大、成熟時,聰明就更不應是我們唯一賴以生存的東西了。 責任編輯:邱四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