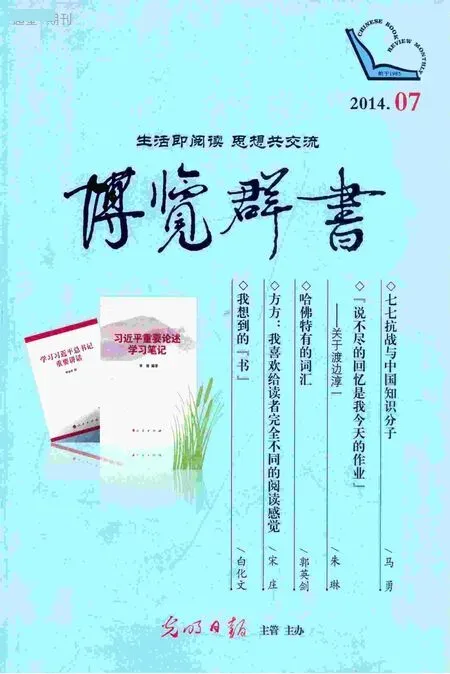學習雷海宗先生的宏觀世界史體系
馬克盎
雷海宗先生學貫中西,匯通古今,在中國史和世界史方面都有許多創見。這里謹就學習他的世界史學定觀體系方面,談一點自己的體會。
雷先生治學宏通博識,注重理論思考,反對煩瑣考證,認為“歷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個人格與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并非專由亂紙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種知識”(雷海宗,《伯倫論學集》,中華書局2002,213頁)。他在世界史學科中很早就反對西歐中心論。1928年,他剛從美國留學歸來,在評論韋爾斯的《世界史綱》時,就能夠指出,醉心世界大同的韋爾斯,其書中有26章是講五六千年來各開化民族的歷史,但其中西洋人就占了16章,達61,5%,其余的10章,作者留給了亞述人、巴比倫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國人、猶太人、回人、蒙古人、日本人去擁擠湊熱鬧(同上書,614頁)。雷先生還指出,這并不是作者看其他一切民族為無足輕重,而只是因為作者并不是一個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他缺乏這方面的高深知識,所以他頭腦中的歷史觀就自然是以西洋史為根據的,于是寫出來的世界史就會是這個樣子了。“書雖名為世界史,實只頭緒錯亂參雜質的西洋史”(同上書,616頁)。雷先生還提醒讀者,韋爾斯是富有改造社會熱情的小說家,而并不是歷史學家,他的這本書,西方的人是把它作為一種消遣品來讀的,而我們如果把它當作出類拔萃的一部世界史入門之作來讀,可能就要發生許多謬誤的認識了。雷先生還特別告誡譯者,在譯書時首先要考慮著作的價值,其次要考慮讀者的資格,然后選擇適當的作品來翻譯。我注意到坊間最近又有韋爾斯的這本書出售,我想雷先生的這些提醒和告誡,在時隔七十余年之后,仍然還是有現實性的。
1936年,雷先生發表“斷代問題和中國史的分期”一文,提出好多精彩的有關世界史的見解。他說西洋有三義,可分為泛義的、廣義的和狹義的,狹義的西洋專指中古以下的歐西,就是波蘭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來又包括新大陸,而東歐并不包括在狹義的西洋范圍內。廣義的西洋,除中古與近代的歐西外,又加上希臘、羅馬的所謂經典文化。泛義的西洋則除希臘、羅馬和歐西外,又添上回教與地下發掘出來的埃及、巴比倫以及新石器時代,甚至再加上歐洲的舊石器時代。這就是通史上的泛義的西洋。但西方人又不愿把希臘以前的各民族歷史泛稱西洋,所以又稱之為古代東方,但雷先生指出,希臘最初的文化起源在小亞細亞,和埃及處在同一條經線上,何以埃及是東而希臘是西;回教盛時,版圖包括西班牙,為何也還是東方;希臘、羅馬文化與歐西文化雖然關系密切,但從民族和文化重心來看,都決不相同;西洋史實際上是由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回教、歐西五個獨立的文化組成。世界上還有印度和中國獨立的文化,它們都有自己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這些表達了雷先生對整個由西方學者所建立的世界史學科體系的深刻思考和不同意見。我們可以不同意雷先生的文化形態史觀,但他的對世界史整體的許多思考都是很有啟發性的,時至今日,在如何建立世界史學科的新體系方面,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新中國成立后,雷先生對世界史學科體系提出更多的寶貴意見。除了人所共知的對上古時代是否存在奴隸社會的意見外,他首先提出了在上古中古時期,亞歐大陸上游牧民族的活動和歷史作用問題,并對之進行了研究。霄先生認為,即使在生產力不發達的上古時期,“世界的發展在很高的程度上仍然是脈絡相通的”(同上書,342頁),而把整個舊大陸連為一體的現成媒介,就是游牧民族,就是公元前1000年以下開始特別活躍的游牧民族。他描繪了這些游牧民族縱橫馳騁的歷史畫面,并總結出三點他們的歷史貢獻:即一,馴馬和騎射法由游牧民族發明并由之傳播于全世界,大大改善了交通;二是上衣下褲這種源自游牧民族的服裝推廣到世界上的廣大地區;三是亞歐大陸東西之間的媒介作用。我們知道,雷海宗先生提出的問題,后來由吳于廑先生作了更大的發揮,寫成“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吳予虛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的著名論文,為我國學界所傳誦。
雷海宗先生還再次談到古代東方是一個錯誤的概念,是十九世紀的歐洲學者對東方的認識太少,創造了這樣把問題簡單化的名稱,或多或少有一種對東方的污蔑意味。他更指出沒有什么東方的土地國有制,土地制度并沒有東、西之分。氏族社會土地自然為氏族公有,所以后來的國家亦即土地國有。如果我們要知道土地國有的例子,最具體的不是“東方”國家,而是中古時代的西歐國家,當時西歐認為土地屬于國王,乃是當然的事。而英國國王曾經實際地行使此權(雷海宗,前引書,386頁)。雷先生能匯通中西,觀察所謂的土地國有制,并且指出了其實西方中古各國乃是最土地國有的國家,這實在是對我們認識世界史上的土地制度的一個很大啟發。當時我國史學界關于中國古代土地是國有制抑或是私有制的討論正如火如荼進行,許多人在如何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上下工夫,而沒有更多地去研究實際的世界史上的情況,雷先生的說法實是對討論的一種很好的幫助。
雷先生否定了奴隸社會在上古時代的普遍性后,進一步提出用生產力的發展來劃分世界上古史,把它分為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兩個階段,并且指出了這兩個階段生產關系的不同。銅器時代土地氏族公有的理論仍然維持,實際制度也與理論相距不遠;而鐵器時代土地可以自由兼并,地主階級和無地少地的農民出現(同上書,395頁)。這一分期法在當時使人有石破天驚的感覺,在今天也還很有啟發性,對我國許多學者關注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三階段論,五階段論,歷史分期等等,在討論中都有參考價值。
,雷先生對世界史體系的真知灼見還有很多,可惜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許多見解都沒有進一步發揮。今天我們紀念他,最好的辦法就是順著他開拓的道路前進,為推進我國世界史學科的進步、發展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