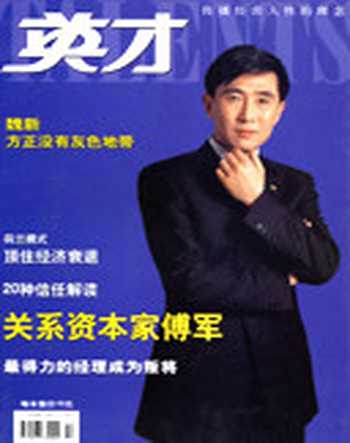信任生產力
趙 加
推選2002年度“10位聚人氣企業家、10位具價值經理人”的活動拉開帷幕之后,我們的視野一直企圖穿透那些勝出者相關的領先指標,以期解讀出可資眾多中國企業參照的基本管理元素。
當我們把這種努力放在肇始自美國的公司丑聞全球聲討與反思語境中,并重新審視近兩三年來發生在中國的有關企業家或者企業主與經理人纏斗的種種案例后,我們發現“信任”實在是無法回避的話題。因為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源于對這一企業存在意義的支撐點的誤讀,并為此付出成本。令人不安的是,這種誤讀不僅有來自企業家角度,有來自經理人角度,還有來自理論界的。
亞當斯密當年曾經斷言,股份公司這種企業形式不可能發展起來,因為董事和經理人們受股東之托代人理財,不可能像業主型企業家們那樣節儉和勤奮。但現代工商企業的發展卻完全否定了這種判斷,甚至出現了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眼中,市場體系已如完美,現在這些大型的企業存在理由是什么?英國經濟學者科斯在對美國的大型工商企業進行深入調查之后,以經典性的論文“企業的性質”回答了這一問題:公司之所以能夠誕生和發展,是因為公司可以通過內部的信任和協調來降低交易成本,當公司付出的交易成本低于市場中同類的交易成本,公司就有了存在的意義。科斯的結論直接指明了“信任”在企業生命中的決定性作用。
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所有者與經營者的信任關系自然是公司內外多維關系中最重要的一環。在我國企業中的諸多所有者與經營者信任關系失敗案例中,所有者誤讀“信任”的癥兆是,一味指責職業經理人職業操守與專業水準,把制度和規則裝在手電筒里,只照別人,對自己沒有任何約束力。而經理人誤讀“信任”的癥兆則是,自以為比所有者懂得規則,喜歡指責對方沒有給足舞臺,自己的業績與利益沒有得到承認。雙方在“情”、“理”這兩個坎上搞不定的話,都認可“法”為最后的解決方案,而中國在“法”上的相對滯后又常使這種訴求成為無頭公案。
而理論界有一種觀點喜歡把中國企業中這種信任危機歸因于傳統的情、理、法思維模式,歸因于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和游戲規則缺位。
如此一來,把信任建立在制度上便成各方接受的惟一方案。從理論上看這樣的邏輯毫無問題,也是未來必然方向。
問題在于,其一,基于制度的信任社會首先出現在美國深刻背景是,18世紀末以來的大規模移民破壞了原來基于身份和基于歷史的信任,并催生了被社會學家稱為負責“信任生產”的行業,比如律師、銀行、會計、證券交易所、信用調查局等等。而中國正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大量流動人口產生的“生人社會”轉化,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尚須長期努力。其二,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同時也存在極大“交易成本”。而美國公司丑聞頻頻出現,也反證規則并不能成為信任的終極解決方案。
顯然等待制度的健全重構信任關系的想法,對當前急欲領跑企業的中國企業家和經理人本身來說并沒有現實的操作意義。如果回歸到“信任”的基本定義上來考察,我們會訝然地發現最節省成本的路就在腳下。
1998年,美國《管理學會評論》在集納了幾個學科權威人士的觀點后,將信任定義為:信任是一種心理狀態。在這種心理狀態下,第一,信任者愿意處于一種脆弱地位,這種地位有可能導致被信任者傷害自己;第二,信任者對被信任者抱有正面期待,認為被信任者不會傷害自己。
實際上,在對外部因素和環境不能改變的同等條件下,從道德層面上解決自身對“信任”的理解與把握,應是企業家與經理人最現實的選擇,因為其中的成本更多地在于自己是可消化的個人克制,局部犧牲,而換取合作,創造更大、更長遠的價值。而且道德傳統也正是我們最具優勢的本土資源,反觀美國從來就沒有道德傳統。它在擁有制度之后,要重新塑造新的道德觀,也是需要花大成本的,但我們卻大可不必。
本次評選最終入圍的獲獎企業家和經理人大都因為付出了更多的信任,或獲得更多的信任,而創造了令人信服價值,并樹立了自己的社會公民形象。
而擁有這樣理念的企業家和經理人,才可能把企業繞過只有業績沒有羞恥的陷阱,一直堅實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