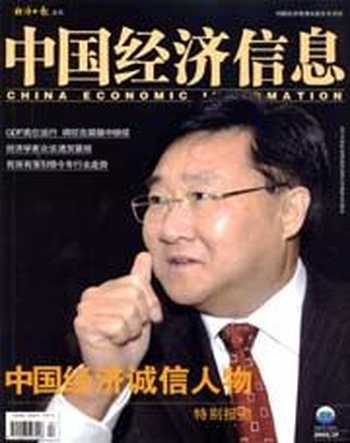土地變革廣東啟幕
10月,新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土地流轉改革已由廣東省首開先河,一份據稱是能掀起全國新一次土地“革命”的法規將在廣東率先實施。廣東省以“政府令”的形式發布的《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下稱《辦法》)規定,農村集體土地將與國有土地一樣,按“同地、同價、同權”的原則納入土地交易市場。
困擾廣東及國內多年的土地緊缺難題可望得到破解。據了解,此份《辦法》是國內第一份對農村建設用地流轉入市具有法律效應的實操性文件,被專家解讀為中國土地政策的新一場“革命”。
土地緊缺得到破解
10月1日之后,受盡“缺土少地”之苦的廣東省將獲得充足的土地“支援”,源源不斷的農村集體土地上市交易將打破這種“缺地困局”。
據了解,廣東新出臺的這一《辦法》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范圍、用途限制、流轉的程序和流轉后的收益及法律責任等問題都作了具體明確的規定。農民不再受“占地”之苦,政府也走出缺地之困。《辦法》使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擁有了合法地位,對農地出讓、出租、轉讓、轉租和抵押等行為都給予了頗具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城鄉統一、以用途管制為中心的土地管理制度首先由廣東破題。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發達地區由于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加劇,在5年內幾乎無地可征。例如蘇州、無錫等地就面臨這種情況,給招商引資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謝揚說。這一矛盾在珠三角地區同樣突出,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上市能解決一部分土地緊缺問題。
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三農專家王利文介紹,在地方招商引資的過程中,這些集體用地由于產權不清晰,也拿不到產權證,土地的“身份不明”使得一些想來投資的外商止步門前,也成了困擾當地政府的一大難題。
有關資料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占全部建設用地總量的50%以上,這些用地的流轉是補充城市用地的一條重要路徑。
地方辦法沖擊國家法律
《辦法》在給廣東帶來諸多“利好”之后,更多的“利空”因素也顯現出來。廣東省的這份地方性規章與國家大法相沖突,這給《辦法》的實行置下障礙。
據了解,《辦法》與《土地管理法》有根本上的沖突。《土地管理法》第63條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法規里也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必須征為國有后才能出讓。
“由于原有的法規對農村建設用地流轉的不可操作性,土地出租、轉讓等流轉行為仍然是隱性地進行。”廣州番禺區政府綜合調研科科長傅銘深說,雖然之前在流轉管理辦法上有條例參考,但都難以操作。《辦法》已生效,廣東省內的各地區都寄予了厚望,但業內人士也擔憂,《辦法》其實與《土地管理法》有沖突的地方,這些沖突今后將如何解決。
廣東省法制辦法規處趙副處長表示,《辦法》與《土地管理法》是有些不大一致,但現在農村土地在放開,實際上各地的農村土地也在流轉。現在政府在進行規范,至今還沒遇到操作沖突。但對于這份《辦法》的法律效用,趙副處長也表示,現在只是政府的規章制度,不是人大的條例。
有關專家表示,一份名為《非農建設用地管理條例》的建議稿今年已經納入全國人大立法程序,具體內容是規范農村非農建設用地流轉的問題。但今年內出臺的可能性非常小。
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地價所所長鄒曉云表示,現在解決“非農建設用地”問題迫切需要建立政策規范,對非農建設用地建立統一的規劃、建設和管理機制。只有在法律法規方面予以完善,非農建設用地才會成為解決土地供需矛盾的一個突破口。各地都在進行土地規劃的修編工作,而土地供求矛盾已經越來越成為發達地區的“心頭之痛”,而本輪土地利用規劃綱要修編也將面臨著保護農地和經濟快速發展之間的矛盾。
“所以廣東省對非農建設用地流轉管理的破題,對于這次修編工作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有專家表示,非農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上市流轉的做法,將有利于盤活農村原有的建設用地。
雖然廣東的做法走在了前面,但鄒曉云也告訴記者,對于國有土地使用權,國務院有明確規定轉讓的條件、轉讓的范圍、轉讓辦法,而對非農集體土地使用權的轉讓至今還沒有一部相關的法規。
“農地入市”為何難在全國施行
1995年前,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一度推行“轉權讓利”政策,規定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1995年后,國家的政策導向發生變化,不再強調必須轉為國有,但也沒有明確應該怎么辦。
到2001年底,全國多數地方仍沿襲“轉權”模式。少數地方另辟蹊徑,探索保留集體土地所有權、允許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新模式。目前能追溯到最早的基層自發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試點,是1995年的江蘇蘇州試點;接著是1997年浙江的湖州市試點,再往后是福建古田、河南安陽。1998年國土資源部成立后,也于2000年3月在安徽蕪湖5個鎮進行試點。
“蕪湖模式”實際上是把農村建設用地流轉與新農村的建設結合起來。當時選擇二三產業發達的鎮建設農民住宅小區,把建設用地置換出來搞工業。這樣的模式由基層政府推動,不是企業和市場自發的交易;雖曾名噪一時,終因流轉方式單一、未能完全按照市場規劃運作而缺乏推廣價值。
相比之下,東南沿海地區的試點由農民和企業進行市場化談判,更具活力和影響力。比如湖州的“農地入市”,主要做法是先進行地價評估,而后再流轉。土地流轉收益在鄉、村兩級進行分配;村級土地的流轉收益要給鄉鎮分成10%,作為對鄉鎮政府轄區基礎設施投入的回報。到2001年4月,湖州市本級約40個鄉鎮中,已有23個進行了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改革。
基層的實踐事實上也獲得了上層的認可。2004年10月28日,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這份高級別的文件,可被視為各地自發進行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流轉試點的“尚方寶劍”。
但是,上有國務院文件,下有持續十年的各地基層試點,“農地入市”的全國性改革措施和法規仍遙遙無期。
稅收政策也是制約因素之一。目前房地產稅屬地方稅種,地方政府為獲取更多稅收,自然傾向于更多地向開發商批租土地,鼓勵房地產開發。征用農民土地成本最低,收益最大,這也是政府不想放棄征地權的一個原因。基層政府的牟利動機與現行財政體制互相作用,實際上阻礙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交易。
此外,農地入市擴大試點也有操作上的障礙。依照現行擔保法,“集體土地使用權不能抵押”,農民和企業都不可能借此獲得銀行貸款。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使用權法律地位不平等,企業為獲得貸款,最后還是傾向于購買國有土地使用權。(范?哲)
小編點評
廣東土改只代表它自己
眾所周知,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土地制度關乎“三農”問題甚至整個經濟體制的根本變革。《辦法》涉及的僅是非農建設用地,對于最為根本的農業土地制度問題,并沒有任何說法;而如果這一問題沒有解決,“新土地革命”的使命就遠不會完成。另外,《辦法》僅僅是從促進非農產業發展的視角解決土地供給的瓶頸問題,在土地供需矛盾有望得到根本緩解的同時,這一“新土地革命”也在失地農戶的可持續發展以及鄉村建設方面留下了重大懸念。
還需要注意到的是,廣東省土地流轉市場化的創新之舉并不一定適合于其他省份和地區。做為經濟發展先行的地區,廣東對土地供給增加的需求是實實在在的,通過現有的非農土地市場的整合,帶來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是必然的;而對于大多數的省份來說,過早的放開建設用地市場可能會導致土地資源利用的混亂。
無論如何,城市化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服務業的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廣東省《辦法》的實施讓我們再次看到了制度變革所可能釋放出的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