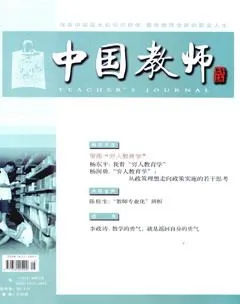從“窮人教育學(xué)”的角度看受教育權(quán)屬性
2007年9月9日,國務(wù)院總理溫家寶來北京師范大學(xué)看望那些剛剛?cè)雽W(xué)的免費(fèi)師范生時,指出:“學(xué)校的大門是向人人敞開的。讓所有貧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學(xué),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權(quán)利,這就是窮人教育學(xué)。”這實際上點出了“窮人教育學(xué)”與受教育權(quán)屬性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即受教育權(quán)所具有的平等與人權(quán)屬性,正是“窮人教育學(xué)”對受教育權(quán)屬性的一種內(nèi)在規(guī)定。
一、“學(xué)校的大門向人人敞開”與受教育權(quán)的平等屬性
“窮人教育學(xué)”的內(nèi)涵之一——學(xué)校的大門向人人敞開,意味著受教育權(quán)的平等屬性,它表現(xiàn)為平等對待所有學(xué)生,使每個人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權(quán)。德沃金在關(guān)于公民受教育權(quán)平等的討論中特別區(qū)分了兩類不同的平等權(quán):“第一類是平等對待的權(quán)利,即機(jī)會、資源或義務(wù)的平等分配的權(quán)利;第二類是作為一個平等的個人而受到平等對待的權(quán)利,即與他人受到同樣的尊重和關(guān)心的權(quán)利。”[1]“平等對待”追求的是分配結(jié)果上的無所差別,即完全平等。所謂完全平等,并不是指絕對的或普遍的平等,而是指入學(xué)和升學(xué)機(jī)會平等,即達(dá)到義務(wù)教育階段入學(xué)年齡的所有兒童,根據(jù)國家或各地市、縣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在入學(xué)機(jī)會等方面應(yīng)該享有平等的權(quán)利。此外還包括受教育待遇的平等,即在義務(wù)教育階段內(nèi),保證所有的學(xué)生接受基本相同的知識、內(nèi)容和年限的教育。
在現(xiàn)代社會,教育不僅具有很強(qiáng)的功利價值——教育被稱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加速器、科學(xué)技術(shù)的孵化器;同時,還具有突出人文內(nèi)涵的非功利價值,即具有促進(jìn)社會平等、保持社會穩(wěn)定的調(diào)節(jié)功能。在存在各種不平等的社會現(xiàn)實中,由于能夠給人提供公平競爭、向上流動的機(jī)會,能夠幫助弱勢者改變其生存狀態(tài)、減少社會性的不公平,教育因而被視為社會平等的“最偉大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的受教育權(quán)平等就是社會公平價值在教育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方式。
然而,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盡管法律早已確認(rèn)了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quán),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人們特別是弱勢群體仍然面臨著受教育機(jī)會的不平等。例如,城鄉(xiāng)之間、男女童之間、不同民族之間、健康兒童與殘疾兒童之間都存在大量的教育機(jī)會不平等的現(xiàn)象。不同地區(qū)之間也存在以教育機(jī)會不平等為特征的教育發(fā)展的不平衡。正如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fā)展委員會在《學(xué)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指出的:“同公平合理完全相反,那些最沒有社會地位的人們往往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權(quán)利——在這方面現(xiàn)在文明過早地引以為榮了。在一個貧窮的社會里,他們首先是被剝奪權(quán)利的人;而在一個富裕的社會里,他們是唯一被剝奪權(quán)利的人。……不管教育有無力量減少它自己領(lǐng)域內(nèi)個人之間和團(tuán)體之間這種不平等的現(xiàn)象,但是,如果要在這方面取得進(jìn)步,它就必須事先采取一種堅定的社會政策,糾正教育資源和力量上分配不公平的狀況。”[2]這說明,教育平等仍然應(yīng)該是我國教育追求的重要價值目標(biāo)。在理論和法律上對于平等受教育權(quán)的確認(rèn)并不等于現(xiàn)實中教育機(jī)會的平等。教育平等是一個具有強(qiáng)烈實踐色彩的概念,它的完整的意義應(yīng)該是指建立在人格平等和政治權(quán)利平等基礎(chǔ)上的受教育權(quán)平等和教育機(jī)會平等。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今天,應(yīng)該承認(rèn),教育資源被最大程度地挖掘出來,教育潛力被最大限度地激發(fā)出來。然而,在多數(shù)人受到教育,并通過教育改變命運(yùn)的同時,卻仍然有一些人享受不到教育發(fā)展的成果。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農(nóng)村。一方面,他們迫切希望接受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改變在經(jīng)濟(jì)上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經(jīng)濟(jì)弱勢,他們又拿不出足夠的經(jīng)費(fèi)來接受相應(yīng)的教育,造成貧困的復(fù)制局面乃至惡性循環(huán)。因此,“教育平等”顯得彌足珍貴、不可或缺,因為教育平等不僅是教育本身的平等,更是實現(xiàn)其他平等,如經(jīng)濟(jì)、文化平等并促進(jìn)其繁榮昌盛的前提。[3]“窮人教育學(xué)”正是將視野投向了最需要關(guān)注的這部分人,所以,受教育權(quán)的憲法屬性首先體現(xiàn)為平等屬性。
二、“所有貧困子女都能上學(xué)”與受教育權(quán)的人權(quán)屬性
“窮人教育學(xué)”站在人的權(quán)利的角度,考察權(quán)利與貧困之間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受教育權(quán)的人權(quán)屬性。
從價值或邏輯分析的角度看,人權(quán)是一種應(yīng)有權(quán)利,是受一定倫理道德支持與認(rèn)可的人應(yīng)當(dāng)享有的各種權(quán)利,即人之為人所應(yīng)享有的道德意義上的權(quán)利。從規(guī)范或?qū)嵶C分析的角度看,人權(quán)是一種法定權(quán)利。人權(quán)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存在才有意義;從社會分析的角度看,人權(quán)是一種實有權(quán)利。經(jīng)驗表明,在許多情況下,問題的關(guān)鍵并非人權(quán)是否得到倫理道德認(rèn)可,也不是人權(quán)能否在紙上得到規(guī)定,而是人權(quán)能否在實際上得到承認(rèn)和保證。只有當(dāng)人們真正地享有權(quán)利時,人權(quán)才是現(xiàn)實的、有意義的權(quán)利。[4]受教育權(quán)的人權(quán)屬性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展開。
受教育權(quán)在法制史上的發(fā)展表明,它具有人權(quán)的特征和相應(yīng)的具體形態(tài)。在原始公社時期,出于人類傳授生產(chǎn)經(jīng)驗和社會生活經(jīng)驗的需要,人類已有了教育活動。這時的教育沒有階級性,主要表現(xiàn)在人人平等地接受一定的教育,此時受教育權(quán)是以道德權(quán)利和義務(wù)——應(yīng)有人權(quán)的形式而存在。在隨后以習(xí)慣法為主要調(diào)整手段的社會里,受教育權(quán)表現(xiàn)為習(xí)慣權(quán)利的形式。到了奴隸社會,“學(xué)校”這種專門從事教育的場所出現(xiàn)了。但這時,學(xué)校教育是奴隸主階級的特權(quán),他們運(yùn)用自己掌握著的國家機(jī)器和法律,將受教育這一權(quán)利規(guī)定為自己這一階級的特權(quán),自此,受教育權(quán)成為法律權(quán)利。此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受教育權(quán)又演變?yōu)楣竦姆ǘɑ緳?quán)利,即法定的人權(quán)。因此,在人權(quán)的意義上,受教育權(quán)是指每個人都應(yīng)當(dāng)享有的權(quán)利,它不僅是一項可要求的權(quán)利,還意味著對個體的尊重和人的價值的體現(xiàn)。作為人權(quán)的受教育權(quán)應(yīng)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其權(quán)利主體是現(xiàn)實生活中具體的“人”,并且應(yīng)該是所有的人,具體到某一國家則是指所有公民。從年齡上劃分,受教育權(quán)主體有幼兒、兒童、成年人、老年人;按性別劃分,有男性公民、女性公民;按身體健康狀況劃分,有健康者、非健康者等。《世界人權(quán)宣言》第2條明確規(guī)定了人權(quán)的基本原則:“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quán)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chǎn)、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qū)別。”《經(jīng)濟(jì)、社會和文化權(quán)利國際公約》認(rèn)為受教育權(quán)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間以及任何條件下都必須加以保障的基本人權(quán)”。《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9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財產(chǎn)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jī)會。”可見,我國至少在法律規(guī)定上實現(xiàn)了每個人的權(quán)利主體地位,這表明法律認(rèn)定受教育權(quán)對于每個人的生存和發(fā)展具有同等的意義。
第二,受教育權(quán)對于每個人而言具有生存權(quán)的意義。隨著人權(quán)內(nèi)涵的不斷拓展,受教育權(quán)將逐漸地由國家賦權(quán)變?yōu)樽晕屹x權(quán)。也就是說,受教育權(quán)不僅是國家或者通過法律賦予的一項外在權(quán)利,更是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需要自我賦予的一種內(nèi)在權(quán)利和需要。受教育權(quán)的實現(xiàn)將是一個公民自我賦權(quán)的過程。
第三,當(dāng)前我國的教育法制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正在努力實現(xiàn)由倫理本位向法律本位、由國家權(quán)力本位向個人權(quán)利本位的轉(zhuǎn)型。作為人權(quán)的受教育權(quán)應(yīng)是權(quán)利本位的,并要求國家履行積極作為義務(wù)的一種權(quán)利,其實現(xiàn)依賴于相對主體義務(wù)的履行。由于受教育首先是對個體發(fā)展而言的,所以現(xiàn)在我們把受教育權(quán)作為一項人權(quán),更應(yīng)強(qiáng)調(diào)其權(quán)利特性。也就是說,作為人權(quán)的受教育權(quán)意味著教育是為了每一個人的需要存在,而不只是為了他人或群體的需要而存在;國家不應(yīng)僅以塑造某種類型的國民為目的來決定甚至強(qiáng)迫人民接受何種教育,父母及教師也不應(yīng)該僅以自己的目的決定孩子應(yīng)該接受什么教育,每個人受教育是建立在充分發(fā)展其人格與各種能力的個別需要上,因而必須以受教育者個人的最大利益為考慮基點,以決定其應(yīng)在何處、以何種方式接受何種教育。這種教育不應(yīng)當(dāng)僅僅是政治或經(jīng)濟(jì)的工具,而應(yīng)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
筆者認(rèn)為,受教育權(quán)可以區(qū)分為形式上和實質(zhì)上的落實與保障。形式上的受教育權(quán)意味著個體獲得了入學(xué)的機(jī)會和資格,這可以通過法律規(guī)定強(qiáng)制實現(xiàn)。而實質(zhì)上的受教育權(quán)則意味教育方式、內(nèi)容等都必須“以人為目的”,通過教育實現(xiàn)個體“健康且文化性的生活”,即人權(quán)意義上的受教育權(quán)蘊(yùn)涵著受一種“真正”的教育。如果說平等屬性可以視為是對受教育權(quán)形式上的保障,那么人權(quán)屬性就是對其實質(zhì)上的保障。長期以來,我國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目中無人”。無論從神化教育還是到物化教育,它們具有一個一脈相傳的邏輯、準(zhǔn)則、思維方式與理念,都在某種程度上呈現(xiàn)出否定與壓抑人性、個性、自主性、主動性的特征。因而,明確受教育權(quán)的人權(quán)屬性具有重大的意義。說到底,受教育權(quán)的人權(quán)屬性就是旨在教育中確立起人的本體地位和人性化的教育觀,真正以每個人的發(fā)展為目的。
總之,從“窮人教育學(xué)”的角度來理解受教育權(quán),應(yīng)具備平等與人權(quán)的基本屬性,這既是受教育權(quán)入憲的權(quán)利來源和理念所在,也是“窮人教育學(xué)”對受教育權(quán)屬性的一種內(nèi)在規(guī)定。
注釋:
[1] 德沃金.認(rèn)真對待權(quán)利[M].信春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300.
[2]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fā)展委員會.學(xué)會生存:沒有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學(xué)出版社,1996:101-102.
[3] 毛建國.窮人教育學(xué)體現(xiàn)教育核心價值理念[N].西安晚報,2007-09-11.
[4] 韓德培.人權(quán)的理論與實踐[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5:356-357.
(作者單位:北京工業(yè)大學(xué)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