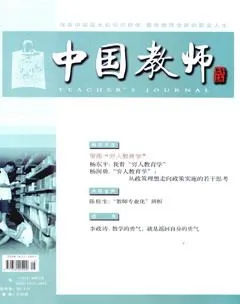教學的勇氣,就是返回自身的勇氣
教學,需要勇氣嗎?這對包括我在內(nèi)的許多教師來說,是一個似乎從未想過的問題。至少對于我而言,教學首先是自身的職責和義務,教學的過程就是履行職責、完成任務的過程。與許多教師一樣,我孜孜以求的是教學的理念,魂牽夢繞的是教學的技藝,而不是什么“教學的勇氣”。要完成一個已經(jīng)機械化的教學過程,我不需勇敢,也無須勇氣。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早有人說過:生活是經(jīng)不起追問的。那些看起來習以為常、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一經(jīng)追問,就漏洞百出,張皇失措了。
美國教師帕克·帕爾默就是這樣的追問者。在《教學勇氣》(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美)帕爾默著,吳國珍等譯)這本書里,他通過對教學勇氣的追問,建立了這樣一個信念:優(yōu)秀教學不能降格為技術(shù),優(yōu)秀教學源自于教師的自我認同和自我完善。這一信念與教師的心靈有關(guān)。很少有人像帕爾默一樣,如此關(guān)注教師的心靈,并以如此的方式進入教師的心靈。因而,有人認為:“這是一本引導教師返回內(nèi)心,走向自我的書,是試圖超越于外在的技術(shù)、技巧,而走向內(nèi)心的書,是一本涉及到教師的靈魂奧秘的書”。帕爾默提醒我們。教學不外乎是人生中的心靈工作,是生命本身的一件樂事,既游離于學科又與學科關(guān)系密切。教學對于教師本人最大的價值在于,教學滋養(yǎng)著他的心靈,“在我所知的任何工作中,教學對心靈最有益。”在他看來,任何一本討論教師的書,都不能不涉及到教師的心靈問題,都應該以某種方式去探索教師的靈魂奧秘。
提到教師,人們常常馬上想到的是教學,是艱辛的勞作,進而聯(lián)想到奉獻精神,僅此而已。似乎“奉獻或犧牲”就是教師全部的靈魂奧秘。在這樣的靈魂世界里,教師的靈魂是圓滿的、完善的,籠罩其上的天空始終是晴空萬里,彩旗飄揚,這樣的靈魂始終流光溢彩。與此同時,教師情感中的焦灼、困惑、迷惘、痛苦等心靈風暴常常遮掩在黑暗里,教師心靈中的軟弱甚至懦弱,常常被視而不見。在以往,教師的勇氣,是朝外的,是面對學生和教學之事的,因而是與自己無關(guān)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教師成長的過程中,常常被教導,要勇敢地面對教學中的困難和失敗,要無懼地面對學生的挑釁,換而言之,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迎接“外部”的挑戰(zhàn),很少有人告訴他們?nèi)绾斡印皟?nèi)在”的挑戰(zhàn),很少有人直截了當?shù)叵喔妫耗阈枰氐阶陨恚阈枰祷貎?nèi)心,直面你的內(nèi)心,透析精神懦弱、心靈浮躁、靈魂無根等種種心靈的缺失,將它們勇敢地挖出來,置于陽光之下,日日揣摩反省。
在教學中,教師之所以常常缺乏勇氣,是因為我們往往把這些困境歸結(jié)為外部環(huán)境,歸結(jié)于學生,但很少歸結(jié)于自身,很少從自我的角度去尋找教學困境的根源。我們?nèi)狈γ鎸ψ晕业挠職猓斪晕沂艽欤庥鰝χ螅⒓创掖颐γΦ乇几巴獠浚瑢ふ铱梢辕焸闹雇此幒桶参縿缓蟀阉鼈兿窀嗨幰粯淤N在創(chuàng)口處,像遮羞布一樣遮擋自己的隱私。殊不知膏藥下的傷口正在持續(xù)地腐爛,遮羞布里的隱私正在發(fā)生隱秘的癌變。帕爾默的意義就在于揭開了靈魂的傷疤,讓丑陋的、腐爛的、觸目驚心的傷口裸露出來。他以充滿激情的理性方式對教師的心靈說了真話,這是一本說真話的大書。種種關(guān)于教師心靈的真話,可以歸結(jié)為一句話:教師具有對自我的恐懼,害怕打破心靈的幻象,害怕看到那個因幻象消失后裸露出的存在著種種缺失的“我”,因此,他缺乏返回自身的勇氣。這句話背后的預設是:教育者首要的任務不是塑造別人,而是重建自身。
僅僅把教師視為“犧牲者”,并不能簡單地視作具有“教學的勇氣”,如果同時犧牲掉的是返回自我、正視自我的勇氣,如果這樣的犧牲是以喪失自我存在的價值為代價,那么,我們可以將其看做是懦弱的犧牲和不道德的犧牲,正如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在《教育——財富蘊藏其中》這份報告中所言:“假如把犧牲性的行為看成是只對別人有意義而對自己毫無意義的行為,這恰恰意味著自己只不過是一件cubT22O7U+WfXloVKk9b1T0TI3GK1H9YBo6XRPpxNg8=工具而不是一個顯示著人的價值的人,如果一個人自身是無價值的,那么他所做的犧牲也就成為無道德價值的貢獻。”
如果教師敢于犧牲自我固有的種種幻象,敢于因承認心靈的缺陷而犧牲對自我的種種預設,敢于犧牲一遇問題就歸結(jié)于外部因素的教學習慣,這樣的犧牲,可以稱之為完美的犧牲和有道德的犧牲,這樣的犧牲,就是一種教學的勇氣。因為,這種犧牲不僅成全了別人,也成全了自己。
對教師而言,教學的價值就是能夠滋養(yǎng)教師的心靈。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學都能達到這樣的目的,不好的教學反而使自我的缺失彌漫擴大,從而變成對自我生命的傷害。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一些因教學而傷害了甚至摧殘了身心的教師。好的教學之所以能夠成全自己,滋養(yǎng)心靈,是因為教師將教學和自身認同、自身完整結(jié)合在一起,他不會只顧埋頭于教學之術(shù),而不顧教學之“我”,不會把外在的“技術(shù)”和內(nèi)在的“自我”割裂開來。真正好的教學來自于教師回到內(nèi)心世界,來自于教師的自身認同與自身完整。在帕爾默看來,就像任何真實的人類活動一樣,教學不論好壞都發(fā)自內(nèi)心世界。教師把自己的靈魂狀態(tài)、所教的學科,以及教師共同生存的方式投射到學生心靈上,教師在教室里體驗到的糾纏不清只不過折射了其內(nèi)心生活中的交錯盤繞。從這個角度說,教學提供通達靈魂的鏡子。如果教師愿意直面靈魂的鏡子,不回避他所看到的,他就有機會獲得自我的知識,而就優(yōu)秀教學而言,認識自我與認識學生和學科是同等重要的。相反,自身的不認同、不清晰和自身的四分五裂,是不好的教學的源頭,是教師不幸的根源。
能夠進行如此好的教學的教師,就是好教師。帕爾默對此不吝筆墨:“好的老師有一共同的特質(zhì):一種把他們個人的自身認同融入工作的強烈意識”,“好的老師則在生活中將自己、教學科目和學生聯(lián)合起來”,“好的老師具有聯(lián)合能力,他們能夠?qū)⒆约骸⑺虒W科和他們的學生編織成復雜的聯(lián)系網(wǎng),以便學生能夠?qū)W會去編織一個他們自己的世界”,“好老師形成的聯(lián)合不在于他們的方法,而在于他們的心靈——人類自身中整合智能、情感、精神和意志的所在”。
歸根到底,好教師擁有豐富的關(guān)于自我的知識。帕爾默深信,作為教師,無論我們獲得哪方面有關(guān)自我的知識,都有益于更好地服務于教學和學術(shù)。優(yōu)秀教師需要自我的知識,這是隱藏在樸實見解中的奧秘。這種奧秘可以解釋教學為什么如此復雜:因為教學的過程,不僅是促進學生學習的過程,也是教師教導自己認識自我的過程。兩個過程如此緊密地縫合在一起,隨著學生的變化和教師的變化,展現(xiàn)出復雜多變的格局。
這意味著,教師在教學中,與之相遇的首先不是學生,不是課程內(nèi)容,而是自我。當教師還不了解自我時,他也不能夠懂得他教的學科,不能夠出神入化地在深層的、個人的意義上吃透學科。這種對自我的知識,不僅在教師從事教學工作的起始階段很重要,對教師發(fā)展過程中的任何一個階段都至關(guān)重要。無論“我”處在教師生涯的什么階段,無論“我”教的學科多么學術(shù)化、專業(yè)化,“我”教的東西都是“我”關(guān)心的東西——“我”關(guān)心的東西就是“我”的自我。這種對自我的關(guān)心,并不意味著對學生的漠視。教學不僅僅是為了守護自己的靈魂,更是為了愛護學生的心靈。如果教師對自我毫不關(guān)心,導致靈魂失守,如何去愛護學生的心靈?
因此,教師愛的力量,首先來自于愛自身的力量。隨著教學生涯的延續(xù),我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這種心靈的力量。我們怎樣才能在教學中把我們的心靈找回,像優(yōu)秀教師那樣,將真心獻給學生?獲得這種力量的首要途徑就是,返回自己的根基,在自己的根基上教學和思考,同時,將教師的根與學生的根相連。這時,教師的心靈就變成了一臺動力強大,心思細密的織布機,“當優(yōu)秀教師把他們和學生與學科結(jié)合在一起編織生活時,那么他們的心靈就是織布機,針線在這里牽引,力在這里繃緊,線梭子在這里轉(zhuǎn)動,從而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精密地編織伸展。毫不奇怪,教學牽動著教師的心,打開教師的心,甚至傷了教師的心——越熱愛教學的老師,可能就越傷心!教學的勇氣就在于有勇氣保持心靈的開放,即使力不從心仍然能夠堅持,那樣,教師、學生和學科才能被編織到學習和生活所需要的共同體結(jié)構(gòu)中。”一旦教師進入到了這樣的共同體中,教師就可能重獲失去的內(nèi)心世界的資源和內(nèi)在的力量。有心靈力量的教師,有完整心靈的老師,才會培育出具有內(nèi)在力量的學生,才會教導學生獲得完整的自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已經(jīng)是或者即將成為教師的任何一個人,都值得看一看這本關(guān)注教師生存意義和心靈缺失的書,都需要將帕爾默的如下一番話作為教學的箴言:
一種優(yōu)秀教學永遠需要的是重獲內(nèi)心世界資源的小徑。記住我們是誰,就是把我們的全部身心放回本位,恢復我們的自身認同和自身完整,重獲我們生活的完整。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