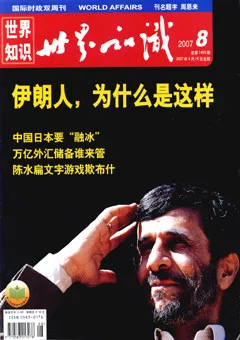中國(guó)日本要“融冰”
目前中日關(guān)系出現(xiàn)的麻煩,是中日間綜合實(shí)力對(duì)比正在發(fā)生歷史性變化所引起的一種反應(yīng)性動(dòng)蕩。一旦新的中日關(guān)系平衡結(jié)構(gòu)確立起來(lái),動(dòng)蕩和麻煩自然會(huì)隨之大幅減少。
中日高層互訪(fǎng)因日本前首相小泉堅(jiān)持參拜靖國(guó)神社,從2001年起一直處于停滯狀態(tài),中日政治關(guān)系也因此徘徊不前。去年日本新首相安倍訪(fǎng)華,完成了他的“破冰之旅”,今年4月中旬溫總理訪(fǎng)日,踏上“融冰之旅”。中日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回暖之勢(shì)。
當(dāng)今世界最冷的一對(duì)大國(guó)關(guān)系
在過(guò)去2000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中,絕大部分時(shí)間兩國(guó)處于友好交往、相互學(xué)習(xí)的狀態(tài)。但近代以后,日本走上對(duì)外侵略擴(kuò)張的道路,中日交惡。特別是1931年始日本發(fā)動(dòng)為時(shí)14年的侵華戰(zhàn)爭(zhēng),兩國(guó)處于完全敵對(duì)狀態(tài)。
1972年9月中日恢復(fù)了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永不再戰(zhàn)”成為雙方共識(shí),官方民間交往空前活躍。雙方領(lǐng)導(dǎo)人定期互訪(fǎng),兩國(guó)貿(mào)易驟增,民間特別是青少年間的交流頻繁。這一時(shí)期也是中日關(guān)系的“蜜月期”。
但冷戰(zhàn)結(jié)束后,中日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新的情況。上世紀(jì)90年代初,日本政治外交出現(xiàn)轉(zhuǎn)型,其直接體現(xiàn)是:對(duì)近百年來(lái)日本的歷史特別是對(duì)其侵略擴(kuò)張史進(jìn)行美化,對(duì)戰(zhàn)敗進(jìn)行翻案;謀求修改和平憲法,為重新武裝掃清障礙;爭(zhēng)取成為安理會(huì)常任理事國(guó),充當(dāng)多極世界中的一極,等等。
這期間,中日關(guān)系也開(kāi)始走向低谷,特別是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臺(tái)以后,兩國(guó)關(guān)系逐步演變成當(dāng)今世界最冷的一對(duì)大國(guó)關(guān)系。
實(shí)力對(duì)比改變后導(dǎo)致的不適應(yīng)癥
關(guān)于中日關(guān)系趨冷的原因,人們經(jīng)常提到的是,日本政要參拜靖國(guó)神社引發(fā)中日歷史觀的沖突;中日共同對(duì)付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需求消失,中日間原有的潛在矛盾逐步顯露;日本“55體制”瓦解后政治右傾化趨勢(shì),等等。但筆者認(rèn)為,這些僅僅是表層原因。深層原因則是,中日間綜合實(shí)力對(duì)比正發(fā)生結(jié)構(gòu)性變化,兩國(guó)戰(zhàn)略關(guān)系正在發(fā)生轉(zhuǎn)變,中日雙方對(duì)這種變化不適應(yīng),在內(nèi)心深處互有被威脅感,從而產(chǎn)生抵觸。

對(duì)日本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的復(fù)興和重新崛起使他們感到恐懼。
在近代史開(kāi)始以前的2000多年間,在亞洲,中國(guó)以其廣袤的國(guó)土、發(fā)達(dá)的經(jīng)濟(jì)、強(qiáng)大的文化感召力成為華夷朝貢體系的宗主國(guó),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許多國(guó)家主動(dòng)吸收中國(guó)的先進(jìn)文化、文物制度和生產(chǎn)技藝,從而使自己獲得長(zhǎng)足發(fā)展。當(dāng)時(shí)誰(shuí)也沒(méi)有感到“中國(guó)威脅”。
近代歷史開(kāi)始以后,在東西兩大國(guó)際體系撞擊中中國(guó)敗北,繼而淪為西方列強(qiáng)的半殖民地。而在這歷史大變局中,日本毅然維新變法,“脫亞入歐”,轉(zhuǎn)身加入西方掠奪者的行列,成為戕害中國(guó)最甚的國(guó)家。第二次大戰(zhàn)中它戰(zhàn)敗了,但旋即卻在集團(tuán)政治的保護(hù)下,通過(guò)發(fā)展經(jīng)濟(jì)恢復(fù)了它亞洲頭號(hào)強(qiáng)國(guó)的地位。
近150年的歷史使日本產(chǎn)生了“亞洲之王”的自負(fù)和舒適感。他們對(duì)歐美強(qiáng)權(quán)勢(shì)力懷著衷心的敬畏和欽佩,對(duì)身邊積貧積弱的亞洲各國(guó),則懷有輕蔑和自負(fù)。如上世紀(jì)80年代,日本一些學(xué)者討論亞洲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時(shí)就設(shè)計(jì)出所謂“雁行式”,把日本視為亞洲的領(lǐng)頭雁。
但90年代初情況開(kāi)始發(fā)生變化。1992年日本泡沫經(jīng)濟(jì)崩潰,而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開(kāi)始高速增長(zhǎng),中日GDP之差距逐年縮小,由開(kāi)始的1︰10縮小到如今的1︰3。到2004年中國(guó)外貿(mào)總量達(dá)1.2萬(wàn)億美元,超過(guò)了以貿(mào)易立國(guó)自稱(chēng)的日本(1.07萬(wàn)億),躍居世界第三位。另外,從相互依存角度看,自1992年到2003年,日本一直是中國(guó)最大貿(mào)易伙伴,但2004年日本下滑到第三位,低于歐盟和美國(guó),日本占中國(guó)進(jìn)口和出口市場(chǎng)的比例都在下降。相反,2001年至2004年日本對(duì)華出口增加70%,日本經(jīng)濟(jì)復(fù)蘇對(duì)中國(guó)的依賴(lài)度大增。
上世紀(jì)50年代,日本乒乓球稱(chēng)雄世界,60年代初中國(guó)取而代之,且至今長(zhǎng)盛不衰;70年代初,日本女排世界第一,中國(guó)曾恭請(qǐng)日本“魔鬼教練”訓(xùn)練中國(guó)隊(duì),到了80年代,中國(guó)女排則獲五連冠。如果說(shuō)在體育項(xiàng)目中的中日位序翻轉(zhuǎn)日本人尚能平靜處之的話(huà),在國(guó)家綜合實(shí)力方面出現(xiàn)的這種變化趨勢(shì),卻使一些日本人坐臥不安,甚至有些恐懼了。在中國(guó)高速發(fā)展面前,一些日本人開(kāi)始失去自信,內(nèi)心深處出現(xiàn)了危機(jī)感和恐懼感,并開(kāi)始向外宣泄。這就是前一階段日本流行“唱衰”中國(guó)、大肆宣揚(yáng)“中國(guó)分裂論”、“中國(guó)崩潰論”、“中國(guó)威脅論”的原因。另外,日本政界人物故意作對(duì)似地一再參拜靖國(guó)神社,否認(rèn)侵略歷史,挑起東海之爭(zhēng),在臺(tái)灣問(wèn)題上大做手腳,制造“安大”、“安納”油氣管道之爭(zhēng),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他們對(duì)歷史發(fā)展大勢(shì)的絕望和反抗。
而從中國(guó)方面來(lái)說(shuō),由于近150年來(lái)中國(guó)受到了太多的侮辱和傷害,這種歷史經(jīng)歷在中國(guó)人心底刻下了太深的傷痕,從而產(chǎn)生了極強(qiáng)的受害者心理。不少人習(xí)慣于用狐疑的眼光觀察世界,對(duì)任何可能的傷害都極為敏感。雖然今日的中國(guó)已不是昨日的中國(guó),今天的世界也不再是昨天的世界,但是,對(duì)許多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仍需時(shí)日才能培養(yǎng)出應(yīng)有的大國(guó)心胸和強(qiáng)國(guó)心態(tài)。
就這樣,中日兩國(guó)開(kāi)始扮演國(guó)際社會(huì)新角色,它們相互不適應(yīng),相互猜疑,甚至是相互恐懼。于是,中日關(guān)系便走入了歷史性的低谷期。
破冰、融冰時(shí)代的到來(lái)
對(duì)于中日關(guān)系的前景,筆者是樂(lè)觀派。理由有以下幾點(diǎn):
一、目前中日關(guān)系出現(xiàn)的麻煩,是中日間綜合實(shí)力對(duì)比正在發(fā)生歷史性變化所引起的一種反應(yīng)性動(dòng)蕩。舊的平衡結(jié)構(gòu)打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我們要以平和的心態(tài)看待之,要以通達(dá)的方式處理之。一旦新的中日關(guān)系平衡結(jié)構(gòu)確立起來(lái),動(dòng)蕩和麻煩自然會(huì)隨之大幅減少。
二、中日兩個(gè)民族都是成熟務(wù)實(shí)的民族,中日是近鄰,地緣關(guān)系決定了誰(shuí)也離不開(kāi)誰(shuí),近年來(lái)日益密切的經(jīng)貿(mào)關(guān)系就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因此,雙方大多數(shù)民眾和政治家都明白,和則兩利,斗則皆輸,尤其是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今天。因此,可以斷言,中日之間的麻煩會(huì)繼續(xù),但動(dòng)蕩是有限度的,不會(huì)發(fā)展到失控的狀態(tài)。但要特別注意不能情緒化,這包括民間的冒失舉動(dòng),也包括有關(guān)職能部門(mén)為化解當(dāng)前過(guò)程性困難而在涉及國(guó)家長(zhǎng)遠(yuǎn)利益方面作出不當(dāng)讓步。
三、在當(dāng)今東亞國(guó)際關(guān)系中最為重要的莫過(guò)于中、日、美三角關(guān)系。有人認(rèn)為,目前美日搞同盟聯(lián)手對(duì)付中國(guó),中國(guó)對(duì)此應(yīng)雙拳出擊,尤其是在臺(tái)灣問(wèn)題上,應(yīng)做好與日美聯(lián)軍作戰(zhàn)的準(zhǔn)備。筆者認(rèn)為這是輕率的無(wú)謀之談。中美、中日關(guān)系在大方向上都是向好的方面發(fā)展,特別是隨著中國(guó)的崛起,中美、中日間的共同利益在迅速增加,而發(fā)生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則越來(lái)越小。
去年10月,安倍首相打破僵局,訪(fǎng)問(wèn)中國(guó),今年4月,溫家寶總理又訪(fǎng)問(wèn)日本。以恢復(fù)領(lǐng)導(dǎo)人互訪(fǎng)為標(biāo)志,中日之間各個(gè)領(lǐng)域里的交流和對(duì)話(huà)迅速增加。去年兩國(guó)恢復(fù)了防務(wù)安全交流,舉行了中日第七次安全磋商;雙方戰(zhàn)略對(duì)話(huà)持續(xù)進(jìn)行;雙方民間人士互訪(fǎng)交流日趨活躍。資料表明,中國(guó)方面在堅(jiān)持中日長(zhǎng)期友好的既定方針的基礎(chǔ)上,在對(duì)日認(rèn)識(shí)的重心方面,已從“促使對(duì)方理解中國(guó)民眾悲情與和平崛起的善意”,轉(zhuǎn)換到與此同時(shí)也“理解對(duì)方戰(zhàn)后以及將來(lái)繼續(xù)走和平國(guó)家之路的心情”。對(duì)此日本新領(lǐng)導(dǎo)人也作出了善意的回應(yīng)。最近,日本方面將兩國(guó)關(guān)系的定位,由一般友鄰關(guān)系轉(zhuǎn)變?yōu)椤皯?zhàn)略性互惠關(guān)系”,日本官員稱(chēng)安倍首相的這一定位是“日本對(duì)華政策新思維”、“預(yù)言日中關(guān)系新時(shí)代的來(lái)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