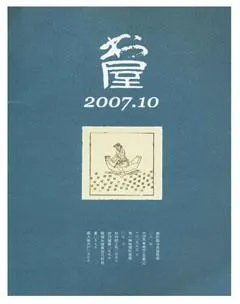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日本真相》(選載之二)
高宗武 著 夏侯敘五 整理 注釋
我記得我第一次所辦的對日具體交涉,比較重要的是對滿洲偽國通郵交涉。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政府封鎖對“滿洲國”的通信事務,塘沽協定后,中日雙方諒解在停戰相當期間內,中日兩國應開始商談關于對“滿洲國”的交通通信事件。當時黃郛任華北五省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這個委員會的成立,可以說是完全對付日本人的。日本在那時候雖然剛拿到東北四省,但第二步就要圈定他在華北的勢力范圍,所以中國政府在華北設立一個大規模的地方機關應付它。那時華北地方事件的外交本來大部分由華北當局就地辦理,當然以黃郛為中心,無奈黃氏所經辦的通車事件,被國民攻擊得體無完膚,因為中國人民十分反對政府當時的撫慰政策,黃郛個人因此也很受攻擊。所以這第二件即與“滿洲國”通郵事,黃郛不肯再經手辦理,請中央派員主持。中央以為過去的關內外通車事件辦得不甚圓滿,政府為此受到輿論攻擊,所以這一次也有意由中央派人負責辦理比較妥當一點,這是他們幾位要人在廬山會議時決定的。
有一天下午大約四點鐘的樣子,我有一位朋友郭心崧君〔1〕來看我,他說:“他們在廬山會議決定,通郵的問題是不能再拖下去了,大家的意思,要請你去主持。這本來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但國家的事總要有人去干的,大家以為你最相適應,所以今天特來征求你的同意,切莫推辭。”我當時對日本的事情雖然相當注意,但對于實際上的與日本交涉,可謂是一年級的學生,一點經驗也沒有,關于郵政的事務,更是一點也不懂,同時這吃力不討好的事我若去干,或者因此送命,也未可知,所以十分猶豫,請他另請高明。郭說:“這是他們在廬山會議秘密決定的,你若不愿意的話,你最好向他們去說。至于郵政事務不懂,并不成問題,郵政局的事務人員你盡可調用好了。實際上我們并不是要你去辦技術事務的。”我答應考慮幾天再回答他。后來我和許多朋友及前輩商量,大家都主張我去干,他們說吃力的事也必須去嘗試一下。我接受了朋友們的意見。
因為當時有一部分輿論的反對,所以這次交涉不能不在秘密中進行。我記得我于1934年9月24日由南京秘密赴北平,當時我和郵局內一位郵務長余君〔2〕以及幾位隨員同去的。政府給我的訓令最重要的一點,是要避免有承認滿洲偽國的嫌疑,換言之,在不承認“滿洲國”的原則之下,與“滿洲國”進行通郵交涉。說起來,這是有點滑稽,一方面說我不承認你,一方面又派人來和你商量通信,只從這兩點上看,這篇文章就不是好作的。在法律上不承認他,在實際上又派人和他商量通信的辦法,這總是有點不好辦。我在接受命令的時候,倒沒有什么,以為總可相機應付,后來一路在火車上靜思默考,總覺得有點想不通,難以自處,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然而命令已經領受了,事體非辦不可,政府有政府的方針,當局有他的苦心,我呢,也有我的犧牲精神。所以火車一到北平,我就不管理論通不通,只求在事實上做得通和事體的整個解決。
到了北平之后,首先去看望華北五省政委會黃委員長。他本來是和我相熟的,我很直率的告訴他,我此來人地生疏,同時于對日交涉毫無經驗,和日本談判,即使是有經驗的人也要上當,請多加幫助和指導。他答道:只要是辦得到的事,一定幫助。對我表示十分的好感和殷勤。
這通郵問題本來可以說是很小的一件事,因為郵政上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重大問題,但是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環境來看,又可以說是很要緊的一件事,因為一旦處置不當,小則事體本身不得解決,大則可影響到整個政府,因為當時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對政府的撫慰政策不諒解,非常反對。我臨行時,當時的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氏再三再四地吩咐我,有事要直接向他請示,關于郵政技術問題,可向交通部和郵政總局商量。日本方面呢?真正負責的是日本駐北平的特務機關長儀我(GiGa)大佐,駐北平副武官柴山中佐,另外是“滿洲國”的郵政司長日本人藤原三人。“滿洲國”本來是中國之一部,因為日本軍事上的占領,成立了一個傀儡國——“滿洲國”,“滿洲國”人就是中國人,這通郵實際上是中國人和中國人內部的事,但為要避免承認“滿洲國”起見,中國人自己避不見面,而偏要和日本人談判,用法律和事實一比較,又想不通,然而世界上想不通的事太多,我想不通也沒辦法。
記得第一次和日方代表見面,是在殷同〔3〕家中。殷同是北寧路局局長,黃郛身邊最重要最紅的紅人。當時中國方面我是主任代表,余翔麟為副代表,殷同、李擇一〔4〕為參與人。日本方面藤原為首席代表,儀我、柴山為參與人(但實權在儀我和柴山手中)。由殷同介紹我和日方代表相見后,日方就拿出他們預備好的許多“通航方案”和“通電方案”、“通郵方案”,一起當面交給我。我拿來一看,都是寫著“滿洲帝國”和中華民國什么什么方案,與殷同事前告訴我的大不相符,于是我就開始說:“本人此次是為辦通郵而來的,所以除了本題之外,關于通航問題、通電問題,并非本人職權之內,本人無權討論,所以關于通郵以外的方案,請帶回去。關于通郵問題,我們在討論之前,要決定兩種原則:一、在不承認滿洲國的原則之下,商討郵政上之技術問題,不作任何有關政治之商討;二、雙方倘意見一致,最后結論不簽字,不調印,以備忘錄方式彼此備案。”這兩項原則,是完全為執行避免承認滿洲偽國的政府訓令而設的,當然是安全之策。但日本方面十分反對,他們說,我們此來并沒有要求你們承認“滿洲國”的意見,但你們一定要寫明白在不承認“滿洲國”的原則之下等字樣,倒不好辦,這是日本所不能忍耐的,日本不愿在這種原則之下和中國辦通郵。關于雙方不簽字,則將來如何對證,彼此也不會有約束力。若是中國堅持非此不可,這通郵問題倒是不必談判好,因為是無法談下去的。日本所謂通信是指郵電合并而言,日本的電報局和郵政局是不分的,這是你們知道的,通郵而不通電報,在日本方面是解釋不通的,所以電報的問題務必一起討論。至于通航問題,若貴代表不在職權之內,可以另作計議。
第一天的商討可以說不但毫無結果,而且馬上發生僵局。但是雙方的態度尚溫和。后來繼續商討了幾天,因為雙方意見不一致,亦毫無結論。而黃郛先生已十分焦急起來,請我回南京去請示,同時要日方代表也返回關東軍所在地請示比較緩和的方案;我則要求日方代表務必先答應我所提的先決條件,我方可回去請示,不然即是回到南京也無用處。后來經過了幾次折沖,日方代表竟答應了。
我回到南京向汪行政院長和朱〔5〕交通部長報告,他們均十分滿意。這時他們給我的訓令是:勿怕決裂。我在南京住了一星期,政府的訓令使我態度更加堅定。
回到北平后,始知日方代表早已由奉天到北平。會議重開,不料雙方代表均聲稱:此番回去請訓的結果和沒有請示以前并無任何不同,不過當時基本原則已經決定,所剩下來的是技術問題,所以比較的尚算好對付一點。
關于技術的急點,最難解決的在郵票本身。中國方面以中國厭惡滿洲偽國,不愿意看見郵票上有“滿洲國”等字樣,要求“滿洲國”制造一種特殊郵票,作為與關內通信之用,這一點可謂是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日方認為不能讓步,中國方面認為非爭不可。此外,中方主張在山海關設立郵電轉遞局,以商用性質來代替中國郵局直接與“滿洲國”郵局來往。但日方堅持直接通郵。雙方爭論達兩個月之久,而仍無結論。
這一次交涉,大概是日本人認為最頭痛的交涉。中途,黃郛、殷同二人希望我多讓一點步,以期早日結束。當時我不肯讓步,我并不是說黃郛不愛國,他是非常愛國的,不過只是我的看法和他有點不同,所以彼此之間時有沖突。代表北平輿論的各大報記者都和我很好,我什么事都告訴他們,他們一點也沒有把我的消息透露出去,而且大家都無條件的作我的顧問。當時華北當局對日不敢說“NO”字,我這樣的堅決,他們非常痛快。
日本人每次與中國交涉,他們的交涉配角,一定是一個人兇一點,一個人緩和一點,這次也是這樣,柴山做好人,儀我做兇人,后來弄得裝好人的柴山也變兇了,他們總是變法地向我威脅,說這通郵交涉若不及時解決,關東軍將認為由中央派來的代表毫無誠意。事態不論如何演變,日本軍人一副可憎面目,天天在我眼中。我則堅持日本若要用兵,那就根本不必與我談,既與我談,則不能引談判以外的話來嚇我。
在決裂了的第三天,我準備回南京去,日方派人來說,大家可以再試談一、二次,以期盡我們做代表的能事。這是他們的要求,我當然接受,因為我并非高調者。后來他們終于讓步,黃郛說是他與殷同從中周旋的,所以日方才肯如此遷就。
未料第四天晚上,我們在北京飯店開會,日方代表完全變更其前緩和的口調,作出一副可怕的樣子,對我說:我們談判至今已兩個月,所以今天的會議只有Yes或No,用不著再討論,再討論一百年也無用。說畢請我答復。我用很溫和的口調解釋我方的立場后,答說“No”字,彼此遂起立握手而別,表示談判完全決裂。
我們出來之后,黃郛派人來要我馬上到他那兒去,說交涉決裂了,萬一中日關系變壞了,誰負責任?!他責備我少年氣盛。我告訴他,你不必擔心,他們會設法挽回的,而且這個問題馬上解決了,中日問題也不會馬上就好;這個問題弄壞了,也不會壞到什么地方。
當時黃郛先生急得沒有辦法,適逢蔣委員長來北平協和醫院檢查身體。一天早上,他由醫院打電話找我去。我趕到醫院將交涉經過向他報告了一番,他并沒有其他的表示。事后有人告訴我,蔣委員長找你去,是黃郛先生的請求,黃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以為我不聽他的話,所以請委員長來教訓我。后來我在蔣委員長出了醫院之后又去見他一次,委員長也并沒有什么吩咐〔6〕,所以當時有人說黃氏的內交失敗了。
有一天,儀我大佐打電話到我所住的北京飯店來,他說有重要的話要和我單獨談。我當然不能拒絕他來見,所以就說請他馬上來。在我掛了電話不到一刻鐘他就來了。他說這次不是辦外交來的,是他個人作私人拜訪來的。他說他十分愿意和我作長久的朋友,倘是我愿意的話。他說我對日本辦外交態度很強,十分愛國,這是日本軍人最佩服的地方。我表面上也當然說,我愿意和他作長期的朋友,但心中明白他此來必另有用意,因為日本人一舉一動皆不落空的。他接著說,我們現在既然是好朋友,所以一切事不能不關心,不然他就不說了。他說關東軍對我的堅持不讓的態度,一方面固表示敬意,但是另一方面卻十分不滿;表示敬意是日本軍人的精神,表示不滿是日本的政策,因此我今后的處境不但很困難,而且很危險。他說關東軍的計劃,就是他也不能完全知道,例如關東軍從前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計劃,他雖身任張作霖的顧問,而且當天也是和張作霖同車回奉天的,也完全不知道,幸而他坐的位置和張氏相隔頗遠,所以得免于死,否則今天不能和我見面了。所以通郵決裂后關東軍的計劃,他雖完全不知道,同時也無法知道,但是關東軍不會沒有第二步計劃的,請我特別留心。明天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Yolhijirs umetvn)中將由天津來北平,明天晚上在日本大使館請我吃飯,也有重要的話和我談,請我務必出席,態度非常誠懇。說完話他馬上就走了。第二天,梅津果然來北平,我應他之請而赴宴。梅津飯后告訴我說,關于通郵的問題,希望大家早點互相讓步,不然把才好轉過來的中日空氣又變壞了,豈不可惜!他再三地說,他一定會幫我的忙,請我不必過分操心,在他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期內,保險華北沒有問題。他的態度十分親切而客氣。我知道他們前后的找我,是要我讓步,他們大概也研究過我的性格,知道我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要,所以用這一次最有力的最后一次友誼的勸誘,以期達成他們的目的。因為在那里,日本不愿意再用兵,同時也不肯讓步,他們拿梅津司令來和我說好話,以為我總可以就范的。但結果還是按照我們的幾條備忘錄式的雙方不簽字的諒解事項,遂于12月初在北京飯店成立,記得那天我們一直弄到天亮才回來。
第二天上午十時,我們去看黃郛氏,他帶著極不愉快的調子說,這些日本人的變化沒法辦,我們昨天通郵問題剛解決,今天早晨七時儀我、柴山兩人又來說,現在通郵問題已解決,非常之好,剩下來的通電通航問題,請從速開始談判,務期于今年年內解決,以解除世人之懷疑。他們這樣的一刻都不放松,如何得了。我告訴他我們在天亮才回來,那是冬天,最少也當在早晨六時半,大概儀我、柴山兩人和我們握別之后就沒回家,便直接到黃郛那邊去提第二次的要求,這是日本軍人一貫的作風,他不怕麻煩,也不怕難為情,更不顧人家的私生活如何,他只求達到他的目的,手段是他們所不擇的。
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軍人交涉所得的深刻印象。柴山是日本軍人中算是最溫和和最進步的人,柴山如此,其他的人更可想而知了。
注釋:
〔1〕郭心崧,字仲岳,浙江溫州人,為高宗武同鄉好友。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教育部司長、交通部參事等職。時任交通部郵政總局局長。
〔2〕余君,即余翔麟,為此次談判中方副代表。
〔3〕殷同,字桐生。北平淪陷后從逆,任偽華北臨時政務委員兼建設總署督辦。
〔4〕李擇一,名宣韓,早年留學日本。時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滬寧淪陷后投敵,參與組織南京偽維新政府的活動。
〔5〕朱交通部長,即朱家驊。
〔6〕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高宗武給同鄉摯友郭俊禾一信,透露蔣與高談話一節,高信中說:“當時交涉方針,皆由汪直接授弟,黃因弟不肯受他指揮,屢表不滿,竟背后向日方表示,由他接受日方條件如何,日方代表則謂渠非此案代表,無權接受日方條件。時適蔣到協和醫院治牙疾,黃即說動蔣找弟去,由蔣吩咐弟受黃指揮。當時弟深感黃之壓力不在日人之下,乃告蔣云,黃即如此勇于負責,當初何以要求中央派人來主辦此事,他自己辦了算了。今日之事我只能將尊意電汪,汪若同意,我方能辦,因我受汪之命而來也。蔣認為十分合理。第二天汪復電堅持原案,不容變更,并云蔣處由他負責去電說明,請勿為念。弟以汪電示蔣,蔣亦不再作主張。……此皆五十二年前之事也。”顯然,高宗武在其手稿中“為尊者諱”,而隱去了此段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