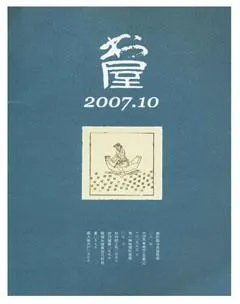封建時代與皇權時代士人效忠對象的差異(外一篇)
本義上的封建時代(如中國的殷周、西歐的中世紀、日本的中世與近世),是領主經濟、貴族政治占優勢的時代,附庸對領主的人身依附是封建社會的一個特色;皇權時代(如中國的秦至清、西歐中世紀末期、日本明治時期)是地主經濟、官僚政治占優勢的時代,人身依附已大為松動。這兩個時代都活躍著一批掌握著知識藝能的士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往往處在貴族、官僚與平民的交界處,“無恒產”卻“有恒心”,即尚未掌握財富與權力,卻有才干與抱負,是一批思想訴求比較明確而執著的人物。略考封建時代與皇權時代士人效忠對象的變化,以昭顯其人身依附性的強勁或松弛,有助于認識這兩個時代的社會性質之異動。
在封建時代,貴族(領主)掌控土地和人民,包括士人在內的人民對貴族有著人身依附關系。以西歐中世紀為例,封建貴族擁有土地所有權和附庸領主權,騎士對上級貴族領主竭誠盡忠,法國作家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等小說,生動描寫路易十三時代(十七世紀上半葉)騎士依附上級貴族領主、為其馳騁疆場、復仇效命的情形。日本江戶時期的武士也與大名領主保有深重的依附關系,不惜以命報主。元祿年間(十八世紀初)發生的“赤穗四十七義士”為主君報仇后全體切腹自殺(所謂“全死節”)的故事,正是日本封建時代武士效忠領主貴族的典型表現。日本有大量文藝作品(如歌舞伎劇目《忠臣藏》等)采用此一題材,以贊頌武士效命主君的精神。
早于中世紀西歐、中世及近世日本將近兩千年,中國封建時代士人的效忠對象,也是有恩于士人的領主貴族。司馬遷《史記》的《刺客列傳》刻畫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等五位春秋戰國間以忠節敢死著稱的武士,其行跡的共通之處是:被某一領主貴族厚待、器重(魯莊公之于曹沫、吳公子光之于專諸、智伯之于豫讓、嚴仲子之于聶政、燕太子丹之于荊軻),武士則為之效力、復仇,不惜殘身以至獻出生命,其信條是“士為知己者死”。
以豫讓為例,他先效力于晉卿范氏、中行氏,兩氏以常規態度接納豫讓,范氏、中行氏滅亡,豫讓投奔晉國六卿之一的智伯,智伯對豫讓“甚尊寵之”。后來智伯被趙襄子滅殺,豫讓發誓為智伯復仇:“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史記·刺客列傳》)為了謀刺智伯的仇家趙襄子,豫讓不惜以漆涂身,裝成癩病;又吞炭致啞,“使形狀不可知”。但在行刺中仍被捕獲,趙襄子質問豫讓:你曾事奉的范氏、中行氏被智伯所滅,你為何不替范氏、中行氏復仇,反而委身智伯。現在智伯已死,你卻不惜一切為智伯復仇,這是何故呢?豫讓答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這番答辭頗能代表封建時代士人的心態:“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士人與效忠對象領主貴族之間達成一種“恩賜—報答”的人身依附關系。這種人身依附關系正是封建時代人際關系的范例,被士子所追慕與信守,也被封建貴族所肯認與贊揚,故險遭豫讓刺殺的趙襄子一再稱賞豫讓為“義人”、“賢人”,并打算開釋豫讓,而豫讓卻決心為智伯盡忠到底,以博取忠臣的“死名之義”,請求趙襄子脫下衣裳,豫讓對衣裳“拔劍三躍而擊之”,象征性地替智伯復仇,然后“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皆為涕泣”。這篇刺客傳,完整地表述了三種人(刺客、被刺貴族、被刺國士人)共通的忠節觀。這種士子以身事奉封建主的忠節觀,正是封建時代流行的一種與人身依附密切相聯的價值觀。上述諸刺客效忠封建主,是一種武士行為,往往以“死節之忠”為最高形態,而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文士有著更復雜的表現。郭店楚簡《魯穆公問于思》一篇,載魯穆公與子思的一段對話:
魯穆公問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成孫弋曰:“……恒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亞聞之矣!”〔1〕
這里肯認的“忠臣”,不以自身的祿爵為目標,而以領主(君)家國的安危作矢的,故經常批評君主的缺點過失。先秦時期的武士與文士都以“取義”為人生高標,而這里的“義”,多體現為對封建領主的效忠。
時至專制一統的皇權時代,士人大體從對某一貴胄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來,具有自由身份,其效忠對象由封建貴族領主,放大為代表國家的帝王及其朝廷(以及為帝王、朝廷服務的官僚)。皇權時代士人的理想是“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竭忠盡智,以事其君”,成為士人的生活目標。秦漢以下專制皇權時代涌現大批為君國鞠躬盡瘁的士人,從漢代蘇武、三國諸葛亮、宋代岳飛,到宋元之際文天祥、明清之際史可法,莫不是精忠報國的典型,其忠節的外在形態與豫讓、荊軻有某些相近之處,其內涵卻發生變化:效忠對象由個別封建貴族轉變為代表專制一統國家的皇帝、朝廷,如梁山第二號人物玉麒麟盧俊義所說:“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
如果將《水滸傳》與《史記·刺客列傳》作比較,即可發現,同為豪強仗義的俠士,皇權時代與封建時代的效忠對象發生了大變化。司馬遷筆下的周末刺客不惜殘身獻命于有恩于己的貴族領主,而施耐庵描繪的宋代好漢,外在張揚的是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內在追求的則是效忠朝廷君王之念,正如元雜劇對宋江綽號“呼保義”的詮釋:“安邦立國稱保義。”
往常把《水滸傳》稱之“農民起義的史詩”,其實,這部小說狀寫的梁山好漢,極少農民出身(“菜園子張青”似乎有種地經歷,但小說中他已經與母夜叉孫二娘在十字坡開夫妻黑店),多為因貪官逼使落魄的吏胥、軍官、富豪、僧道以及流民、無賴;小說也完全沒有接觸農民問題的核心——土地問題。故較確切的說法為:《水滸傳》是一部造反者之歌,狀寫宗法專制社會逼使各色人等逸出體制外,走上“造反”的不歸路,而這些造反者的靈魂人物(如宋江)又執著于“忠君”“報國”之念,力圖重返體制內而不得,終于演出一場大悲劇。就揭示宗法專制的皇權時代造反者的心路歷程而言,《水滸傳》是深刻的,它對廟堂與草莽(朝廷與水滸)兩方面都未加粉飾,直顯其本真面目。而“逼上梁山”與“歸附朝廷”這一組矛盾的交錯運行,構成跌宕起伏情節的主線。對于造反者而言,歸附朝廷君王的途徑便是接受“招安”,一部《水滸傳》,宋江當然是頭號“招安迷”,但《水滸傳》最先言說“招安”的,卻是小說中最富英雄氣概的武松。《水滸傳》第三十二回寫到,武松血濺鴛鴦樓,殺了張都監等一干貪官、犯下彌天大罪之后,與宋江相逢,宋江邀武松同去清風寨,投奔朝廷軍官小李廣花榮,武松不愿連累花榮,決計追隨魯智深、楊志去二龍山落草。武松在與宋江惜別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記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
武松、宋江最后作別時,宋江再次叮囑武松戒酒、保重,其言談的落腳處是: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
這番對話,典型地反映了皇權時代的主流人生觀、價值觀,即使被“宗法—專制”社會邊緣化的體制外人物,也未能脫離此種人生觀、價值觀的軌范。而人們效忠對象從封建領主向帝王朝廷的轉換,昭示了皇權時代與此前封建時代社會形態的差異。
皇帝夢:皇權時代的一種社會心理
白秦始皇稱制“皇帝”,進入“皇權時代”以后,中國便籠罩在“皇權”的陰影之下,換一種說法,中國人便處于“皇權”光焰的強烈照耀之下。各色人等做起白日“皇帝夢”,構成秦至清兩千余年間相當普遍的一種社會心理。這種夢,不可能產生在商、周封建時代(本義上的“封建”),它只屬于秦以下的皇權時代。因而,詮釋“皇帝夢”,解析圍繞“皇權”的社會心理,有助于認識皇權時代的特征,認識皇權時代與封建時代的差異性。
皇帝的無限威權,使許多人自認“順民”、“忠臣”,希冀“好皇帝”君臨天下,致使國泰民安,這可以稱之皇帝夢的一種——“明君夢”。即使一些皇帝并不英明,國不泰、民不安,但人們往往把責任歸之于某一級次官吏的腐敗與枉法,認定皇帝本是好的,只是受了蒙蔽,故深懷冤屈的人,常把平反昭雪、解救危厄的期望寄托在皇恩浩蕩之上(實施者稱之“清官”),故爾“告御狀”成為中國傳統戲曲、小說的一個不朽題材。這種“明君—清官夢”,是一種依戀皇權的夢,可以稱之間接的“皇帝夢”。它不可能發生在商、周封建時代,因為那時的民眾受轄制于某一層級的貴族領主,而與天子并不相干,期望之“夢”做不到天子那里去。反之,皇權時代裁削多層次的封建領主,通過朝廷命官征收賦役、執行詔令,使君權直逼老百姓的種種生活層面,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概莫能外,于是,淳樸而良善的人們只有企望“明君”降世,紛紛做起了“戀皇夢”。
此外,還有一種直接的“皇帝夢”,這是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物試圖取代現存皇朝的夢想。這種民間夢想,也只能產生在專制帝制社會,因為,此前的封建社會,權力來源于宗法世襲與封賜,身處下層等級者無法企望,故商、周千余年間沒有發生過農夫起義,只有貴族革命(所謂順天應人的“湯武革命”)和諸侯兼并戰爭(所謂殺人盈野的“爭城之戰”、“爭地之戰”),偶爾發生“國人暴動”,驅逐君王,但取代者仍然是宗法貴胄。至戰國初,宗法制松弛,卿大夫取代、瓜分公室屢屢發生,震撼力最大的是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順應此種時勢,禪讓古制被請出來作說辭。二十世紀末葉出土的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學者考證,可能作于分晉代齊之際)盛贊禪讓,其文曰:“唐虞之道,禪而不專”,“禪而不專,圣之盛也”。這大約是將戰國初年分晉、代齊歸于禪讓,從而肯認權力轉讓的合法性,所謂“愛親故孝,尊賢故禪”,“禪,義之至也”〔2〕。稍后,燕國禪讓失敗,引起兵血之災,質疑禪讓的議論隨之而起。《孟子·萬章》載,孟子否定堯舜禪讓的實存性;《荀子·正論》載,荀子稱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后之論者,更有直指禪讓的虛構性,認為往古有的只是權力的武裝爭奪。筆者以為,氏族制時代存在著原始民主,首領推舉與強力爭奪并存(現代人類學家在原始部落的調查證明此點),《尚書》所載禪讓制,是對其做了理想化表述,透露出某種“史影”,不能視作全然虛構。至于后人對禪讓制的品評與取舍,則取決于評論者的時代訴求。
總的說來,宗法封建時代權力的分封與禪讓,都披掛著神圣、神秘的外衣,而進入皇權時代,權力雖然繼續被神圣化、神秘化,但權力世俗化是無可遮掩的歷史走勢。皇權時代呈現的實態是:權力,包括最高權力——皇權,大都來自武力爭奪,不僅貴族、官僚,如東漢末的袁紹、袁術、孫堅、曹操,隋末的李淵,后周末的趙匡胤,紛紛參與奪權,有的終于“皇袍加身”,連喪失傳宗接代功能的宦官,如明英宗時的太監曹吉祥也覬覦皇位。更有最底層者,如農夫陳涉、流氓劉邦、沒落貴族項羽、私鹽販黃巢、托缽僧朱元璋、漁家陳友諒、驛卒李自成、邊兵張獻忠、落第秀才洪秀全,借助某種際會風云,揭竿而起,成為皇權的有力追逐者,都曾稱王作帝。“中原逐鹿”這一則成語道破了個中奧妙。《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齊人蒯通的名論: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這里的“鹿”,比喻政權、皇位,并非一定由世襲貴胄去爭奪,那些才能高、動作快的下層人士也有機會得到它。僅就秦末言之,這種逐鹿的“高材疾足者”絕非個別。
《史記·陳涉世家》載,賤為農夫的陳涉一次在勞動間隙,有感于自己的貧賤和統治者的富貴之間的巨大懸殊,向一起耕作的農夫發慨嘆:“茍富貴,無相忘。”聽者認為是妄想,大不以為然,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這里所謂的“鴻鵠之志”,即富貴之志,而“富貴”的極峰便是當皇帝。陳涉起事以后,爭做王侯的意念更趨明確,他在動員造反者時高喚:
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陳涉毫不含糊地向權力世襲的貴族政治提出挑戰,起事后自立為將軍,隨即稱王,號“張楚”(意謂張大楚國)。這在實行貴族政治的封建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在整個商、周千余年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此類庶眾起而稱王的事件,西周末期的國人暴動,是無法忍受厲王虐政的國人驅逐暴君,國人并無取代之意,接替王位的仍是周王室中人:至于晚周的“犯上作亂”,不過是貴族的逾級僭越,如魯國大夫季氏的“八佾舞于庭”之類,最嚴重的事態是下級貴族瓜分公室,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然政權仍是在貴胄間重新分配。而在皇權時代,卻屢屢發生農夫造反、平民稱王,最高統治權被天下人競相爭奪。秦末陳涉首次以平民身份爭奪王侯以后,奪取王侯之位被認為是世人的共同嗜好,甚至被釋為“圣人”的念頭。《金史·辛愿傳》稱:
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
這里的“圣人”,只能視作皇權時代的“圣人”,此前處于封建時代末期的孔圣人、孟亞圣從未流露過稱王作侯的打算,他們把自己定位在王者之師。而到了皇權時代,民間已經相當普遍地做起“皇帝夢”,《西游記》中的孫行者說得很直白:“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陳涉攫取王侯之位的想法并非特例,與其共時代的同志,清清楚楚載之正史的便有劉邦、項羽兩位,而且這兩位當皇帝的愿望更為明確。
《史記·高祖本紀》對早年身處底層的劉邦的思想活動有所載記: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夫,大丈夫當如此也!”
《史記·項羽本紀》記身為楚國舊貴族的少年項羽與叔父項梁看到出巡的秦始皇的盛大車隊,欽羨其威風,頓生取代之念。文曰: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項梁為侄兒項羽“取而代之”的狂語萬分驚懼,因其有可能引來滅族之禍,但項梁內心卻對項羽稱奇贊嘆。太史公的神來之筆,將皇權時代庶眾的皇帝夢昭顯得頗有層次、極為真實可信。
元人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卷一稱:
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有七,項籍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
劉邦、項羽因傾慕皇帝的尊貴而產生的“彼可取而代也”的夢想,是許多改朝換代之際的勇敢分子的共同野心。此類心理的生成機制,除皇帝無上尊榮所產生的誘惑外,更與皇權時代權位獲得與更替的原動力有關:統治權并非如封建時代那樣仰賴宗法遺傳,而是當社會矛盾白熱化之際,由某一強力集團的代表人物憑借暴力爭奪得來。
秦以降的專制帝王雖然也盡力給自己的得位涂抹上神學色彩(“真龍天子”、“奉天承運”之類),但鋌而走險的叛逆者并不信服此種說辭,他們不相信現任皇帝一定是“真龍天子”,卻從歷史真實中歸納出“彼可取而代之”、“強者為王”的法則。《水滸傳》中的李逵口口聲聲喚著:“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晁蓋哥哥當“大宋皇帝”,宋江哥哥當“小宋皇帝”,心存接受招安之念的宋江雖一再制止黑旋風,但在眾多梁山好漢看來,李逵這番話也頗為中聽,這大約是那個“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夢想在眾頭領心靈深處起著作用。
專制帝王試圖用宗法制度和宗法觀念抬舉一姓之尊,提升皇族的神圣性,但此法只能行之于一個朝代之內,如劉氏之尊,可行之于兩漢,為宗室劉秀的中興漢室、劉備的建立蜀漢發揮重要作用,但延及魏、晉,曹氏、司馬氏相繼而起,劉氏則喪失感召力,“正統”也隨之轉變。李唐、趙宋、朱明、愛新覺羅清皆同此例。總之,在皇權時代,中國的皇帝固然贏得某種神學光環和宗法論證,是至高無上的尊崇對象,但大體而言又是一種世俗的、可以爭奪的目標。民眾并不無條件地崇拜它,在某些時刻完全可以棄之如敝屣,直至取而代之。這與日本的天皇制頗不相同,天皇被日本人普遍視為天照人神的嫡子,是不可直視的神,更不可想象去奪取其位。在千余年間,日本的天皇是一系承傳的,唯獨發生過一次平將門自稱天皇的事件,很快便被討平。而且,平將門也是天皇后裔,自認有得位的天神身份。與日本形成比照的是,在缺乏宗教情懷、宗法制又已變態的中國皇權時代,皇位在本質上是世俗的,是權力斗爭的產物,是強橫者彼此奪占的第一把交椅。富于冒險精神的人們,在某些特定時段(多半是一個朝代發生統治危機的關口)不惜以命拼爭皇位,結果無非是兩種:“勝者王侯,敗者寇”,王侯與寇賊的區別僅在成功與失敗。
如前所述,皇權時代還有另一種間接的“皇帝夢”,即期盼好皇帝給社會帶來統一、平和、繁榮,給個人提供升遷發達的光明前景。這是皇權時代常態下許多人的夢想,梁山好漢中史進、林沖、武松等武藝高強的人物,也曾企求“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后來終于被黑暗政治(運作者總稱“貪官”)“逼上梁山”,并對現行皇帝失卻希望,拒絕招安。而梁山好漢的主持者宋江、盧俊義等人,則始終對現行皇帝心存幻想,孜孜以求于朝廷的招撫,走著“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一部《水滸傳》狀寫的造反者,主流確乎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金圣嘆點評曰,《水滸傳》起首,“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而宋江們所“反”的,僅僅是“自上作亂”的高俅們,對重用高俅的徽宗皇帝卻寄予無限期待。與項羽、李逵們“彼可取而代之”的“皇帝夢”相較,宋江、盧俊義們的“招安夢”,豪氣大失,而奴氣十足,故人們往往欣賞項羽、李逵式的富于英雄主義色彩的“皇帝夢”,而鄙棄宋江、盧俊義們的接受皇帝招安的夢想。從審美角度論之,這一好一惡似有道理,但從歷史價值判斷之,兩種夢想實出一轍,都覆蓋在“皇權”的大纛之下。皇權時代的人群,絕大多數都是皇權主義者,區別只是人們做著兩種類型的夢:一種是在現行皇帝之下的夢,企圖從現行皇權那里分得一杯羹:另一種是取而代之,自做皇帝的夢。兩種都是“皇帝夢”,全都脫不出皇權主義的軌跡。
我們在商、周封建時代找不到這兩類做夢者,卻在秦漢以下列朝處處遇見這樣的做夢者,這種夢想演繹了兩千多年,直至近代,由于出現了新的社會土壤,皇帝夢才漸漸幻滅,不過其影響不可低估。孫中山多次警告革命者,不得有皇帝思想;他還一再舉太平天國洪、楊內訌之例,指出“那種失敗,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直到革命掀起民主共和風濤,孫中山呼喚:“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此一1906年發表的讜論,昭示著共和時代的來臨;而1911年清帝遜位,標志著皇權時代的歷史冊頁從總體上已經翻過,當然,皇帝夢的感應力還遠未蕩盡。
注釋:
〔1〕〔2〕轉引自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2~2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