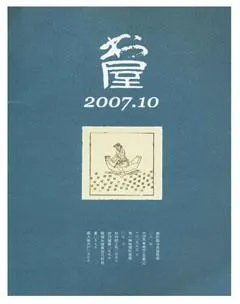鹽水女神、廩君及其變形記
我七歲的時(shí)候,是1972年。與絕大多數(shù)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樣,在緊巴巴的日子里摘取屬于自己的樂(lè)趣。父親是鹽業(yè)鉆井的技術(shù)人員,常年出差,奔波于井場(chǎng)與鹽廠之間。我放假后,他被我纏得實(shí)在沒(méi)法,只好就把我?guī)希谒拇喜亢蜄|部起伏的山嶺間,從一個(gè)井場(chǎng)遷徙到另一座鹽灶。我記不清楚都去了些什么地方,但濃郁的鹵氣總是伴隨記憶,伴隨著水泥車、壓裂車的轟鳴和鉆桿的鐵銹黃油味,這讓我心跳加速。
每到一個(gè)井場(chǎng),我就遍山遍野地瘋跑,跑到噪音和令人發(fā)悶的鹵氣覆蓋之外。我不認(rèn)識(shí)當(dāng)?shù)厝耍捎诳谝舻牟顒e,我說(shuō)的鹽,他們說(shuō)是“銀”,但俚俗間故意把“賣鹽”說(shuō)成“賣淫”。其實(shí),這個(gè)誤差其實(shí)可以理解為鹽是白銀的隱喻。山西作家李銳寫《銀城故事》,就是故鄉(xiāng)自貢的繁華往事。翻開(kāi)西方上古史,也可以發(fā)現(xiàn)相同的隱喻。古羅馬時(shí)代,在通向羅馬城的道路中,最重要的道路是從鹽場(chǎng)到羅馬的大路。最高當(dāng)局派重兵把守大路,嚴(yán)防歹徒盜鹽。那時(shí),守衛(wèi)大路的士兵的收入就是鹽,由此,鹽已具有“薪俸”的意思。后來(lái),鹽巴便演變成為“薪水”一詞。而在古代的自流井,鹽一度也是折合工錢的硬通貨。而始于唐代的“折博”作為食鹽的專賣手段,它與“飛錢”變相結(jié)合為“引鈔”,以及宋代的“鹽鈔”,更是典型的體現(xiàn)了鹽的貨幣功能。
鹽廠一般都坐落在馬蹄形構(gòu)造的山勢(shì)凹陷處,我經(jīng)常爬到可以俯視廠區(qū)的高處,坐在縱橫交錯(cuò)的枧桿上發(fā)呆,看著遠(yuǎn)處從枧桿上空飛過(guò)的黑鳥。枧桿里面發(fā)出怪響,微微顫動(dòng),起伏的彈性讓我聯(lián)想起蹺蹺板,它吱吱嘎嘎地叫,又很像是行進(jìn)的滑竿。多年以后,每當(dāng)聽(tīng)說(shuō)那些瀕臨倒閉的鹽廠四處低價(jià)賣鹽,被人們戲謔地稱為賣淫時(shí),猛然想起,鹽很長(zhǎng)時(shí)間來(lái)就被西方人視為刺激性欲的神秘物品,性力不亞于秘?zé)挼拇核帯?br/> 我經(jīng)常順著那些枧桿走很遠(yuǎn)的路,反正再遠(yuǎn),我總能順著回來(lái),從不擔(dān)心迷失方向。它們像一群奇怪的蛇,肚皮里稀里嘩啦,渾身潮濕,透過(guò)竹篾纏絲不停往外滴水。那是鹵水,像石鐘乳一樣,成為了一根根鹽柱。我隨意掰斷很多,仿佛手握遠(yuǎn)古的奇門兵器,展開(kāi)與空氣的廝殺。有些鹽柱像生鐵,有些則潔白晶瑩,忍不住用舌頭去舔,就發(fā)覺(jué)不但咸,簡(jiǎn)直苦澀而惡心,還有滿口鉆的鐵腥味,就跑到水田邊去喝水,啃一個(gè)生紅薯,仍然沒(méi)有擺脫嘴里的味道。父親后來(lái)警告我,不要去嘗這些鹽柱,因?yàn)闆](méi)有提煉過(guò)的鹵水,雜質(zhì)太多。他告訴我,所謂“苦”,就是古人說(shuō)的“大咸”。
但是,我真正理解“大咸”,卻是在很多年以后。
舊時(shí)四川農(nóng)村把食鹽稱作“上味”。在我會(huì)寫鹽字之前,我已經(jīng)體味到了這種白色的結(jié)晶體是如何“上味”的了。百味之中,鹽是上味。它是什么時(shí)候端坐于味覺(jué)頂端的?成為人味覺(jué)上最大的嗜求?在四川,老百姓總要在“鹽”字后再綴個(gè)“巴”字,叫鹽巴。據(jù)專家考證,生活在今峽江一帶的古巴國(guó)幅員狹小、國(guó)力微弱,但這里盛產(chǎn)的井鹽卻名聞天下,常令各方諸侯垂涎不已。于是,產(chǎn)自巴國(guó)的食鹽在流通中也貼上了巴國(guó)的商標(biāo)——“鹽巴”,以示其正宗的地位。這是一個(gè)見(jiàn)仁見(jiàn)智的說(shuō)法。因?yàn)辂u且巴、(鍋)巴鹽一直是川地鹽類產(chǎn)品中的兩種,稱呼起碼有幾百年歷史。
1985年,我已成為井礦鹽設(shè)計(jì)研究院的勘探職工了,幾次到巫溪、云陽(yáng)一帶的鹽廠出差,測(cè)量地形、鉆取土樣,特地到著名的“鹽泉”遺址探訪。在險(xiǎn)峻的大寧河的一條小支流一側(cè),懷想古人對(duì)鹽的渴望,滿目的危石,遍地的砂巖,就很容易進(jìn)入鹽奇特的氛圍。
巴東屬于地層駢褶帶,有很多鹽泉涌出。例如奉節(jié)南岸的鹽磧壩,云陽(yáng)西北的萬(wàn)軍壩,開(kāi)縣東的溫湯井,萬(wàn)縣東南的長(zhǎng)湯井,忠縣的泔溪和涂溪二井等等。除郁山鹽泉與大寧鹽泉均自山地涌出,能很早就被原始人利用,逐漸形成一個(gè)原始文化區(qū)。其它七處鹽泉都是從河水下涌出的,不易為人類發(fā)見(jiàn)。唯獨(dú)習(xí)于行水的巴人能首先利用,他們?cè)O(shè)法圈隔咸淡水,汲以煮鹽,從而擴(kuò)大了行鹽的效果,在白鹽之上建立了巴國(guó)。
在三峽南岸八百里清江古稱夷水,其流域乃是古代巴人部族發(fā)樣之地,同樣繁衍出鹽水女神的故事,以及流傳于巫溪的“白鹿飲泉”、云陽(yáng)的“白龍”“白兔”飲泉、白帝城的“白龍出井”等等,除鹽水女神外都是動(dòng)物,這恐怕不是偶然。動(dòng)物是人的老師,它們飲泉舐鹽的本能,使其成為自然鹽的發(fā)現(xiàn)者。郭正忠在《中國(guó)鹽業(yè)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里指出:“人類對(duì)自然鹽(鹵)的發(fā)現(xiàn)和最初利用,與動(dòng)物對(duì)鹽巖、鹽水的舐飲一樣,往往出自生理的本能。”其實(shí),當(dāng)中自然也隱含了情欲之咸。
鹽水神女最早見(jiàn)于《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但我尤其注意巴務(wù)相(廩君)的傳說(shuō)。《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說(shuō):“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zhǎng),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wù)相乃獨(dú)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dāng)以為君,余姓悉沉,唯務(wù)相獨(dú)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yáng),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lái)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kāi)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這是一個(gè)驚人的神話。在我看來(lái),鹽水女神就是鹽陽(yáng)地域的土地神。務(wù)相在五族爭(zhēng)斗中,投擲精準(zhǔn)、可令泥土做的船浮而不沉,自然受到敬畏,被稱為“廩君”。廩字五行屬火,本意是“米倉(cāng)”,可知他是一個(gè)善于積斂財(cái)富的人。他從夷水(夷水又稱鹽水,今清江)至鹽陽(yáng)途中,遭遇了鹽水女神的直接求愛(ài):“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鹽水女神看重廩君什么?古書上沒(méi)有記載,直接的推測(cè)就在于他有囤積“米倉(cāng)”的勢(shì)力,但女神展開(kāi)的婚姻藍(lán)圖卻是自己的權(quán)力地盤啊。這是一場(chǎng)有關(guān)鹽的經(jīng)典愛(ài)情和戰(zhàn)爭(zhēng),簡(jiǎn)直就是父系取代母系社會(huì)的陰謀與愛(ài)情。鹽水女神可以化為蟲子,一些老人至今是深信不疑的。愛(ài)情的變形記如此浪漫,但蘊(yùn)涵了一個(gè)悖論:鹽對(duì)百蟲具有禁忌力,但鹽為何又可以幻化為百蟲?這浩大的蓬飛蟲群,遮天蔽日,不但具有愛(ài)情的澎湃之力,而且還有與日月較力的愿望——她試圖模糊時(shí)間,用黑暗中的溫柔鄉(xiāng)滯留情郎。
鹽水女神與另一名聲大噪的巫山神女有相同之處,均開(kāi)自薦枕席之先河。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并非貪圖一夕之娛,而是“留君共居”,欲作百年之好;后者則成為了打開(kāi)肉身之門的革命先鋒。楚文化學(xué)者蕭兵先生在《楚辭的文化破譯》中指出:“巫山神女、宓妃和湘君都曾經(jīng)‘自薦枕席’、‘作云雨之游’,實(shí)際上就是這種以獻(xiàn)身不贖身的高媒儀式的歷史陳?ài)E。”所謂“高媒”,原指“郊媒”,因郊音與高接近,故此。但鹽水女神的所為,是否是更為恒久的求愛(ài)方式呢?
這個(gè)愿望,與荷馬史詩(shī)中俄底修斯的命運(yùn)何其相似!奧林匹斯山的眾神同情俄底修斯,赫耳墨斯叫卡呂普索放俄底修斯回去。女神卡呂普索愛(ài)上了俄底修斯,竭力挽留,但俄底修斯一心要回到珀涅羅珀裙下。他以木筏航行十七天后,被海神波塞冬打沉了木筏。危急之時(shí),眾神助他飄到了斯刻里亞島。國(guó)王的女兒瑙西卡在海邊發(fā)現(xiàn)了他,帶他回王宮……接著,又是一個(gè)女人刻意挽留的愛(ài)情。史詩(shī)里的女人,用歌聲、金錢、情色、醇酒來(lái)模糊俄底修斯回鄉(xiāng)的時(shí)間之想,而鹽水神女幻化為遮天蔽日的愛(ài)情蟲陣,在我看來(lái),后者更具綺色之想像。但廩君不是情種,倒是更青睞于權(quán)力,“積十余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世本》又述:“(廩君)使人操青縷(青線)以遺(送)鹽神,曰:‘纓(纏繞)此即相宜,云與女(同汝、你)俱生(同死共生)。’宜將去。鹽神受而纓之(鹽神接受并且佩戴了)。廩君站在陽(yáng)石上,應(yīng)青縷而射之,天乃大開(kāi)(天空由轉(zhuǎn)晴,一片光明)。”
古羅馬詩(shī)人奧維德(公元前43—18年)《變形記》的整篇詩(shī)作均以“變形”為題——呂卡翁變狼,達(dá)佛涅變?cè)鹿饦?shù)(阿波羅月桂冠就是來(lái)自于對(duì)達(dá)佛涅的愛(ài)情,愛(ài)神丘比特對(duì)阿波羅的報(bào)復(fù))、伊娥變牛、河神阿克羅俄斯變形為蛇與赫拉克勒斯戰(zhàn)斗,為了美麗的姑娘伊阿尼拉……變形是最為強(qiáng)悍的動(dòng)詞,將男女天神的故事串聯(lián)在一起,各種天性被詩(shī)人展示無(wú)遺。比如,愛(ài)神維納斯與戰(zhàn)神馬爾斯在偷情,被愛(ài)神的丈夫?yàn)鯛枌l(fā)現(xiàn)。烏爾岡是個(gè)鐵匠,織了一張比蜘蛛網(wǎng)還細(xì)密的大網(wǎng)將妻子和馬爾斯網(wǎng)住,然后“把象牙雙扉打開(kāi),把眾神都請(qǐng)了進(jìn)來(lái)”,企圖羞辱偷情人。而這時(shí)有個(gè)神卻禱告說(shuō),他也希望蒙上這樣的羞辱——“眾神大笑,這件事在天堂上流傳了很久。”但鹽水女神的飛蟲之網(wǎng)沒(méi)有達(dá)到如此神效,她留住了十幾天的甜蜜,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jià)。
愛(ài)情信物即為殺戮的記號(hào)。愛(ài)情如黑鹵。但接下來(lái),鹽把鹽水女神包裹起來(lái),愛(ài)情是鹽肉,女神血流殆盡,成為鹽柱。攻陷女神的“米倉(cāng)”,的確是陰鷙的,宛如比遮蔽天空的蟲陣更黑的鹵缸。
漢語(yǔ)辭典上沒(méi)有具體解釋“反水”的本義。我推測(cè),這與古代風(fēng)水有關(guān)。蔣平階《水龍經(jīng)》曰:“自然水法君須記,無(wú)非屈曲有情意,來(lái)不欲沖去不直,橫須繞抱及彎環(huán)。”對(duì)水流的要求是要“彎環(huán)繞抱”,講究“曲則有情”,因?yàn)椤昂铀畯澢她垰庵蹠?huì)也”。而且《水龍經(jīng)》認(rèn)為,凡“反飛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之類的地形均為兇地,不利生養(yǎng)居住。所謂“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環(huán)朝穴。水乃龍之接脈,忌乎沖射反弓”。在那反水之地,出現(xiàn)反水之人,以及其操控的所謂愛(ài)情,歷史的常數(shù),均因這反水之舉而拐彎。
《晉書·李特載記》指出:廩君射殺鹽神之后,“復(fù)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之如穴狀,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余,而階陛(天子的階叫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zhǎng)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簡(jiǎn))計(jì)算,皆著(附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種類(原夷水諸部落的后裔)遂繁”。廩君在香爐石附近始建夷城,是巴國(guó)的興起之始。
位于湖北省長(zhǎng)陽(yáng)土家族自治縣境內(nèi)的武落鐘離山景區(qū)的德濟(jì)亭,是為紀(jì)念鹽水女神而建,當(dāng)?shù)厝俗鸱Q鹽水女神為德濟(jì)娘娘,故名德濟(jì)亭。當(dāng)?shù)厝司谷徽J(rèn)為鹽水女神是廩君的夫人!這豈非咄咄怪事。登亭四望,油菜花與桃花在尚未散去的煙云深處,形成了一種粉紅、偏黃的霧靄,不由得心頭一驚,前面就是廩君向西開(kāi)拓遇見(jiàn)鹽水女神之地,這些飛騰而縈繞的霧靄,是鹽水女神的桃花瘴么?這是否就是那遮蔽天日的蟲陣呢?在石神臺(tái)東面,有上粗下細(xì)的世石,就是鹽水女神的化身,她一直僵立于此,俯視清江,后悔了嗎?這讓我想起《變形記》最后幾行詩(shī):“吾詩(shī)已成。無(wú)論大神德震怒,還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為無(wú)形!”從事情愛(ài)變形的詩(shī)句,反而不會(huì)被時(shí)間“變形”,那么,鹽水女神不是已經(jīng)遭到了民間的極大顛覆和變形么?飛蟲之陣已經(jīng)灰飛煙滅,愛(ài)情之網(wǎng)早已魚死網(wǎng)破,連鹽也正在被物欲變壞。
《后漢書·南蠻傳》記載說(shuō):廩君死后,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本地土著產(chǎn)生了血祭白虎圖騰的崇拜形式。所謂血祭即人祭,這是一種古老而殘酷的崇拜形式,隨著社會(huì)的進(jìn)步而被“祖先崇拜”形式所替代。顯然,這又是一個(gè)絕妙的變形記,白虎的滅情之魂,繼續(xù)在山岳間盤桓。看來(lái),孔子“苛政猛于虎”的經(jīng)典名言還是太單純了,而是在于柄權(quán)者本身就是猛獸。飛蟲落地為鹽,白虎沿白鹽而走,難道這就是歷史的宿命么?
時(shí)間就仿佛是那些不舍晝夜的流水,千百年來(lái)并沒(méi)有改變什么。石頭依然堅(jiān)硬,山峰依舊巍峨。我想起錢鐘書先生的一個(gè)比喻:“鹽溶于水,體匿性存,無(wú)痕有味。”但愛(ài)情已經(jīng)被權(quán)力淪陷,鹽水已越來(lái)越少,反水卻越來(lái)越多,愛(ài)情也罷,歷史也罷,就像是一場(chǎng)鹽溶于水的幻覺(jué)。富有深意的現(xiàn)實(shí)對(duì)比是,1996年大寧鹽廠就已經(jīng)停產(chǎn),究其根本原因,經(jīng)濟(jì)決定了它無(wú)法維持下去的命運(yùn)。大寧鹽廠停產(chǎn),三峽地區(qū)的鹽業(yè)生產(chǎn)全面消失了,一個(gè)曾經(jīng)給這一地區(qū)帶來(lái)光榮與夢(mèng)想的產(chǎn)業(yè),至此宣告其使命的完結(jié)。鹽泉何在?在巫溪縣城上游十二公里大寧河邊的寧廠古鎮(zhèn),我目睹帶著泡沫的鹽水之夢(mèng)在石頭上白白流逝,像是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