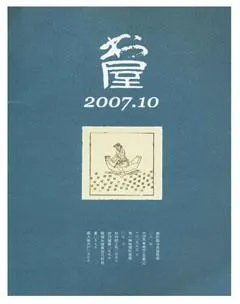何為“端賴呂后智謀多”?
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之一《上學記》(三聯書店2006年8月出版),在提及當年西南聯大讀書時,同學的鄒承魯(后為科學院院士)曾對他說:在西南聯大的教師之中,“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的是馮友蘭”。
所以“最不欣賞”馮友蘭,在當年,倒不是出于學術觀點的差異,而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即許多同學反感于馮“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如當年他那本《新世訓》最后的《應帝王》,“是為蔣捧場的”,因而有失學者的身份。后來,馮友蘭在“批孔”運動中又曾隨江青赴天津,期間寫了一些詠史詩,其中有“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后智謀多”等等,何兆武先生以為:“這話說得毫無根據。現在有關漢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記》和《漢書》,可是這兩部書從來沒提到漢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賴’)呂后的智謀,捧呂后其實是捧女權,跟著江青的意思走。”是耶非耶?
其實,當年“文革”結束之后,如梁漱溟先生等就特別反感于馮友蘭的“曾謅媚江青”,彼時馮先生則征引《周易·文言》中“修辭立其誠”的話來反省和批判自己,認為自己的問題“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不過,在具體情節上,他是有所保留的。比如“曾謅媚江青”一事。
在寫《三松堂自序》時,馮友蘭特意就此事述其原委。原來,1973年謝靜宜代表江青訪問馮友蘭,之后有人建議他上書銘感,“信是寫給江青的,但表示感謝毛主席、黨中央”。再后,江青“導演”了一出“批孔”的鬧劇,可憐“一代大儒”的馮友蘭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謂大會發言、外出參觀(天津)等等,及在小靳莊看了農民寫詩,又詩興大發,在醫院時吟《詠史詩》二十五首,其中歌唱“女皇”武則天,所謂“則天敢于作皇帝,亙古中華一女雄”等,這又被人非議為“諂媚江青”。此外,1976年華北地震,江青又親到北大地震棚來看望馮友蘭,事后馮友蘭又“奉旨”獻詩,所謂“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華講話,再次召見了馮友蘭。
那么,馮友蘭的這些“詠史詩”是不是意在恭維江青呢?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是這樣解釋的,即當時自己是從“批儒”的觀點出發,以為武則天“反儒”最為徹底,卻并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圖”,盡管當時全社會私底下都有議論“女皇”的傳聞,然而他自己“向來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書房也聽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認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國內國外的資產階級編造出來的。我只信報紙上的消息,我對于國內外形勢的認識都是以國內的報紙為憑”,于是,局促于書齋中的馮友蘭果然“畢竟是書生”,他大概不曾會料到:“向來說,‘詩無達詁’,可以靈活解釋,但是靈活也不能靈活到這樣的地步。”
后來,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女士更譴責道:“有些人慣于歪曲詩的本意,甚至在所謂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測硬安在別人頭上,這種做法甚不足取。”
那么,是不是現在何兆武先生又來妄自“杜撰”和“揣測”了呢?
《上學記》中還說到《三松堂全集》。何兆武先生說該書主持者涂又光先生曾向他解釋《三松堂全集》不收馮友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檢討,“因為那都是言不由衷”的,我記得許多馮友蘭的弟子在寫紀念先師的文章時,也每每提到“其過也,如日月之蝕”這句話。但是,何兆武先生卻不同意這種觀點,從出版角度來說,“作為一個全集來說,凡是他有的就都應該收,至于是否言不由衷還是要由讀者來判斷,不能由編者來決定,不然就應該叫選集。雖然有的人在迫于壓力的情況下說了假話,可是這些作為原始資料都應該保留。馮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為,馮先生的檢討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歷程,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可以算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思想狀態的結晶。所以,不但不應該刪掉,反而真應該給它出個單行本,為當時中國整個文化界、知識界留一份典型史料,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還重要,更有價值得多”。何兆武先生說得很對。也是因此,我對許多所謂《全集》抱懷疑態度。
其實,何先生的建議并不是沒有影子,前些年出版的聶紺弩、沈從文、郭小川等的集子,全集或是“檢討”的單行本,都已有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