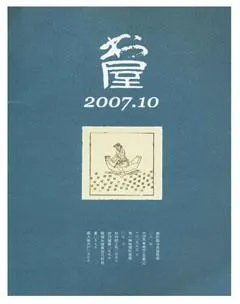惡人張大戶
潘金蓮死得很難看,不管人們寫了多少文章和搞了多少花樣為這女子翻案,至今仍然不會(huì)有哪個(gè)華裔女性會(huì)自喻為潘金蓮,也不會(huì)有人拿著潘金蓮三個(gè)字當(dāng)高帽子送。不過如果人們愿意感同身受潘金蓮,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雖然她解決與武大的婚姻問題的手段很不高明,但在那個(gè)年代似乎也難找到一個(gè)既符合風(fēng)化禮教、又能有效終結(jié)苦海的辦法。私奔?想想那個(gè)為丈夫守了十八年活寡的王寶釧,我們對她這一稀里糊涂做法的高調(diào)炒作就證明這一著也不會(huì)讓這潘姓妮子被見容。學(xué)習(xí)今天還被一些男性奉為至善至明的策略:維持家中紅旗和外面彩旗同時(shí)飄揚(yáng)?武大不同意了,因?yàn)槲涠迨逡呀?jīng)來到清河衙門了,就是武大愿意也不行,我們很多游戲規(guī)則是為男性設(shè)計(jì)的,女性不能這樣玩。所以在潘金蓮那個(gè)時(shí)代,沒有婦聯(lián)為她撐腰,沒有法律救助能幫她獨(dú)立,又沒有一點(diǎn)好的武功可以走進(jìn)綠林,還偏偏不甘心守著枕邊一個(gè)既無外在美也無內(nèi)在美的男人過一生,不像她那樣做還能如何?我們今天吟誦唐琬的《釵頭鳳》,翻讀朱淑真的《斷腸集》,可以盡情滿足審美需求,但那些字里行間的無奈和痛苦是沒有人愿意真正承受的。
從《金瓶梅》里看,潘金蓮的人生之所以會(huì)這么一塌糊涂和一個(gè)姓張的人有很大關(guān)系。沒有這位姓張的,潘金蓮不見得會(huì)嫁給武大這么個(gè)人。不嫁給武大這么個(gè)人,潘金蓮不會(huì)那么守不住婦道,至少有那賊心也沒那賊膽,就不會(huì)惹出人命案來。所以,這筆賬最后要算到這位姓張的身上來。
姓張的這人在《金瓶梅》和《水滸傳》都是在交代武大和潘金蓮姻緣時(shí)作為藥引子各使了一回,兩書的作者沒怎么肯把筆墨花在他身上。不過,和《水滸傳》一書相比(這人在該書中連姓名都無,就是一個(gè)模糊的影子,詳見《水滸全傳》第二十四回),在《金瓶梅》中,他還算是有了個(gè)姓氏,名字仍不詳。大戶相當(dāng)于一個(gè)表示尊敬的title,指這一張姓人物雖無官無職,但有錢(“有萬貫家產(chǎn),百間房屋”),比如今天老板一詞的社會(huì)交際功能一樣,能表示在一定圈里相互的尊重,也是對被稱呼人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一種介紹。在《水滸傳》一書中,這人造的孽要少點(diǎn):“……(大戶由于不能勾引得手)以此記恨于心,卻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在《金瓶梅》一書中,他就多占了幾行,而且顯然比《水滸全傳》中的更壞。據(jù)《金瓶梅》一書,張大戶時(shí)已年過六旬,卻無子女。張?zhí)軈柡Γ坏煞虿荒苋⑿∩B(yǎng),連家中的使女但凡長得清秀點(diǎn)都不肯用。這不免讓張大戶很沮喪,書中交代:“只因大戶時(shí)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大年紀(jì),又無兒女,雖有幾貫家財(cái),終合大用。’”這樣的話說多了,太太也不忍了。依照當(dāng)時(shí)習(xí)俗,當(dāng)太太的如未生養(yǎng),丈夫娶妾大有人在。余氏大概覺得有點(diǎn)理虧,為了向丈夫表示安撫,便請了媒人買了兩個(gè)使女,早晚習(xí)學(xué)彈唱,服侍大戶。潘金蓮就是這兩個(gè)中的一個(gè)。潘金蓮進(jìn)張府是使女身份,當(dāng)年也不過十五歲。不過潘金蓮自九歲就被生母賣到大戶人家習(xí)學(xué)彈唱,書中說她“不過十二三,就會(huì)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女紅針織,知書識(shí)字,梳一個(gè)纏髻兒,著一件扣子衫,做張做致,喬模喬樣”。那么到十五歲就更多些心眼,也更多些嬌美了。
隨著中唐以后城市化的進(jìn)程,帶動(dòng)市井平民文化發(fā)達(dá)興旺。從那時(shí)起,市民商務(wù)活動(dòng)中心就在一種叫瓦子(又叫瓦市)的地方進(jìn)行(所謂瓦子或瓦市相當(dāng)于今天的綜合貿(mào)易市場,游人看客來來往往,來時(shí)如同瓦合,散時(shí)如同瓦解,因此得名)。在瓦市中設(shè)有勾欄,即四周用欄桿圍起的演出專門地點(diǎn),也叫做樂棚。當(dāng)時(shí)的藝人也越來越凸現(xiàn)其專業(yè)性,有專門玩雜耍的專門說書的,還有專門演唱的。到宋朝時(shí),演唱就可分好幾種,有“小唱”、“嘌唱”、“彈唱”等等。有兩種人會(huì)買些窮人家小孩在家調(diào)教,成為家里的文藝演出隊(duì),因?yàn)橹挟a(chǎn)人家不屑去瓦市勾欄和人家擠進(jìn)擠出,被臭腳臭汗的味道熏死,有些學(xué)問的文人也要喜歡有些格調(diào)。買唱曲的在家是當(dāng)時(shí)一種風(fēng)氣,就像咱們很多人有了閑錢會(huì)買電視、DVD或卡拉OK在家自娛自樂一樣。潘金蓮進(jìn)張家就是做這種使女,不做家務(wù)粗活,是專門給主人唱曲彈琵琶、哄主人開心的家庭娛樂DJ。這種使女往往被主人收房,未被收房就在成年后被主人放出擇嫁。但女主人余氏不容張大戶下手,直到潘十八歲那年,一天,余氏去赴一個(gè)鄰居的飯局,一頓飯的功夫,潘金蓮就被張大戶收用了。可是她的苦日子也就此開始,在此之前余氏對這個(gè)使女甚是抬舉(“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等等)。但知道自己老公和潘金蓮有那么一回事后,她就翻了臉,將怨氣、妒氣都撒在處于弱勢地位的潘使女身上(“與大戶嚷罵了數(shù)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張大戶見了很心疼,只好倒賠些房奩忍痛將潘嫁了武大。
張大戶為潘金蓮安排這段婚姻時(shí),如意算盤打得很好:三方都是受益方,而且三方都相對能在各自最匱乏的方面獲得最大受益,為這段三角關(guān)系持續(xù)提供了保證。事實(shí)上,在某種層面上看來的確如此。
潘金蓮無論從情感需求還是生存需要都要一個(gè)丈夫,一個(gè)家,可以名正言順逃脫張?zhí)呐按埣掖舨幌氯チ耍氐缴干磉叢恢謺?huì)被賣往哪里,出嫁是潘金蓮最好的出路。她幼年喪父,又被生母兩次賣掉,親情于她是“稀缺資源”,所以她渴望有個(gè)自己的家,得到護(hù)佑,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她的生活能有保障。
武大本是個(gè)婚姻困難戶,無貌(綽號(hào)三寸丁谷樹皮)、無才(雖然會(huì)蒸饅頭,但按今天人力資源師的眼光看,如果找工作,他不能進(jìn)人才市場,只能進(jìn)勞務(wù)市場)、無錢(賣饅頭的本錢都折了)、無房(住的是張大戶家的房子,以勞務(wù)抵房租),還無情趣(唯一的興趣愛好就是喝酒)。現(xiàn)在不但娶到老婆,還是二九佳人(比他與前妻所生的女兒只大六歲),長得漂亮還有才藝,堪稱尤物。更妙的是,這個(gè)老婆還是真正的財(cái)神婆,她帶來陪嫁,還有以后張大戶不斷的接濟(jì),有這等好事,他也應(yīng)該滿意了。我想他聽到張大戶提親時(shí)除說了表示“我愿意”一類的話,還對張大戶說了很多感激的話。
張大戶當(dāng)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第一,悍妻沒有理由再發(fā)作,他的耳邊清靜了;第二,潘金蓮其實(shí)離他不遠(yuǎn),就住在他臨街的房子里,見面很方便,省了他時(shí)間氣力;第三,搭上一些錢財(cái)就把武大這樣一個(gè)孱頭搞定,等于敲定一樁買賣。張?zhí)糁辛宋浯蟛皇且驗(yàn)樗L得難看,而是看中武大的性格窩囊。張對武大那么幫襯,因?yàn)槊x上潘金蓮嫁給了張家房客武大,實(shí)際上是被寄放到武大屋里,人還是他張大戶的。武大拿了人家銀子也就談不上什么骨氣,明明曉得張大戶和自己妻子不干凈,卻也會(huì)討乖巧,一味裝聾作啞,主動(dòng)回避,直到張大戶過世,這段孽緣才算了結(jié)。
張大戶這樣做很不地道,他利用潘金蓮當(dāng)時(shí)的無知和無助,武大的困窘、貪心和外表丑陋,安排下這么一段令當(dāng)事人很快就會(huì)覺得并無愉悅可言、只有羞辱和不堪的婚事,為后來的悲劇、丑劇播下種子。
看過《紅樓夢》或《金瓶梅》的讀者往往會(huì)有一個(gè)錯(cuò)覺,以為古時(shí)的漢族男子和今天北非沙漠上的貝都因男子一樣,個(gè)個(gè)都盡享齊人之福。其實(shí),一夫一妻制實(shí)際上并未因納妾習(xí)俗的存在而邊緣化,經(jīng)典的家庭觀或婚姻觀仍然認(rèn)為一夫一妻是合乎天理的。“妻”這個(gè)字在古文從女從貴,潘光旦先生說貴在這里指有意義,《說文》中這樣解釋:妻者,婦與夫齊者也。我引用這些不是想扮演風(fēng)化警察在這里對張大戶做什么道學(xué)層面的批評(píng),只是想說張大戶年輕氣盛時(shí)都忍得住,能自覺遵守主流的婚姻價(jià)值,到老了竟敢和老婆叫回板,可能還不只是因?yàn)橄胍⒆踊虮慌私鹕徝宰×恕K畹搅嗔耍@個(gè)年紀(jì)的人一般來說真的沒什么造反精神了,他這些年來在余氏監(jiān)督下都過了,實(shí)踐了和老婆一起“慢慢變老”,怎么現(xiàn)在就不能再這么過下去?
雄性生來是多偶取向的,這在生物界已經(jīng)證明,后來也被心理學(xué)界證明。講到這里,想起一個(gè)人來,那就是美國第十三任總統(tǒng)約翰·卡爾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