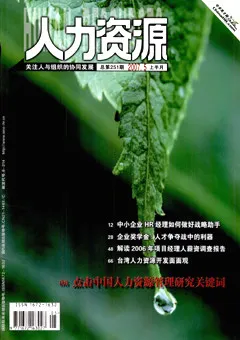從個稅申報探究高收入者的社會責任
2007年4月2日,是年所得12萬元以上納稅人自行納稅申報的最后一天。據國稅總局發布的數字,全國自行納稅申報人數達到1 628 706人,雖然與目前稅務機關按建檔情況估計的應申報人數比較接近,但與社會上普遍預計的高收入群體600~700萬人,還是有較大差距。
從申報人員的職業結構看,“唱主角”的是收入相對透明的工薪階層,占申報比例的60~70%,而私企老板、自由職業者、個體工商戶等寥寥無幾。尤其是高收入者中的私營業主、律師、演藝明星等,收入來源多種多樣,收入形式或明或暗,不易被稅務機關掌握。其中的有些人在平時就變著法偷稅逃稅;有些私企老板表面上不拿工資或拿得很少,可是個人和家庭的各種開銷都直接或變相打入企業成本,不但偷逃個人所得稅,還逃漏企業所得稅;有些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則是大量的現金交易,因而心存僥幸,以為可以逃過稅務機關的監管。
凡此種種,暴露出我國現行高收入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依法納稅觀念淡薄,社會責任意識嚴重缺失。
社會責任,是指公民在社會生活中對國家或社會以及他人所應當承擔的一定使命、職責、義務。當一個人占有的公共資源遠遠大于社會平均占有量時,這個人的社會責任就應該相應地提高。美國思想家約翰·羅爾斯在“補償原則”提到,跑到前面的人一定要對后面的人進行補償。中國古人云,“損有余而補不足,天之道也”,也是這個道理。因此,高收入者應當比普通公民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其中既包括法律責任,也包括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
法律責任是“底線”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提倡正義的社會。在正義的社會中,高收入者承擔著對國家財政稅收做出更大貢獻的責任。因為與普通公民相比,高收入者能夠從政府那里享受到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而政府也有責任以立法、執法等強制行為確保其履行這類義務。
稅收是國家賴以生存和運轉的主要經濟來源,同時還具有重要的社會調劑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可以通過稅收獲得公益性資金,用以維持低收入者和無收入者的基本生計,并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和發展能力;二是政府通過征收個稅、遺產稅,適當地減少高收入者過多的收入和財產,用以調整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為均衡社會財富、保持社會和諧發展提供保證。
所以,我國同大多數發達國家一樣,采取了累進稅率(收入越多繳稅比例越高)征收個人所得稅,讓收入多者多繳稅,多承擔社會責任,讓低收入者少繳稅直至享受社會補助。在美國,高收入者就是國家個稅納稅的主體。據有關統計資料,美國年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群體,繳納的稅款每年占國家全部個人稅收總額的60%以上,是美國稅收最重要的來源。
我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以后,首次以法律形式做出規定: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個人要自行申報納稅。這項強制性措施劃定了高收入者社會責任的“底線”,其法律層面的意義非常深遠。一是有利于明確高收入者納稅的法律責任。在規定的時效內自覺申報納稅,是高收入者的法定義務,違者要受到懲誡。二是變過去的被動納稅為主動納稅。納稅雖然是由法律規定的強制性行為,但對于高收入者來說,更要靠自覺申報。三是彰顯強勢的示范效應。以高收入者主動申報為樣板,提高全體公民對稅法的遵從度,為我國個稅走向全員申報打下堅實的基礎。
全員申報納稅,要有一個社會輿論形成和公民行為適應的過程。如法國是一個全員申報納稅比較到位的國家,那是因為法國稅法形成了嚴密的法律體系,構建了嚴格的法制環境,讓納稅人難以鉆空子;同時管理和制約手段也很完備,公民達到納稅人年齡后,會收到稅務機關有關繳稅的詳細說明信件;而納稅人在行使相關公民權利時,必須出具完稅證明。在許多發達國家,完稅證明是個人信用的重要體現。
因此,培養公民納稅意識是全民申報納稅的基礎,而強化高收入者的法律責任,則是其樣板作用得以實現的“底線”保證。
道德責任是“準繩”
道德責任是指一定經濟關系所產生的對人的道德要求。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社會都必然要求每個人履行他對公眾和他人應負的道德責任。這是一個道德“準繩”。而對于每個社會成員來說,主觀上都要認真地選擇自己行為的動機,考慮行為的后果。因此可以說,履行道德責任,是要靠內心信念和高度的道德責任感來實現的。
對于高收入者來說,這種內心的信念就是“多勞多得還要多回報”;道德責任感就是“我是高收入者,本來就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因為高收入者掌握和使用著比普通勞動者更豐富的資源;而不論其占有這些資源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應當說,高收入者比普通勞動者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也符合當今公眾普遍認可的道德要求。
高收入者多納稅,雖然從形式上看帶有某種“削高”甚至“劫富濟貧”的色彩,但實質上體現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從長遠意義看,這種做法對于高收入者來說,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其一,高收入者多納稅,其結果是個人財富與公共利益同步增長,從而使高收入者也成為改善了的公共利益的受益者。其二,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看,個稅和遺產稅的征收,有助于高收入者的后代“平等”地進入社會,其面臨的風險因素會降低和減少,高收入者也可以減少后顧之憂。其三,高收入者對于稅收所做的積極貢獻,也是其自我價值實現的一個重要標志,可以從中獲得精神上的莫大滿足。
從道德的角度來看,誠信納稅也是高收入者道德觀念的重要體現。納稅意識不強,偷稅、欠稅、騙稅甚至抗稅,說到底是人品不好、自私自利的表現,應當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前不久,由某省國稅局舉辦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80.5%的被調查者表示,不愿意跟欠稅或涉稅案件曝光企業往來,說明大多數民眾對納稅不誠信、有不良記錄或者有“案底”的企業和企業家保持著高度戒備心理;這些企業在資金支付能力及合同履行能力等方面受到質疑。“人無信不立,商無信不興。”個人也好,企業也好,失去了信用,就難以在市場競爭中立足。所以企業家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個稅申報不良記錄一旦被曝光,不但影響個人的聲譽,而且危及企業的生存。
慈善責任是“境界”
慈善責任也是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方面,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越多,所應承擔的慈善責任也應越大。高收入者將個人財產捐助給社會慈善事業,積極、主動、無私地直接援助弱勢群體,是履行社會責任的最高“境界”。
慈善捐贈,在我國現階段和諧社會建設中更有意義。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在拉大,根據2003年9~10月在全國城鎮范圍內進行的抽樣調查,當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我國城鎮家庭最高20%收入戶與最低20%收入戶,年人均收入的差距在1990年是4.2倍,1998年是9.6倍,而2003年這一指標的倍數已經達到兩位數。據《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年11月24日)報道,中國目前每年有近6000萬以上的災民需要救濟,有2200萬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還有6000萬殘疾人、1.4億60歲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幫助。可見我國社會慈善事業的包袱是何等的沉重。
在西方,人們把財富和責任融為一體,把投身慈善事業不僅看做是一種社會公德和責任,更當作一種回報社會的生活習慣。因此出現了比爾·蓋茨、巴菲特等諸多大慈善家。我國目前也并不缺少高收入者。據統計,在全國各大銀行總數約7萬億元的儲蓄存款中,不到20%的富人占據了80%以上的份額。然而,據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全部私人捐贈僅17億元,這其中大約75%來自國外,10%來自普通勞動者,只有15%來自國內的高收入群體。這兩組數字對比表明,在我國現階段,財富占有與慈善捐贈存在著巨大反差,折射出高收入者慈善責任嚴重不到位的缺憾。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慈善責任是高收入者的社會責任。我們應該構建尊重和鼓勵“幫貧救困人群”的社會氛圍來喚醒高收入者的良知;同時,憑借公共權力和強大的社會輿論力量,促使高收入者履行好自己的法律責任——依法履行個稅申報,確保自身的完稅責任達標,進而達到超越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的境界——做一個受人尊重的慈善家。
(作者系遼寧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現工作單位:沈陽市和平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