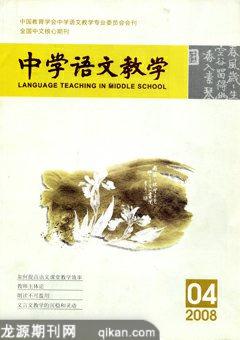尋求“量”與“質”的動態統一
長期以來困擾語文教學的“少、慢、差、費”問題,在實施新課程的當今仍然存在。很多教師還沒有真正弄懂語文教學的任務,語文學科的特點,語文學習的特殊性。專家也沒有弄明白。圈里圈外的人士出于好心,瞎子摸象似的就各自所“摸”到的東西發表宏論,闡述“摸”的技巧。當然本文也屬瞎子摸象之類。
已經實施新課程的省份的語文課與未實施新課程省份的語文課整體上有何區別?實施新課程省份的教師個體在新課程實施前后上的語文課有否本質不同?未實施新課程的省份的教師所上的語文課就沒有新課程的因素嗎?這些問題都難以簡單肯否。
據調查,進入新課程省份某校的教師,《燭之武退秦師》講七節課,《鴻門宴》講十節課,而且教材所有篇章都細講,得知此事我曾當面挖苦人家“用自殘的方式殘害學生,用認真負責的假象誤人子弟”。一篇短文講上兩周,不外乎“逢山開道,遇水搭橋”,碰到什么講什么。于是疾呼課時不夠,于是許多學校把規定的每周四課時增加到五課時,周六再增加一課時,加上相當于兩課時的晚課,每周實際上為八課時。這是很普通的課時“量”。這是量多而無質:課時“量”的積累并沒有促成“質”的飛躍。甚至從小學到高中學習語文十二年,也沒有很大突破。
一次新課程研討會上,某省教師上觀摩課只講《短文三則》中的一則;某省新課程競賽,多位教師只講《詩三首》中的一首。這是量小亦無質:課堂容量小,也沒有實現質的轉變。
一、 根本轉變學習方式是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前提
《基礎教育改革綱要(試行)》指出:“改革課程實施過于強調接受學習、死記硬背、機械訓練的現象,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合作學習。”《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在“教學建議”部分規定,語文教學要“積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這是新課程學習方式轉變的核心理念。是對傳統語文教學重接受輕探究、重認識輕體驗的接受性學習方式的揚棄。這一理念強調了學習和發展的主體是學生,學生在課程與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得到了真正的確認和尊重,調動了每個學生的參與意識和學習積極性,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給語文課堂面貌帶來了生機。
其實,教師在單位時間內完成的工作量不一定轉化為學生學習的“質”。因此,探究“量”與“質”的統一是提高課堂教學效率不可回避的問題。這里的“量”指課時量,也指完成教學任務的工作量;“質”著重指學生對教師傳授的知識的有效接受與能力遷移。因此,不管學校安排多少課時,教師使用多少課時完成教學任務,如果學生仍是一味被動接受,都不足以使之達到“質”的飛躍。問題的關鍵在于,要轉變學習方式。
據調查,高中生面對課文(以文言文為例)文本,借助工具書和書下注釋能夠讀懂50%~70%。以上述《燭之武退秦師》(必修1)講七課為例,同樣是七課時,如果前面的六課時教師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工具書檢索有關文言詞語、基本弄懂文章大意(基本情節),并且提出未能獨立解決的問題,嘗試同學之間探究解決,實在解決不了的拿到課上師生共同解決,那么,一課時足以完成教學任務。這樣安排教學的最大益處是,教師強化培養學生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獲得語文學習的正確方法,經過今后語文課堂的鞏固、積累,自然達到語文學習的質的飛躍。能夠堅持下來,到講《廉頗藺相如列傳》時(必修4)也不用七課時了。
這里“質”的飛躍似乎“量”也很大,但同鋪天蓋地、教師包辦、昏天黑地地“講”七課時而沒有達到“質”的飛躍的性質不同。這樣的大“量”投入只是初期學生沒有形成學習習慣的時候,這種“量”的投入是值得的,逐漸地會不斷減“量”而增“質”。可是如果教師沒有促成學生學習方式的根本轉變,只靠單方面去完成工作量,在課堂上這樣特定時空完成的任務再多,也是難以取得實效的,因為學生沒有真正動起來,一切提高效率的方法都難以實施。
二、 學習時間前移是提高課堂效率的基本途徑
課堂教學的時間、空間、內容都是相對固定的,時間長度40多分鐘,空間幾十平方米,內容多由課本規定,教師有限選擇,這都可能制約學生的發揮。通常情況是:學生沒有形成較好的語文學習習慣,不能獨立自主地學習,課堂才接觸課文,根本不了解課文的基本內容,只好被動聽教師講解。因為課前基本上沒有瀏覽課文,也提不出什么問題,就習慣地由教師滿堂灌。這樣一來,學生是在“聽課”——徹底淪為“聽眾”,主體不在場;教師是在“演講”——徹底變成獨角戲。師生不能真正對話,是因為沒有對話的話題。而課文一般都比較長,在有限的時間內難以將所有環節都完成。這就要求教師指導學生把熟悉文本基本情況的任務在課前完成,實現學習時間的前移。課堂則作為討論重要問題的舞臺。
我八年前聽過一堂省級教學競賽課。一位教師同別校學生用一課時學習《燈下漫筆》。班級是某市重點中學重點班。課前教師要求學生自讀課文,并提出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課上,教師請學生提出自己的問題,由教師寫在黑板上,共計21個問題。然后教師請學生逐次擦掉問題,同時解釋擦掉的理由。最后,只剩下一個問題:“為什么作者認為中國歷史只有兩個時期,即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最后,學生解決了問題,下課時間到。
這位教師在自己授課班級“講解”這篇課文時,學生沒有提前熟悉文本。課堂上只見他抱了一摞參考資料,一會兒介紹某某的觀點,一會兒宣讀某某的成果,學生處于半睡眠狀態。
檢討這堂課,教者終于認識到,學生在沒有進入文本的時候,教師用比課文文本更艱深的文本闡釋本來不算艱深的文本,學生完全淪為被動的“聽眾”“看客”,主體不在場,課堂當然死氣沉沉。在競賽現場,學生全是尖子,有自主學習的習慣,探究能力強,積極性很高,并且有“為難”這位借班上課教師的意思,所以課前的預習充分,課上思維活躍,解決問題的欲望強烈,使得課堂充滿激情與睿智,令聽課教師幾年后還回味這堂課。
這位教師的最大成功是“沒講什么”,因為在自己的班級全是他自己講。全是自己講,對學生就是“要你聽(看)”,自然被動;看似“沒講什么”,實際上對學生就是“請你講”,由于學生的積極學習動機強烈,“給點陽光就燦爛”,“請你講”就變成了“我要講”。
新課程教材(必修)由“閱讀鑒賞”“表達交流”“梳理探究”“名著導讀”四部分構成。上面舉例針對“閱讀鑒賞”。梳理探究部分以人教社必修1為例,有“優美的文字”“奇妙的對聯”“新詞語與流行文化”三課,篇幅不長,內容豐富,如果不引導學生課前充分閱讀,查找相關資料,拓展知識視野,僅僅靠課堂講解是難以奏效的。再如名著導讀,如果課前對“導讀”的名著沒有一定的了解,課堂上只能是鴨子聽雷了。
由于學習時間前移,拓展了課堂時空,從學習過程看,是增“量”而達到“質”變;但從課堂教學過程看,則是“量”少而“質”精。
三、 恰當增刪教材內容是提高課堂效率的必然選擇
教材只是實現教學目的的憑借之一,不是唯一。因此,任何教材都不足以完全“照本宣科”,也就是說,優秀教師善于“用教材教”,而不是只“教教材”。
既然教材不是唯一,當然就要適當增“量”,目的當然為了促成“質”變;由于語文教材結構都是文選式,單篇課文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講哪篇不講哪篇一般不會影響語文學習效果,因此完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刪除一些課文,以達到減“量”不減“質”。
增與刪的標準,一方面根據學生的需要,一方面根據教師個人的學養靈活確定。
古代詩詞、現當代詩歌、外國詩歌單元一般以活動課效果為好,可以增加一些詩篇。請學生自行選擇喜歡的詩人的其他詩作推薦給同學,在課堂朗讀。小說、戲劇長篇節選作品還可引導學生通讀全書。這都是通過增“量”實現“質”變。
四、 優化課堂結構是提高課堂效率的顯著手段
優化課堂結構,就是剔除無效教學環節(這也是一種減“量”),統籌課堂動態的教學資源提高效率。
長期以來語文課堂結構都是由以下幾步構成:介紹作者及創作背景,分析題目含義,歸納段落大意,總結中心思想,分析寫作特點。一般說來,以上幾個環節對解讀文本是必要的,但不等于說解讀文本必須按照這幾個環節展開。這樣的模式禁錮了對文本的精彩解讀。
《荷塘月色》創作于1927年,作者又是一位有骨氣的知識分子。于是創作背景被演繹成“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作者的“不寧靜”便是源于對“四·一二”的不滿。尋找重大政治背景就成了文本解讀的重要任務,用重大歷史事件詮釋文本就成了必要手段。每堂課都這樣解讀,并且試圖引導學生尋找其中必然的邏輯聯系。由于多媒體的介入,很多有條件的教師把作者、背景制作成演示文稿用電子屏幕展示,內容都是下載的詞條式說明語言,使得或許有必要的環節索然無味,甚至令人生厭。有的教師則是請學生課外查找作者、背景資料,課堂宣讀;更有教師把作者介紹變成固定格式,什么生、死、名、字、號、籍等等,讓學生背下來。
優化課堂結構,就要對許多環節精心整合。縱觀教材,魯迅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詩歌、《史記》的篇章都是教材中選擇較多的,而且分散在不同年段。有必要反復多次介紹魯迅、李杜、司馬遷嗎?雖然劃分段落、歸納段意在解讀文章時不能回避,也不必把這些當成解讀文章的核心因素。至于寫作特點,以往那種教師先列出條條框框,然后再用文章中的具體內容加以說明的做法,并不能使學生將所謂寫作特點轉化為自己的寫作能力。
優化課堂結構,還要摒棄一些習慣成自然的教學方法。以“表達交流”為例,很多學校以課時不夠為由將課堂作文變成家庭作業,作文指導也主要是寫作知識講解,作文講評則是范文宣讀。我對目前慣用的作文指導、講評之法存有異議,認為在摒棄之列。
關于寫作指導。揚雄說:“能讀千賦,則能為之。”這是講讀書與寫作的關系,他認為,多讀書就會寫作了。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是講讀書與寫作的關系,他進一步認為,書讀得多文章就能寫得好。這兩位都是大文學家,他們的經驗之談令人信服。
梁衡說,他寫文章一是學習司馬遷,一是學習韓愈。他說從司馬遷和韓愈那里學到了文章的結構章法。也就是說,他是在研讀司馬遷、韓愈的文章時得到了關于寫文章的啟迪,又在自己的寫作中不斷嘗試,讀寫結合,終于大成。這是今人學古人的例子,有現實意義。
今人、古人都認為會寫、寫好文章來自多讀書。可是,目前語文教師的閱讀面普遍較窄,大于等于教材,小于等于教參。教師用編制試卷、做試卷來替代讀書(也用同樣的方法剝奪學生讀書的權利),用系統講解所謂“寫作知識”來掩蓋不會寫作的真相(同時也誤導學生),而學校又習慣用“全批全改”檢查教師的工作(教學管理中最形式主義的作風)。但是,無論如何,不讀書、思考,就難以形成寫作能力,就不能教會學生寫作;“全批全改”也批改不到點子上,只是徒耗心血而已。
關于作文修改。《呂氏家塾記》說:“歐公每為文既定,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傅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稿,其精審如此。”①這是強調作者自己多改的例子。既然作文的主體是學生自身,修改文章卻是教師的事,主體不參與,不可思議。我們不能因為不曾嘗試學生自己修改文章,就以學校、家長不同意,學生不習慣為借口,關鍵是教師自己要“立規矩”。你是這門課的專家、權威,你沒有發言權起碼說明權威性不夠,你也要先長能耐。
《世林廣記·速成法》說:“若改小兒文字,縱作得未是,亦須留少許,不得盡改。若盡改,則沮挫其才思,不敢道也。直待作得十八分是了,方可改作十分。”②這是強調教師少改的例子。教師少改并不是偷懶,不負責任,而是在學生不得其法、水平欠佳時多改,容易令學生產生畏懼感,影響其才思的發揮。只有學生文章水平長進到比較好了,才做較大修改。古人的這條經驗在今天也有實際意義。
如果教師能夠在修改文章方面立下這樣的規矩,利用課堂時間學生個人多改,學生之間多改,教師少改(改則點鐵成金),每次根據具體情況確定修改的標準,逐步提高標準,學生按這樣的規矩修改,看看結果如何?作品修改的形式多種多樣,在教學過程中能夠根據教學情景生成許多動態方法③,不僅提高學生作水文平,還能提高教學、學習效率,教師還能探索出一條新路。
①②轉引自《中學語文教學研究資料》(第四冊),北京師范學院、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學語文教學研究室編,內部資料。
③參見張玉新《動態演示作文評改的設計與實施》,《語文教學通訊》(高中版),2007.1
(吉林省教育學院 1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