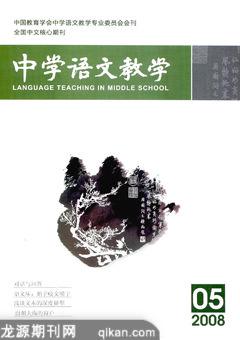學生意識:語文教學的起點
鄭逸農 汪益軍
記得余秋雨先生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說,他七歲的時候接過媽媽的接力棒,開始代全村人寫信。從那時開始,他的面前就站著一個收信的人。
那我們語文教師面前是不是都“站著”學生呢?不一定。
比如說備課。教師想著的可能只是自己該怎樣來教這篇課文,而不是想著學生面對這篇課文的時候,會是怎樣的一種認知狀態和情感態度,學生學習這篇課文要達到的理想目標是什么,作為教師應該怎樣幫助學生達到這個理想目標。傳統教學強調教師備課要充分,但這種充分,是為教師的“教”而準備的,而不是為學生的“學”而準備的。有位專家說:“教師為教而準備,即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教師自覺不自覺地準備將自己放在課堂的中心,因而盡可能想把課堂情境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①
再比如說上課。有的教師只是把預設好的教案滴水不漏地講一遍,灌輸一通,指示一番。雖然教師有時也會讓學生參與進來,但這種參與基本上屬于陪襯和點綴,是一種假參與。就說提問,教師提出一個問題后,不是讓全體學生一起討論,充分交流,而是隨便點一兩名學生回答。學生回答后,有的教師連一句點評的話都沒有,又繼續“灌課”了。有的教師提問的目的只是引學生說出某個詞,以便順著這個詞繼續往下講課。如果學生說不出教師所需要的這個詞,課就上不下去了。有的教師為了在黑板上寫出某個預設好的詞語,也來提問,但學生的回答往往與教師預設的答案不一致,而實際上學生的回答和教師預設的答案可能還是近義或是同義的甚至學生的回答更精彩,可教師就是不往黑板上寫。因為這不是他們預設的答案,這樣寫上去會讓他們覺得心里不踏實。有的教師是真的想向學生提問,但剛剛提問,就讓學生匆匆起來回答了;而教師在課前可能是花了好長時間才思考出這個問題的。有的教師用多媒體上課,答案早就預設在多媒體中,亮出的速度更加快,學生幾乎沒有思考的時間和機會。
還有課堂小結。一節課教完了,教師會很自然地對自己的“教”小結一番,卻沒想過要讓學生對自己的“學”小結一番,乃至反省一番。
所以,王尚文先生說:“學生,仿佛是教師的附屬;教學,仿佛是一種入侵,一種心靈殖民行為。”{2}
新課改需要的不是“表演”,而是“表現”。
“表演”和“表現”,一字之差,相距萬里。前者是“目中無人”,只有教師自己;后者是“目中有人”,和學生一起,切磋交流,相互教育,共同成長。
我們需要建立這樣的新理念:由基于教師付出的教轉變為基于學生自我學習的教,由基于教師教的學轉變為基于學生教自己的學。
說到這里,學生意識的含義基本明了了。
學生意識,簡言之就是“目中有人(學生)”。它是對學生生命的自覺關注,是把課堂還給學生,保障學生的學習權。
那么,學生意識如何在教學中體現呢?
第一,要讓學生參與到整個教學過程中來。
比如提問,要讓全體學生參與進來。教師提出問題后可以先讓每人獨立思考,然后讓他們在同桌或小組內交流討論,形成共識,最后才讓學生代表起來說說。同時還可以讓每個學生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嘗試著探究問題答案。
比如朗讀,也要讓全體學生參與進來,讓每人都有自己的體驗,然后才讓一些同學讀一讀,或者教師也讀一讀,或者播放一下錄音。
再比如課堂小結,教師要引導學生主動地對自己的“學”進行小結和反省,要由“基于教師教的學轉變為基于學生教自己的學”。
總之,每個學習環節都應讓學生充分參與,充分體驗。
第二,要和學生平等對話,一起進步。
王尚文先生曾經說:“教師的心靈未必比學生高尚,教師的人格未必比學生高貴,教師的能力未必比學生高強。”{3}確實,教師的經驗和知識不完全是學生學習的前提,師生對某些問題的理解不一定有明顯的正誤與優劣之分。在進入一個作品的時候,教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學生也是一個有思想有個性有活力的人,而不是一只等著填充的鴨子。教師以自己的閱歷、經驗、知識、個性所理解到的作品的意義,與作為學生的理解是有差異的,教師不應該把自己的理解作為定論灌輸給學生,強迫他們接受,而應該積極引導,讓學生調動自己的閱歷、經驗、知識、個性等與文本主動對話,積極建構自己的意義,不把現成的答案和結論灌輸給他們。杜威說:“要使教育過程真正成為師生共同參與的過程,成為真正合作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師生兩方面都作為平等者和學者來參與。”{4}巴西教育家保羅·弗萊雷說:“沒有了對話,就沒有了交流;沒有了交流,也就沒有了真正的教育。”{5}師生間平等對話,相互教育,共同成長。
平等對話的學習情景是什么樣的呢?筆者不妨借用李鎮西先生的生動比喻來描述:“面對美味食物,師生共同進餐,一道品嘗;而且一邊吃一邊聊各自的感受,共同分享大快朵頤的樂趣。在共享的過程中,教師當然會以自己的行為感染帶動學生,但更多的,是和學生平等地享用同時又平等地交流:他不強迫學生和自己保持同一的口味,允許學生對各種佳肴做出自己的評價。在愉快的共享中,師生都得到滿足,都獲得營養。師生平等和諧,教師在保持其教育責任的同時又尊重學生,和學生一起進步。”{6}
平等對話的教學,既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也不是以學生為中心,而是教師引導下的交流共進。
第三,要把學生當做完整的生命體來培養。
面對每個文本,都要努力把理想的教學目標確定為讓學生的認知和情感同時得到發展,使學生的語文生命健康成長。就是說,教學中不只關注學生的認知獲得、考試分數,還要關注他們的情感發展和品性提升。既關注學生外部行為的變化,也關注學生內在心靈的美化。把學生當做行為和心靈相融、知識和情感和諧的完整的生命體,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說:“教育,并非只是用來訓練心智。訓練提升了效率,然而卻無法造就一個圓滿的個人。”{7}
比如:教學《荷塘月色》時,既要讓學生學習優美柔麗的語言,又要讓學生體會由語言而營造出的優美恬靜的意境;教學《項鏈》時,既要讓學生學習生動的語言、巧妙的構思,又要讓學生體會由語言而表現出的主人公瑪蒂爾德在不幸命運前的尷尬和勇毅;教學《我有一個夢想》時,既要讓學生學習邏輯嚴密、氣勢磅礴的演講語言,又要讓學生體會作者在演講中表現出的為同胞的自由平等而斗爭的堅定信念和非暴力的文明修養……這樣就能讓學生在語言和精神兩方面同構共生,“使學生在語文學習和技能訓練的過程中得到情感的陶冶、心靈的建構、文化精神的涵養,為學生打下堅實的精神的底子……”{8}
樹立學生意識,教師是否可以放任不管呢?不是,它對教師的要求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既要求教師提高眼界,又要求教師夯實根基。而這些,都來源于學習,“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①周軍《教學策略》,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第27頁。
{2}王尚文《走近語文教學之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573頁。
{3}王尚文《一份富于創見的答案》,《語文學習》2000.7
{4}王承緒、趙祥麟編譯《西方現代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48頁。
{5}保羅·弗萊雷、顧建新等譯《被壓迫者教育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第41頁。
{6}李鎮西《共享:課堂師生關系新境界》,《課程·教材·教法》,2002.11
{7}[印]克里希那穆提著,張南星譯《一生的學習》,群言出版社,2004,第7頁。
{8}曹明海、史潔《用語文點燃學生的生命之燈》,《中學語文》,2007.1
(浙江省江山中學 241000 浙江省衢州一中 32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