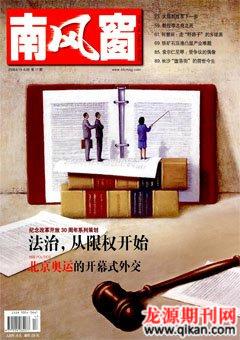教授李志良之死
楊 軍
雖然李志良廣受學生愛戴,但奇怪的是,在采訪過程中,幾乎所有聯系到的采訪對象都像躲瘟疫一樣躲避記者。
千古艱難唯一死。2008年5月24日,年僅46歲的重慶大學教授李志良,從自家樓上一躍而下,放棄了正處于學術盛年的生命。
近年以來,教授自殺事件已有數例:2006年6月,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師文力從辦公樓墜下,當場死亡。2007年1月,年僅45歲的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某女教授自殺身亡。2007年12月,50歲的人民大學中文系博導余虹跳樓自殺,并引起媒體大范圍關注和討論。
相比類似事件引起的熱議,數月之間,理工科教授李志良之死卻只引起了網絡上小范圍的討論。
學生愛戴的老師
李志良是重慶大學化學化工學院的老師,研究生導師,因為化工學院沒有博士點,李同時在重大生物學院帶博士。重點從事藥物疫苗設計創制、藥物生物譜學、化學生物信息與計量學等方面的研究。在采訪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表示,他是一個好老師,“是學生特喜歡的那種老師”。
李老師中等身材,人看起來很學術氣,頭頂略禿,被學生開玩笑地稱為“锃光瓦亮的腦袋”。1990年3月博士畢業,師從著名的化學家俞汝勤院士,博士畢業后赴日做博士后,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兩年后,他謝絕老師的挽留回到母校湖南大學任教,傳為佳話。
1997年調入重慶大學。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據說會說三門外語。一口濃重的湖南普通話,學生戲稱他說日語可能更容易聽懂些。講起課來縱橫捭闔,偶爾穿插吟誦詩詞格律,對學生總是微笑著,“雖不善言談但是很有魅力”,上課會讓學生自己出來講或者走到學生中間像聊天一樣講課。“讓我欽佩的老師不多,李老師是一個。”有學生這樣告訴記者。
學生們說得最多的是他對學術的癡迷。他會在凌晨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就跑到實驗室做實驗。他和同學談起學術問題滔滔不絕,完全沉迷其中,忘了周圍的事物。他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搞科研。對學術專注執著到近乎“迂腐”,工作起來沒有節假日、星期天,沒有時間概念。“經常看到很晚他實驗室的燈仍亮著,第二天胡子拉碴地上課。”其建模能力也很強,每年輔導參加數學建模比賽的學子。
“李老師是化工學院做學術做得最好的幾個教授之一,招研究生的時候,分數不夠高報考他的研究生肯定沒戲。他的學生就業也相當不錯。”沒敢報考李老師研究生的學生有點遺憾地說。
李志良主研或主持完成了國家和省部基金課題20多項及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獨立及聯合申請中外發明專利十多項。所發表論文,被SCI收錄數十篇。
和學術一樣獲得學生高評價的是李志良的人品。他“沒有一點架子”,和藹、謙遜,為人“正直善良”,“富有愛心和同情心”,對每一個學生都十分關心,自己生活非常簡樸,卻常常無償資助一些家庭困難的學生。
他是為數不多的能親自帶學生搞科研的老師,很多老師都是拿到課題分給學生,自己深入科研一線的很少,李老師恰恰能做到這一點。別的老師一般也都是讓學生去報賬,只有李常常都是自己去報賬。
汶川特大地震之后,李志良給災區捐了3萬多元,雖然據學生估計,“他的積蓄應該也不多”。
壓力何在?
同時李又是一個不太修邊幅的、在生活中粗枝大葉的人,“外表全然看不出是一個科學家、優秀的教授”,他會在凌晨想到問題的時候直接穿著睡衣就跑到實驗室,曾因為把家里和辦公室鑰匙都忘在實驗室里,而在實驗樓的路燈下站一夜。
據介紹李志良有一個能力的妻子,還有一個在重慶重點高中讀書的女兒,成績非常優秀。看上去是一個很好的三口之家,李事業發展也不錯,又如此受學生歡迎。似乎沒有選擇離去的理由。
當時,李志良上課是在新校區D區,在從新校區回老校區的車上還和同學們聊天探討學術問題,沒有任何反常,第二天很多學生聽到他自殺的消息,第一反應是不相信。沒有人知道他最后的心路歷程,是什么導致他跨出了這一步。他的筆記本上這樣寫:“同學們,我對不起你們……”
學生們告訴記者,前幾年李老師的學生出了點問題,似乎是論文抄襲或者是代寫,具體不是很清楚,但當時負面影響很大,一度影響到李老師的招生。但李老師一樣挺了過來,說明他心理承受能力應該還可以。
有學生推測:也許是對學術環境絕望了吧,否則我想不出他自殺的理由,他是個對學術很執著的人。很多學生都認為,李老師是一個不太管人情世故的人,除了學術,其他的東西多看得很淡。
也有學生告訴記者,李老師學術上比較厲害,但是項目申請有問題,因為現實的學術環境,能力強是一回事,申請到項目是另一同事。在相鄰幾個實驗室中,他的實驗室條件是比較差的。因為他爭取不來資金,在他手下的學生就沒有一定的補償。李實驗做得比較多,但是以計算為主。很多老師在外面都有自己的事業,而李志良就是純粹搞科研的一個老師。
一個認識他的人說:我聽說化學學院有老師自殺了,我想那一定是李老師。在有些人看來,李“太專注于學術了”,以至有點“迂腐”,“有時候有點古怪,甚至偏執”。他性格里面有種現在大學里面缺少的執著和認真,有人認為是“太過認真”。這導致了他在現實中有些格格不入。“不怎么適應這個社會,相對來講,為人處事很單純,特別天真。和同事領導相處不太好。”
也許他已經不理解這個世界的規則,當他無比認真地給出版社填寫選題申請表的時候,他可能根本沒意識到,書能否出版,和他的認真與否并無太大關系。
據介紹,因為專心于學術,李的生活能力比較差,因為妻子長年在深圳工作,妻子的姐姐過來照顧他和女兒的生活。
“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一切茍活者/都失去了…重量。”在課堂上,李志良曾把這句詩寫在了黑板上。李不是那種只對枯燥的實驗數據感興趣的理工科教授,而是“一個相當有激情的人”,“對科學的思考很有哲學韻味”。這樣的心靈是極其敏感的,但在現實中,他卻是“挺能忍的一個人”,別人和他說話生氣大聲他也不計較。
有學生這樣總結:是各方面的綜合壓力,造成了現在的結果。有太專注學術導致的性格缺陷,以及可能延伸出的家庭問題和人際關系問題,有處處碰壁、情郁其中卻不得發之于外的心理抑郁,還有現實的學術環境帶來的失望以至絕望。
有學生告訴記者,李志良老師有抑郁癥,曾經入院治療過。
沉默的大多數
在現實面前,總有個人不可逾越的困境和障礙。某種程度上,中國教育體制現狀導致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在縮小。這可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但確實給一些知識分子造成了困擾。
“李志良老師是重慶大學優秀的教授,學術造詣極高,但高山仰止,李老師雖與世
無爭,但在化工學院仍受到學霸排擠,李老師生活清貧,一心治學。但李老師面對同事關系,面對國內教育現狀,時有困頓,不可自拔。”這是百度詞條對李志良老師的介紹。
雖然李志良廣受學生愛戴,但奇怪的是,在采訪過程中,幾乎所有輾轉聯系到的采訪對象都像躲瘟疫一樣躲避記者。
一些學生和記者約好了采訪時間和地點,第二天卻又反悔,臨時爽約。有學生當記者要到約定的采訪地點打電話給他時,才告訴記者他正在去往成都的火車上。
李志良的一位研究生只告訴記者,他不想再談這件事情,聲音低沉。而他的一位師妹一開始同意和記者聊聊,并且約定了時間地點,后來聽說師兄不愿意接受采訪,她立刻也拒絕了采訪,理由是讓李老師入土為安,不再打擾他是最好的緬懷方式。
有學生接到記者約采訪的電話,推說自己正忙,再約時間通電話,到了約定時間并不接電話,再打永遠不接。在重大化工學院從本科一直讀到博士的人告訴記者自己一點都不了解李志良老師,相當于不認識,所以無法接受采訪,卻有后來接受采訪的人告訴記者,該博士對李老師的了解起碼比自己多。
開始幾天記者一直覺得莫名其妙,直到一位前年碩士畢業留校的輔導員聲稱,學校有規定,采訪要通過宣傳部統一安排,他不方便私下接受記者采訪。后來不斷有學生以這個理由拒絕記者的采訪。
當日出警的派出所也告訴記者采訪他們也要通過重慶大學宣傳部。重慶大學宣傳部則以放假師生都出行不好協調把采訪時間推到了“開學以后再說吧”。
李志良的幾位同事和同門也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當采訪終于有所突破,愿意接受采訪并幫記者聯系了多人的采訪對象告訴記者,他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對李老師的感情。他也希望記者能理解不愿意說的人,畢竟涉及畢業等等諸多問題。不否認有學生不接受采訪是不愿意再提起傷心事,想李老師早日入土為安,或者為尊者諱,怕說的什么有損老師形象。但對很大一部分人來說,也許主要是對老師的愛戴,還敵不過對自己的擔心,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不想去關心他跳樓的原因,不想,一點也不想。我只感覺到心里的真切的難受,感覺到真正的懷念,懷念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個真正的從事研究的人,一個做事認真嚴謹的人,他所具有的這一切我想也是處于這個浮躁時代的人都應該懷念的東西。”這是網絡流傳很廣的悼念李志良老師的文章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