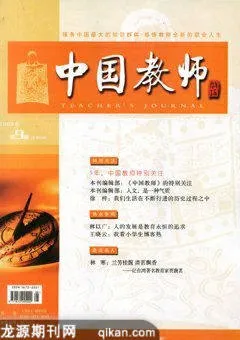我們生活在不斷行進的歷史過程之中
《中國教師》創刊5周年之日,也是我為她的“教海鉤沉”寫作屆滿1年之時。我與《中國教師》的結緣,是因為主編勞凱聲教授盛情邀約我為“教海鉤沉”專欄撰稿。當時他叮嚀最殷的是,希望通過這個欄目,向廣大教師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教育的知識,以提升廣大教師的文化素養和人文素質。
在商品經濟日益浸透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當今社會,功利成了這個時代的偶像,財富成為眾生追逐的目標,“所有的權力都必須為之服務,所有有才智的人都宣誓為之效忠。”擁有財富的多少,成了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尺度,成了判斷人生是成功還是失敗、是榮耀還是屈辱的標準。改革開放以來短短30年的人生沉浮和世象變化,人們已經能夠很清楚地意識到,那些距離金錢最近的職業、崗位和學科,是最能獲得財富、也是“前程遠大”的職業、崗位和學科;而人文教育、文化素質,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則被視為迂遠而疏闊。這從30年來高考熱門專業和學科的變遷,就可以窺見一斑。優秀的考生,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往往報考的是文史,80年代中后期之后,則集中于經濟、管理和法律,現在則群趨金融、IT、生物工程等熱門專業。
我并不打算以“崇高”的名義,實施道德的“暴政”;不愿指斥為著直接的功利目的、學習單一的專業化的技能,畢竟學習是有成本的,資源不是無限的;更不是鼓勵人們群趨文史之學,畢竟當代社會給予傳統學科的空間是有限的。我只是想說明,為現實功利而學習的癥結在于,它從謀求物質財富、追逐榮譽出發,盡管也會心無旁騖,專注于此,但只是學習特定的或有用的知識,那些實際上關聯、看似不相干的知識,絕不涉獵。而且一旦認為能夠獲得自己希求的功利,一旦認為自己拿到了能進入財富之門的敲門磚之后,便迅即停止了學習,乃至拋棄已有的知識。這樣不僅會使自己的知識結構狹隘,而且會使自己的精神世界猥瑣。過窄的專業學習所導致的心靈的貧困和心胸的狹隘,對價值的漠視和對知識的短視,二者互為因果,惡性循環。
迂遠而疏闊的歷史,就這樣被很多人漠視了。實際上,對于《中國教師》的廣大讀者來說,了解歷史絕對必要。我們總是說我們生活在現在,可是嚴格說來,現在并不存在,或者說它不是固定的。現在是不斷運動、變化的一個點,轉瞬即逝。就在我們說它是現在的時候,它已經成了過去。我們做的任何一件事、說的任何一句話,做完或說完之后,就進入了歷史的序列中。甚至就在我們做這個動作時,前一個動作已經成了過去;說這個字的時候,上一個字已經成了過去。所以,與其說我們生活在現在,不如說我們生活在不斷行進的歷史過程之中。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乃至現在在哪里,境況如何,都只能在歷史中得到解釋。如果沒有歷史,沒有包括剛剛逝去的所有過去支撐著我們的記憶和精神世界,我們就會一無所知。不必說遙遠的未來,就連剛進來的那扇門也找不到。我們就會好似生活在無底的、黑暗的深淵中一樣,前瞻了了,后顧茫茫,不知道自己從哪里來,更不知道自己向何處去。正是因為有了歷史,我們才超越了人生百年的短暫,獲得了深長的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直言之,是歷史延長了我們的生命,并且使我們的人生有目標,有意義。
歷史知識極其廣泛,中國教育的歷史和文化異常豐富,所以,我們的介紹必須而且只能有所選擇。只有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仍有影響的傳統,才是活的傳統;只有那些構筑我們知識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文化,才能豐富我們的生活,滋養我們的生命。基于這樣的考慮,我選擇了《說“老師”》《說“先生”》《說“師范”》《師傅與師父》以及《木鐸金聲的由來》《“天地君親師”的源流》《“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淵源》等論題,希望它們能貼近廣大教師的生活,引發廣大教師對古典文化的興味,并由此浸淫于其中,日與性成,習與漸長,日就月將,涵養純熟,成為一個既有一定專業知識、又有較高文化底蘊的合格的現代中國教師。
我所做的,無論是與勞主編的期望還是我自己的設想之間,都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希望在今后的寫作過程中,得到廣大讀者更多的支持,把你們的意見和想了解的問題告訴我,以便“教海鉤沉”對廣大教師真正有所助益。
(責任編輯:張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