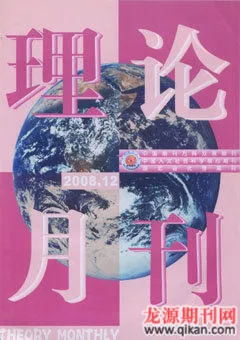意識形態與主體的生成
摘要:意識形態與人的主體性生成密切相關。意識形態通過身份建構、語言教化和“主義”話語建構人的主體性。
關鍵詞:意識形態; 主體; 生成
中圖分類號:B0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8)12-0045-03
意識形態是一個團體、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時代的主導價值觀與核心價值觀,是塑造社會性格與思想觀念的文化力量。意識形態兼具霸權與教化兩種特性:意識形態霸權規定了人們“不能想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意識形態教化規定了人們“應該想什么”、“應該做什么”。通過意識形態霸權的禁忌,通過意識形態教化的灌輸,社會塑造了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主體”。意識形態塑造人的主體性的機制或途徑是什么呢?本文認為,意識形態通過身份建構、語言教化與“主義”話語建構了人的主體性。
一、 身份建構
“我是誰?”這一問題的提出,標志著個體自我意識的形成,標志著個體主體性開始確立。而法國哲學家路易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認為,意識形態正是通過塑造個體的自我意識完成了“把個體變為主體”的過程。“意識形態‘起作用’或‘發揮功能’的方式是通過我稱之為傳喚或呼喚的那種非常明確的作用,在個人中間‘招募’主體(它招募所有的個人)或把個人‘改造’成主體(它改造所有的個人)。”[1]“主體是構成所有意識形態的基本范疇”,[1]“所有意識形態都通過主體這個范疇發揮的功能,把具體的個人呼喚或傳喚為具體的主體。”[1]阿爾都塞甚至認為,“沒有不借助于意識形態并在意識形態中存在的實踐;沒有不借助于主體并為了這些主體而存在的意識形態。”[1]需要說明的是,阿爾都塞使意識形態概念發生了重大轉向,使意識形態從表示主觀思想的觀念變成了一個客觀的社會領域。在阿爾都塞那里,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是機構性的,然后才能被看成是和意識有關的事情。”[1]可見,在阿爾都塞那里,意識形態彌漫于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成為人自身的組成部分。阿爾都塞不僅揭示了意識形態通過對個體自我意識與身份認同的建構把“個體變成主體”的過程,[1]而且還論證了意識形態、主體與實踐之間的內在統一性,揭示了“主體性”的實質是“意識形態”的主體性。
當代英國學者進一步揭示了身份建構在意識形態與主體(性)生成過程中的作用機制。英國學者J·費斯克(John·Fiske)認為,意識形態不僅可以在國家和社會的宏觀層面發揮作用,而且也可以在個體的微觀層面運作。費斯克指出,個體與主體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要理解意識形態對個體的影響必須用“主體觀念代替個體觀念”。“個體為自然所產生,主體為文化所產生;個體理論關注人們之間的差異性并將這些差異解釋為自然本性。相反,主體理論則關注人們在社會中的共通經驗,這種經驗是解釋(我們認為)我們是誰的最卓有成效的方式。”[2]因此,“主體是某種社會建構而不是一個自然物。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女性可能具備男子主體性(即她可以通過父權意識形態來理解世界、她自己以及她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同樣地,一個黑人可能有白人的主體性,工人階級可能有中產階級的主體性。”[2]“在實踐中被自然化了的意識形態標準不僅僅為我們構造了世界觀,也構造了我們的自我觀、我們的身份意識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我們同他人、同社會的關系意識。于是,我們每個人都作為意識形態中的一個主體被構造”。[2]意識形態通過賦予人們解釋世界的特定視角與意義的方式來建構人的主體性即社會身份,從而將權力與知識聯合起來。“意識形態在引導我們以某些方式解釋世界的同時,就建構起了我們的主體性,亦即社會身份,它是權力和知識之關聯結構的組成部分。單個主體在政治和心理上的社會化,有助于維持一種意識形態,有助于保全其解讀和觀察世界的方式,有助于將其特定的意義賦予我們所解讀和觀察的世界。”[3]
可見,意識形態是通過建構人們的世界觀、自我意識、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使人們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的過程中形成自身的主體性。
二、 語言教化
意識形態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塑造人們的身份意識的呢?語言。“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是很密切的,通過語言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某種意識形態。”[4]意識形態正是通過語言載體把自然人教化成主體。“主體與客體范疇能夠涵蓋我們所要思考的一切。但對這對范疇的思考最終無不追溯到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和理解。”[5]原因在于,人是通過語言認識客體世界并與之打交道的。整個客體世界都飄浮在語言中。此外,從人的成長過程看,個體從自然人成長為社會人、文化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以語言為媒介的教化。“語言在實際運用中(包括在傳授中)總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以一定的意識形態為導向的。這就是說,傳授一種空洞的語言是不可能的,傳授語言的過程本質上就是傳授意識形態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教化的過程也就是接受意識形態的過程。意識形態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一個人進入并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的許可證書。一個人只有通過教化與一種意識形態認同,才可以與以這種意識形態為主導思想的社會認同。”[5]正如澳大利亞學者安德魯·文森特(A Vincent)所說:“我們生活于語言世界中,語言決定我們是誰、是什么。”[6]語言教化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某種意識形態的支配,個人的主體性的實質是意識形態主體性。“無論是認識對象、認識主體還是整個認識過程,都飄浮在意識形態中。我們常常加以夸大的主體性實質上乃是意識形態主體性,認識者不過是意識形態的傳聲簡或翻譯者罷了。只要人們還不認為自己生活在意識形態中,他們的主體性就是虛假的;反之,當他們開始反思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識形態時,他們的真實的主體性才開始顯現出來。”[7]可見,意識形態與人的主體性之間存在悖論:一方面,人的主體性是意識形態建構的;另一方面,人的主體性又表現為對意識形態的反思與超越。
怎樣超越這一悖論呢?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Geertz,c.)對意識形態的利益論與張力論研究進路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意識形態研究的符號論進路。格爾茨認為,“對意識形態的社會決定因素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兩種方法:利益論(the interest theory)與張力論(the strain theory)。對前者而言,意識形態是面具和武器;對后者而言,意識形態是癥狀及處方。在利益論中,意識形態見解被置于為好處進行的普遍斗爭的背景之中;在張力論中,則被看成是為糾正社會心理的不平衡而進行的長期努力。前者把它看做人追逐權力的工具;后者把它看做對焦慮的逃離。”[8]利益論是由馬克思開創的社會學研究進路,關注和解決社會利益爭斗中的思想觀念問題。個體在融入社會獲得經濟獨立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對利益發表見解的問題。正是在利益的生產、分配與斗爭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將人塑造成社會歷史的主體。同時,正是在對利益問題進行反思與批判的過程中,人們能夠最真切地感受到意識形態對人的束縛與控制,從而使人們能夠將利益分析與意識形態批判結合起來,超越意識形態的統治,體現人的主體性。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將意識形態僅僅理解為在社會利益沖突中為爭奪權力和利益而采用的“觀念武器”是有局限性的。這種局限性,一方面在于“它的理論手段已經過于粗陋,不能應付由它所發現的社會、心理及文化因素之間互動作用的復雜性”;另一方面,當把意識形態僅僅局限于論戰中的思想觀念時,忽視了意識形態的其他社會功能,即“確定(或模糊)社會分類,穩定(或擾亂)社會期待,維護(或破壞)社會規范,加強(或削弱)社會認同,緩和(或加劇)社會緊張”,[8]從而縮小了意識形態分析的知識范圍。因此,意識形態在建構人的主體性的社會維度方面是多功能的、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
與利益問題密切相關的是人的欲望與心理問題。意識形態不僅在主體形成的社會維度產生作用,而且在塑造主體的欲望與心理方面起到控制、激發與治療的作用。格爾茨認為,由于“社會持久的不良整合”造成了“無所不在”和“不可取消”的“社會磨擦”。[8]這種磨擦或社會張力在個體人格層面上表現為心理張力、“個人的不安全感”。“社會的不完善與性格沖突正是在社會角色的經驗中被發現并被互相加劇”,而“意識形態是對社會角色的模式化緊張的模式化反應。”意識形態為由社會失衡造成的情感波動提供了一個“象征性的發泄口”。[8]
意識形態是如何協調人的主體性的社會維度與心理維度的呢?是通過文化符號建構出來的意義系統與意義模式實現的。事實上,在真實的社會交往與社會結構中,利益問題、心理問題和文化問題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而作為文化載體的符號彌漫于整個社會場域,滲透在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利益活動和心理活動之中。符號不僅成為聯系、協調人的主體性的社會維度與心理維度的紐帶與中介,而且作為文化與消費的意義體系取得了當代消費社會的統治地位。對消費社會如何運用符號及景觀激發人的欲望進行反思,對“無休止的誘惑”作為“主導性的社會關系,成為了富足社會的整體組織原則”進行批判,[9]有助于人們對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保持一種理性的自覺和價值的批判。
三、 “主義”話語
意識形態往往表現為“主義”話語。所謂“主義”話語是帶價值論斷的社會化思想言論,這些論述以某種知識學(科學)的論證來加強價值論斷的正當性,以此促成不同程度的社會化行為;并不是任何思想論述都具“主義”話語的性質,只有當某種思想話語進入社會化推論和訴求時,或當某種由個體提出的思想論述要求社會法權時,思想論述方轉換為“主義”話語;一旦“主義”話語獲得社會法權,就成為意識形態。因此,必須區分三個不同層次的話語:個體言說,“主義”論述和意識形態。[10]作為意識形態的“主義”話語是由哪些要素構成的呢?“任何一種‘主義’都包含了至少三種在邏輯上不能相互還原的成分,其一是‘主義者’所追求的價值目的,其二是‘主義者’所認知的客觀聯系,或曰道理,其三是‘主義者’所設計的操作方案”。[11]可見,價值、道理、方案,構成了“主義”話語的三個異質性要素。這三個要素還可以表述為“是(解釋世界)”、“應該(規范世界)”、“做(改變世界)”。[12]
人們為什么需要作為意識形態的“主義”話語呢?美國學者雷迅馬(Michael E. Latham)認為,“有意識形態要比沒有意識形態使人們更容易地對待現實。意識形態為理解復雜的現實提供簡單的模式。意識形態指示著歷史運動的方向。意識形態靠言辭賦予行動以正當性。”[13]這說明,意識形態在人們成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過程中,起到了“認識世界的面目,闡明現狀的意義,指引前進的方向,提供解決危機的方案,強化民眾的團結,進行必要的社會動員”的作用。[14]作為“主義”話語的意識形態之所以會產生,原因還在于“任何的意識形態必須有著形成的長久過程,而且必須處理與人類攸關的問題,它的產生和死亡都與它解決問題的能力緊密相結合。”[15]也就是說,意識形態表現為“主義”,而其實際價值和功能在于解決與處理“與人類攸關的問題”,是“源自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產物”。[15]所以,無論人們是否喜歡意識形態,都必須面對而無法逃避。當意識形態“開始介入我們的日常運作后,便成了我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在一連串形成和有效解決我們主要問題的發展過程之中,意識形態才得以獲得其完備的形式,用以保障我們的利益、使我們生存。但是,假如它不能推展它的權力于上述對象或者獲得實踐之機會,便將成為過時之物,或者被忽略遺忘,或者轉化成提供有限幫助之物。若是前者,它將被解消,而且被一個新崛起的意識形態所取代;若是后者,則將轉型,包揉在新繼起的意識形態而成為其中的因子。無論如何,完全自意識形態中解放的觀念是天真的。在此,我們必須接受曼海姆(Mannheim)所提出的悖論:沒有人可以逃離意識形態。”[15]
綜上所述,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消亡、轉型與變遷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據,即與它在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時的作用與能力相關。意識形態集“主義”與“問題”于一身。人可以選擇或拒斥“主義”,卻無法回避與逃脫與人類攸關“問題”的控制,如幸福與命運、自由與秩序、生存與發展、生與死等問題。正是因為人類必須面對和解決自身存在與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人類才需要意識形態,以便在矛盾與兩難中進行選擇。因而,人可以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作出選擇,卻無法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意識形態中完全解放出來。
參考文獻:
[1]陳越.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Z].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英]J.費斯克.英國文化研究與電視(上)[J].世界電影,2000,(4).
[3][英]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4][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精校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俞吾金.意識形態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澳]安德魯·文森特.現代政治意識形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7]俞吾金.從抽象認識論到意識形態批判[J].天津社會科學,1995,(5).
[8][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
[9][法]吉爾利波維茨基.空虛時代——論當代個人主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10]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11]徐長福.“主義”三元素:價值、道理、方案——對人文社會學說性質的審查[J].求是學刊,2002,(3).
[12]徐長福.是、應該與做——對解釋世界、規范世界與改變世界諸問題的形上離析[J].哲學動態,2001,(10).
[13][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14]季廣茂.意識形態視域中的現代話語轉型與文學觀念嬗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5]陳文團.意識形態教育的貧困[M].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9.
責任編輯 劉鳳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