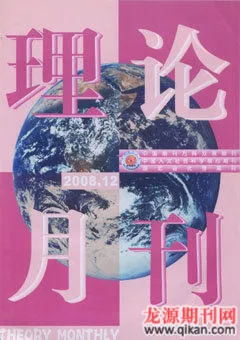論關(guān)學(xué)的精神特質(zhì)
摘要:關(guān)學(xué)是宋明理學(xué)中一個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學(xué)術(shù)流派。盡管在關(guān)學(xué)的流變傳承中學(xué)者們的學(xué)術(shù)觀點屢有變化,但在學(xué)術(shù)思想和學(xué)風(fēng)方面卻體現(xiàn)出共同的精神特質(zhì)和一脈相承的精神傳統(tǒng)。關(guān)學(xué)的精神特質(zhì)表現(xiàn)為:“經(jīng)世致用,篤行踐履”的務(wù)實精神;“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和合精神;“學(xué)古力行,篤志好禮”的道德實踐精神;“關(guān)注生民,以天下為念”的愛國精神;剛毅不屈,不畏艱苦的進取精神。關(guān)學(xué)的精神特質(zhì)是鮮活的,在當(dāng)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關(guān)鍵詞:關(guān)學(xué); 關(guān)學(xué)精神; 精神特質(zhì)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8)12-0059-03
“關(guān)學(xué)”即關(guān)中(函谷關(guān)以西,散關(guān)以東)之學(xué),因其創(chuàng)始人張載是關(guān)中人,“關(guān)學(xué)”各弟子也多為關(guān)中人,如高陵的呂涇野,長安的馮存吾,周至的李二曲等,故稱之為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關(guān)學(xué)是宋明理學(xué)思想發(fā)展中重要的一個支脈,其間雖然也經(jīng)歷過衰落,但隨著理學(xué)思潮的發(fā)展,它自身始終保持著一個相對獨立的傳承脈絡(luò),而且在其傳承的過程中涌現(xiàn)出眾多的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宋代張載之后,關(guān)學(xué)思想大體呈現(xiàn)兩種趨向:其一是向洛學(xué)轉(zhuǎn)化的趨向,以藍田呂大忠(生卒年不祥,字晉伯)、呂大均(1030-1082,字和叔)、呂大臨(1042-1090,字與叔),即“藍田三呂”為代表。他們吸取了洛學(xué)“涵泳義理”,空說心性的特點,但卻始終沒有離棄關(guān)學(xué)“學(xué)貴有用”、“躬行禮教”的主旨;其二是關(guān)學(xué)的“正傳”發(fā)展,以長安人李復(fù)(1052-1128,字履中)為代表,他繼承、弘揚并進一步推進了張載的“氣本論”思想。金元時期,先有楊奐的“戶縣之學(xué)”,后有楊天德,楊恭懿,楊寅子孫三代所創(chuàng)的“高陵之學(xué)”繼續(xù)倡導(dǎo)關(guān)學(xué)學(xué)統(tǒng),使關(guān)學(xué)在程朱理學(xué)一統(tǒng)天下的歷史條件下得以承繼。到了明代,伴隨王陽明掀起的思想變革風(fēng)潮,關(guān)中地區(qū)涌現(xiàn)出一大批理學(xué)家,關(guān)學(xué)開始中興。其中高陵人呂柟(1479-1542,字仲木,號涇野)和長安人馮從吾(1556-1626,字仲好,號少墟)成為當(dāng)時的理學(xué)大儒,其門生幾乎遍及關(guān)中及東南。呂柟倡導(dǎo)“仁心說”,公開反對王陽明的抽象“良知”,突出強調(diào)要從實處下功夫,從現(xiàn)實的禮教做起以達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精神境界,顯示出關(guān)學(xué)不同于王學(xué)的現(xiàn)實品格。馮從吾沿著呂柟的思路,提出“善心說”,力辟陽明學(xué)中佛教“性空”的弊端,反對王學(xué)融合二氏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旨,承襲了張載關(guān)學(xué)堅決排佛、注重實踐的關(guān)學(xué)傳統(tǒng)。明清之際被稱為清初三大名儒之一的周至人李颙(1627-1705,字中孚,號二曲)以昌明關(guān)學(xué)為己任,從“明道救世”的政治目的出發(fā),進一步倡導(dǎo)“學(xué)貴有用”和“下學(xué)”、“實學(xué)”的關(guān)學(xué)學(xué)風(fēng),明確主張實行“明體適用”之學(xué)。李颙的學(xué)生戶縣人王心敬(1656-1738,字爾緝,號豐川)以“全體必兼大用,真體必兼實功”為信條,敬義夾持,知行并進,保持了關(guān)學(xué)的“崇儒”宗旨和實學(xué)學(xué)風(fēng)。近代以降,隨著西學(xué)的漸入,關(guān)學(xué)也同整個宋明理學(xué)一樣逐漸走向了終結(jié)。
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是中國哲學(xué)發(fā)展歷史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學(xué)派,盡管研究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的著作很多,但這些論著多著眼于歷史的考證,著眼于對積淀已久的歷史史實和歷史人物的挖掘和展現(xiàn),而對于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一脈相承的精神傳統(tǒng),對于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在學(xué)術(shù)思想和學(xué)風(fēng)方面所體現(xiàn)的共同的精神特質(zhì)挖掘的還不夠深入。因此,要將關(guān)學(xué)研究進一步推向前進,就應(yīng)該吸收前輩學(xué)者的研究成果,繼往開來,充分發(fā)掘和準確把握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一貫的精神傳統(tǒng),開拓出關(guān)學(xué)研究的新境界。因而,關(guān)學(xué)精神的研究在中國哲學(xué)史以及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
那么,何謂關(guān)學(xué)精神?關(guān)學(xué)精神是指關(guān)學(xué)區(qū)別于洛學(xué)、閩學(xué)以及其他相關(guān)地方性文化的精神方向和精神追求。關(guān)學(xué)自宋代張載開啟,一直延續(xù)到明清之際,經(jīng)歷了近千年的歷史傳承,表現(xiàn)出鮮明的精神特質(zhì)。主要體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 “經(jīng)世致用,篤行踐履”的務(wù)實精神
“經(jīng)世致用,篤行踐履”的務(wù)實精神是關(guān)學(xué)最顯著的特點。這種務(wù)實精神表現(xiàn)為重視對現(xiàn)實問題,如軍事、兵法、天文、生物、醫(yī)學(xué)、水利、教育、禮儀等的研究和對自然科學(xué)和實際問題的探討。關(guān)學(xué)宗師張載早年就“以攘患保民為己任”,熱心于談兵議邊,后來專心從事理學(xué)研究時仍然關(guān)心當(dāng)時的軍事和政治,從不把“道學(xué)”與“政術(shù)”看作互不相干的“二事”。退居橫渠后,他親置井田,“正經(jīng)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xué)校,成禮俗,救災(zāi)恤患,敦本抑末”[1]表現(xiàn)出對現(xiàn)實的強烈關(guān)注。張載的弟子李復(fù)在青少年時代就“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后投師于張載門下,受其影響,對“天文地理”、“易經(jīng)”、“律呂”、“禮樂”、“郊社”、“兵法”均有很深的研究。在被調(diào)入朝廷賢殿修撰期間,他大量閱讀了“天文、地理”、“易經(jīng)”歷律“兵法”等書,寫下了很多著作。由于當(dāng)時百姓對“日食”、“月食”都有一種迷信感,他便寫了《論月食》、《震雷記》以駁斥和解說。同樣,宋元時期的其他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也承繼了這樣的務(wù)實學(xué)風(fēng),他們從“志于用世”出發(fā)治學(xué),指陳時病,并力學(xué)博綜于史學(xué)、歷書、天文、古跡、經(jīng)濟等,形成了“真履實踐”的關(guān)學(xué)主旨。之后,明代關(guān)學(xué)的集大成者呂柟也立志“文必載道,行必顧言”[2](《關(guān)學(xué)編·涇野呂先生》),倡導(dǎo)“學(xué)貴于力行而知要”,反對時人分舉業(yè)與圣學(xué)為二,認為學(xué)問應(yīng)“從下學(xué)做起”,應(yīng)把“做事”與“做學(xué)”統(tǒng)一起來。謫居解州時,他一方面在書院講學(xué),一方面恤煢減役,勸農(nóng)課桑,筑堤開渠,興修水利。他說,“今人把事做事,學(xué)做學(xué),分作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xué),即學(xué)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3]明代另一位關(guān)學(xué)代表人物馮從吾同樣力倡“困而能學(xué)”,“學(xué)而能行”的習(xí)性學(xué)風(fēng),認為知識能運用于實踐,才是真學(xué)問,他以學(xué)射為例,闡述學(xué)行結(jié)合的道理,說“學(xué)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不能射,其所談未必當(dāng)。”[4]到了明清之際,關(guān)學(xué)大儒李颙更以“開物成務(wù),康濟群生”為己任,提出“儒者之學(xué),明體適用之學(xué)也”的重要思想。他說:“明體而不適用,便是腐儒;適用而不明體,便是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便是異端。[2](《關(guān)學(xué)編·二曲李先生》)又說:“道不虛談,學(xué)貴實效”;“立身要有德也,用世要有功業(yè)。”[5]為了經(jīng)世實用,他于政治、軍事、律令、農(nóng)田、水利、天文、地理無不廣泛涉獵。其后的王心敬繼續(xù)發(fā)揚關(guān)學(xué)“經(jīng)世致用”精神,反對空談玄虛之說。他注意研究農(nóng)業(yè),推崇汜勝之的“區(qū)田法”,著有《區(qū)田圃田說》,推廣農(nóng)業(yè)技術(shù)。他還著有《井利說》一文,從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角度,對井灌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可見,在關(guān)學(xué)思想發(fā)展的幾百年間,其“實學(xué)”的學(xué)旨和務(wù)實的精神一直貫穿于始終。
二、 “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和合精神
“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和合精神也是關(guān)學(xué)一貫具有的精神特質(zhì)。關(guān)學(xué)的和合精神主要體現(xiàn)于兩個方面:第一,關(guān)學(xué)特別強調(diào)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張載在創(chuàng)立關(guān)學(xué)之初,就以“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理想,批判當(dāng)時的章句之儒只注重對“人道”的應(yīng)用和對現(xiàn)實政治的適從,而忽視了對“天道”的探求,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他的氣一元的宇宙本體論。他認為“天人不須強分”,因為天人同本于氣,天人萬物都是氣的聚散而形成的,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雖形態(tài)各異,但都統(tǒng)一于氣,所以人和萬物之間應(yīng)當(dāng)是和諧的。這種精神在人類遭遇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的今天,顯得格外的先進和寶貴。在太虛即氣的前提下,張載把自然史和人類史看作彼此密不可分的同一氣化過程。他肯定人是“氣化”的最高產(chǎn)物,混然與天地中處,雖“予茲藐焉”,但“得其秀而最靈”。所以,人一旦產(chǎn)生,就成為整個自然、社會之主。張載在《西銘》開篇就講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6]在整個人類世界中,所有的人都與我同生于天地,人人都是同胞兄弟,因而人們之間相互親愛,既無壓迫,也無“爭訟”,大家和睦相處,達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太平”世界。張載弟子李復(fù)繼承師說,也明確指出“元氣”是產(chǎn)生萬物之本,“元氣既分,象數(shù)既形,萬物蕓蕓而生。”而且“我”與“物”一樣,同為氣生,不可相離,也同樣以元氣為基礎(chǔ)詮釋了天地人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第二,關(guān)學(xué)也強調(diào)人自身的身心和諧。張載提出“氣本論”思想的終極指向不在于建立宇宙本體論自身,而在于尋求一個寄“身心性命”于物外而又“不離日用常行內(nèi)”的超道德的理想境界,即儒家所一貫追求的“孔顏樂處”。這種樂不是樂于外物,而是進行人自身的認同,是自我意識到自身與萬物渾然一體而獲得的樂天安命的內(nèi)心感受。“天道”和“人道”都來源于太虛之氣,因而兩者是一致的,人的生死、貧富,社會的治亂、安危都是“天志”、“天道”,人只要不逆“天志”,順乎“天道”就可以獲得內(nèi)心的和諧,達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的真正自由的理想人格境界。之后呂柟的“仁心說”,馮從吾的“善心說”都是沿著這一思路,在人倫日用之常的修習(xí)中尋求天道性命之妙。李颙更是把“悔過自新”作為明道的唯一途徑,倡導(dǎo)人們通過對身心之過的檢討,“復(fù)反歸其天理”,追求人的身心統(tǒng)一和諧的自由境界。
三、 “學(xué)古力行,篤志好禮”的道德實踐精神
關(guān)中學(xué)者都以捍衛(wèi)儒術(shù)自任,特別重視躬行禮教的道德實踐,這是秦人民風(fēng)純樸,尊理重俗的歷史文化淵源。關(guān)學(xué)的創(chuàng)立者張載以“復(fù)三代之禮”為自己的理想,素來主張“以禮為教”,其學(xué)說也“以立禮為本”、“尊禮貴德”。他曾“知太常禮院”,做過禮官,明庶物,察人倫,“冠婚喪祭之禮”無所不精;學(xué)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zhì)之道”。擔(dān)任云巖縣令時,張載“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yǎng)老事長之義。”他終身“勉修古禮”,“教童子以灑掃應(yīng)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酒漿,以養(yǎng)遜弟”[2](《關(guān)學(xué)編·橫渠張先生》)在他的倡導(dǎo)之下,“相效復(fù)古者甚眾,關(guān)中風(fēng)俗為之大變。”張載的這種精神得到了后代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們的繼承和發(fā)揚。張載弟子“三呂”雖然后來投奔二程,其學(xué)說也逐漸“洛學(xué)化”,但他們始終沒有改變關(guān)學(xué)“躬行禮教”的主旨,論選舉、明兵制、行井田、制鄉(xiāng)約,明教化。呂大忠反復(fù)強調(diào)“修身為己之學(xué),不可不勉”,倡導(dǎo)從實際出發(fā),采用經(jīng)世致用的辦法修身養(yǎng)性,不斷提高治國之道。呂大鈞以“繼承孔孟之絕學(xué),闡明儒家禮治”為宗旨,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愛”禮教,還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編寫了《呂氏鄉(xiāng)約》、《鄉(xiāng)義》等,經(jīng)過推行,對改善關(guān)中風(fēng)俗起到了實際功效。明代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呂柟,著《禮問內(nèi)外篇》,還親自實施《呂氏鄉(xiāng)約》和《文公家禮》。任國子監(jiān)祭酒時期,以四書五經(jīng)及禮儀為教材,并常“取儀禮諸篇,令按圖習(xí)之”,貫徹“禮以立之,樂以和之”的教育方針,并把正心、修身、忠君、孝親作為道德教育的基本內(nèi)容,要求學(xué)生嚴格按照各種道德規(guī)范和禮節(jié)約束自己。馮從吾在關(guān)中書院講學(xué)時,也始終堅持德教為先的原則,提出“講學(xué)即講德”,制定《書院會約》,規(guī)定了各種禮儀,著力于培養(yǎng)“粹然之養(yǎng),卓越之識,特然之節(jié)”的真人品。李颙繼承關(guān)學(xué)傳統(tǒng),進一步闡發(fā)了張載“以禮教人”的思想。他提倡“悔過自新”,“為學(xué)修德”,主張培養(yǎng)“真儒”。他還從《禮記》中摘錄關(guān)于儒者的論述,寫了《儒學(xué)篇》,以作為“真儒”的行為規(guī)范要求。王心敬也力倡古禮,編寫《四禮寧儉篇》以教化人才,變化風(fēng)俗。正因如此,黃宗羲在《明儒學(xué)案》中明確指出“關(guān)學(xué)世所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7]
四、 “關(guān)注生民,以天下為念”的愛國精神
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的學(xué)者高舉“為生民立命”的旗幟,始終堅持高度關(guān)注國家、關(guān)注社會,關(guān)注百姓,始終保持“以天下為念”的愛國精神和憂國憂民的激情。這種愛國主義情愫深深地激勵著無數(shù)三秦兒女,在中國歷史上譜寫了一曲曲愛國主義的慷慨悲歌。張載“居恒以天下為念”,常“訪民疾苦”,在路上見了餓死的百姓,嘆息不止,終日對案不食。雖然仕途不順,但他始終關(guān)注著“陜北邊事”,曾多次為陜西路、涇原路的經(jīng)略使出謀獻策,力圖改變民間“貧富不均”、“士流困窮”的局面。呂柟早年也曾上書勸諫皇帝要“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天下中興。[2](《關(guān)學(xué)編·涇野呂先生》)后被貶為解州判官后,因知州死而無替,呂柟便代行州事。在代職期間,他減了役、勸農(nóng)桑、撫恤獨孤寡,興修水利,建“解梁書院”,聚鄉(xiāng)賢耆老修訂“教民榜”、行“呂氏鄉(xiāng)約”和“文公家禮”,民俗“翕然改之”。同樣是明代關(guān)學(xué)大儒的馮從吾也不顧個人安危,上書萬歷皇帝:“勿以天變?yōu)椴蛔阄罚鹨匀搜詾椴蛔阈簦鹨阅壳瓣贪矠榭墒选保瑒窕实凵傩锞魄谡拢⒘﹃惍?dāng)時“內(nèi)則旱荒盜賊,外則遼左危急”的局面,毅然“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義挽回其間。”后又講學(xué)城隍廟,“欲借此聯(lián)絡(luò)正人同志濟國也。”[2](《關(guān)學(xué)編·少墟馮先生》)愛國之情溢于言表。李颙面對明清之際更迭動蕩的社會現(xiàn)實,也立志救世濟時,發(fā)奮明道存心。他說:“吾輩須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闡往圣之絕旨以正人心,達則開萬世之太平以澤斯世。”[8]他時刻關(guān)心社會問題,著述切于時政,不務(wù)空言。這些都體現(xiàn)出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們炙熱的愛國之情。總之,關(guān)學(xué)始終堅持高度關(guān)注國家、社會和生民,積極參與社會的變革實踐,在實踐中豐富和發(fā)展自己的學(xué)問。他們保持高昂的愛國愛民、憂國憂民的激情,并將其作為做學(xué)問的內(nèi)在動力。無論是他們上疏議諫,還是出仕就職,或是設(shè)館講學(xué),無不洋溢著這樣的激情。
五、 剛毅不屈,不畏艱苦的進取精神
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大都富有高尚的氣節(jié)和德操,往往心存濟世之志,但不茍安于世,不與權(quán)貴同流合污,“既有濟世之大略,又多淡泊之情懷,不為權(quán)貴所脅,更無奴顏媚骨”。[9]他們大多因“學(xué)”而“官”,又因重氣節(jié)而辭(或罷)“官”而又專門為“學(xué)”,然而,無論是為“官”還是為“學(xué)”,他們始終保持高尚的節(jié)操,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自己的道德理想,表現(xiàn)出剛毅不屈,不畏艱苦的進取精神。張載居橫渠時,生活非常艱苦,“僅田數(shù)百畝供歲計”,但他卻“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坐于房中讀書思考,著書講學(xué),創(chuàng)立了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呂柟對當(dāng)時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十分不滿,先后上疏請武宗“入宮親政事,潛消禍本”、勸世宗興“大禮”,“勤學(xué)以為新政之助”,[10]幾乎被劉瑾殺了頭,被皇帝入了獄、貶了官。后歸居高陵,仍然筑“別墅”,建“書室”,“以會四方學(xué)者”。馮從吾由于看不慣萬歷皇帝那種“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fā)”,“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的腐敗作風(fēng),曾“疏請朝講”,惹惱了皇帝,被削籍歸家。“罷居二十六年”,創(chuàng)建關(guān)中書院,著書授徒,探討學(xué)術(shù)源流異同。生活在民族矛盾異常激烈的明清之際的李颙恪守遺民氣節(jié),拒絕仕于清廷,多次力辭“山林隱逸”之薦,斷拒“博學(xué)鴻儒”之征。他一心向往“武侯之偉略,陽明之武功”,當(dāng)復(fù)明滅清成為泡影時,他便歸隱故里,閉門沉研學(xué)術(shù)。雖然饑寒清苦,無所憑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關(guān)學(xué)為己任。在“事功”無望,直接“救世”不成的情況下,他精心制作了“悔過自新說”把他的愛國熱忱深深的隱藏在這一理論核心中。因此,黃宗羲曾稱贊關(guān)學(xué)學(xué)者“多以氣節(jié)著,風(fēng)土之厚,而又加之學(xué)問者也。”關(guān)學(xué)所表現(xiàn)出的這種剛毅不屈,不畏艱苦的進取精神,對于我們在相對落后的經(jīng)濟條件下建設(shè)、發(fā)展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guān)學(xué)作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東西,但是關(guān)學(xué)所體現(xiàn)出的精神特質(zhì)卻是鮮活的,并且經(jīng)過時代的轉(zhuǎn)換仍然可以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事業(yè),為我們更好的構(gòu)建和諧社會而服務(wù)。關(guān)學(xué)學(xué)派所一以貫之的“經(jīng)世致用,篤行踐履”的務(wù)實精神、“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和合精神、“學(xué)古力行,篤志好禮”的道德實踐精神、“關(guān)注生民,以天下為念”的愛國精神以及剛毅不屈,不畏艱苦的進取精神在北宋以后歷經(jīng)元、明、清各代,直至今日仍影響著關(guān)中地區(qū)的民風(fēng)民俗和社會的發(fā)展。就連“心學(xué)”的代表人物王陽明也說:“關(guān)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質(zhì),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guān)中之盛者也”。因此,今天開展關(guān)學(xué)研究,最關(guān)鍵的問題就是要充分展現(xiàn)出關(guān)學(xué)所特有的精神傳統(tǒng),努力從積極的方面和時代視角去總結(jié)、概括、提煉關(guān)學(xué)發(fā)展中所表現(xiàn)出的精神特質(zhì),更好地解決當(dāng)代社會中關(guān)學(xué)精神的繼承、弘揚、改造和轉(zhuǎn)換問題,并且以這種本土的精神傳統(tǒng)為主線,加強中國特色文化建設(shè),促進經(jīng)濟社會的全面發(fā)展。
參考文獻:
[1]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張載集·附錄[M].北京:中華書局,1978.
[2]馮從吾.關(guān)學(xué)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卷8)[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5]李鐘善.陜西歷代教育家評傳[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6]張載.張載集·正蒙·乾稱[M].北京:中華書局,1978.
[7]黃宗羲.明儒學(xué)案·師說·呂涇野柟[M].北京:中華書局,1985.
[8]王心敬.司牧寶鑒序[M],[清]李颙輯.司牧寶鑒,清道光29年本.
[9]劉學(xué)智.關(guān)學(xué)宗風(fēng):躬行禮教,崇尚氣節(jié)——從關(guān)中三李談起[J].陜西師范大學(xué)繼續(xù)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1,(2).
[10]趙馥潔.論關(guān)學(xué)的基本精神[J].西北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5,(6).
責(zé)任編輯 仝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