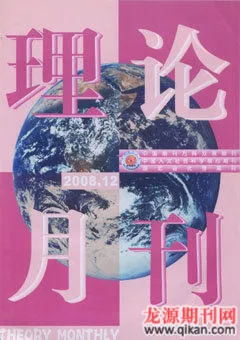現代農業與生態文明
摘要:現代農業能有效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它昭示著建設生態文明成為可能。當然,現代農業也不可避免地帶來某些負面效應,這是我們在發展現代農業時必須清醒認識的。
關鍵詞:現代農業; 生態文明; 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8)12-0139-04
現代農業的產生是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反思的成果。所謂現代農業,是以現代產業組織為紐帶,以現代產業理念為指導,以現代科技為支撐,橫跨一、二、三產業的涉農經濟體系。現代農業有別于傳統農業,不是因為方法與手段的不同,而是因為理念的差異,表現在現代農業在空間上的突破,由產中延伸到產前和產后。生態文明是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審視的產物,是一種后工業文明。可以說,目前生態環境的惡化當歸因于全球性工業化進程,因為工業經濟必須以消耗大量的資源為代價,而伴隨著以能源為主體的資源被耗竭同時的是過度的環境污染,從而把整個世界拋入一種博弈論意義上的“零和等局”結構之中,使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受到根本限制。占世界人口6%的美國居民維持他們令人羨慕的消費水平,需耗費大約1/3的世界礦物資源年產量,“我們無法讓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過上西方人現在過的生活,地球上的資源不足以做到這一點。”[1]要擺脫工業時代的困境,必須使“零和博弈”轉向“總和大于零的博弈”,也就是要另辟蹊徑。現代農業的崛起使知識資本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導致能源在資源結構中的地位相對弱化。現代農業知識所具有的可分享性和無限增值性特點,為我們消解和超越由于傳統資源的稀缺導致的“零和博弈”關系提供了可能。
一、 現代農業有利于建設生態文明
(一) 現代農業為生態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前提和基礎
任何一種經濟形態的發展都要消耗一定的資源,現代農業的崛起標志著作為社會發展所依賴前提的資源發生了一次歷史性變遷,這種變遷為緩解人與自然的矛盾、維系和改善生態環境提供了機遇。確立新資源觀,不僅是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內容,而且是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現代農業時代,以知識為主體的“軟資源”成為推動農業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因為它具有自然資源無法比擬的特征,如非消耗性、非稀缺性和非競爭性。所謂非消耗性,指與只能一次性使用的自然資源所不同的是,知識可以無損使用。所謂非稀缺性,指對于越用越少的自然資源來說,知識是相對豐富的。所謂非競爭性,指知識基本上不具排他性,可供多人同時享用。如托馬斯·杰佛孫在描述知識的非競爭性時說:“他從我這里接受一個想法,他自己接受了指導,并沒有減少我的,就象他在我的蠟燭前面點燃他的蠟燭,他接受了亮光,并沒有使我變暗。”現代農業知識一旦被發現并被公開,增加更多的使用者基本上沒有邊際成本。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過程中,關鍵是稀缺的自然資源如何支持從依賴稀缺資源的傳統農業可持續地發展到現代農業。實際上,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無限性是辯證的,自然資源的多與少、優與劣及利用的層次性,都是相對于人類的認識和利用水平而言的。現代農業對自然資源的理性利用,可以使其顯示出相對的無限性和可持續發展性。
工業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是追求GNP的增長,認為只需把經濟蛋糕做大,一切問題會迎刃而解。在狹隘經濟觀及其體制支配下,經濟增長中的負效應被放大了。企業在生產的同時將壞處轉嫁給社會,這種外部性效應現象是以增大產品的環境成本為代價的。因此,在理性上要揚棄增長論經濟學家把GNP視為衡量經濟的綜合指標的觀點,將環境成本計入生產成本,把企業行為的價值放在環境發展的宏大體系內考察;在實踐上需要一整套新技術替換傳統的技術。為了使有限的資源和環境得到持續利用,現代農業產生的指導思想就是在對人類行為和技術反思之后,通過綜合運用人類智慧,科學、合理地開發現有的和尚未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如生命科學中的基因工程和酶工程技術將為人類揭示生命的奧秘以及合理利用可更新的生物資源展示出廣闊的前景;海洋科學技術是以綜合高效開發各種海洋資源為目的的高新技術,它為生態文明建設開拓了廣闊的空間,因為海洋是生命的搖籃、資源的寶庫、人類的未來;環境科學技術是指減少環境污染和保持生態平衡的各項技術的總稱,如通過信息技術的使用而減少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交往帶來的交通工具的污染,用生物工程培育的優良品種可減少化肥和農藥的用量,污染控制、清潔生產和廢棄物的生物處理技術可最大限度地減少污染物的產生。因此,現代農業能有效解決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為生態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前提和基礎。
(二) 現代農業為重建人與自然系統的動態平衡提供了新的機制
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一個生態系統,系統內各要素之間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達到高度適應,使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處于相對穩定狀態,這就是生態平衡。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既有自然對人的制約,又有人對自然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勢必導致原有平衡狀態的改變,在自然失衡的同時也會危及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現代農業時代,人類在深刻把握自然規律和正確體認人類活動對自然的雙重影響的基礎上,提供適應自然規律的、有科學預見的、可調控的人類行為,促使人類活動對生態平衡的正面影響得以極大發揮。可以借助高新技術建立高效的信息反饋與控制系統,對環境進行有效監測,最大限度地減少現代農業對生態系統影響的不良后果。在幫助生態系統于進化過程中建立更合理的結構的同時,建立各種人工生態系統以重建于優化生態系統,使之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
(三) 現代農業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給予了人文環境支持
工業時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進步,使人類自我陶醉并不斷向自然界提出挑戰且陷入對物質利益的追逐中不能自拔,“使人成為一個具有巨大的力量但對于如何使用力量卻只有很小的判斷能力的現代野蠻人”。[2]物質進步和生態環境之間的不協調隨著物質的進步而加劇,使人類陷入普遍的困惑。人類的困境實質上是人類文明的危機、文化的危機,人與自然的不和諧根源于人類自身,即人的行為、觀念以及人與人關系的不協調。因而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并調整人的行為和觀念。理想的現代農業不是單向度的高科技,而應是科學技術、管理科學、人文科學三輪齊驅的系統工程,三者的有機整合成為任何一個追求有效性的社會不可或缺的工具理性,其中,滲透著價值關懷的人文科學,在保證人類行為的合目的性方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現代農業在帶來經濟增長模式、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變化的同時,將對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現代農業知識超越物質資料成為農業經濟的重要因素將引發價值觀革命,使人們從對物質財富的過分追求轉向對更高層次的精神財富的追求,由此帶動整個社會人文環境的改善,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提供良好的人文環境支持。
二、 現代農業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負面效應
建設生態文明,本質是要通過協調農業資源、生態資源與人類自身三者之間的關系,在實現當代人發展的同時,又要確保這種發展不以損害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即確保后代人發展的機會。而現代農業不可避免地帶來某些負面效應,這有悖于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優化人的生存狀態的旨歸,這是我們在選擇現代農業時必須清醒認識的。
(一) 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并達到極致
生物多樣性一般包括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多樣性,其價值首先是對于生物物種的意義,其次是對于人類生存的意義。從根本上說,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生態系統由簡單向復雜不斷演化的結果,它在基因、物種、生態系統內部所形成的多元互補關系,有助于物種的保存和優化。因為揚長補短式的互補結構,使得生物基因和物種能夠全息性地應對威脅其生存的外部環境。在現代農業時代,生物多樣性銳減,外來物種入侵,遺傳資源喪失。奧帆賽之前青島水域的滸苔已經使國人大跌眼鏡。有人認為,現代擁有商品的數量已遠遠超過物種的數量,而商品多樣性的增加恰恰是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一個直接結果,這是由于自然環境因一個生物物種的消失而減少了一種功能,就增加了發明新的能夠提供同樣功能的人造產品的迫切性。在物種漸次消失的過程中,生物技術功不可沒。基因工程自豪于可以跨越生物邊緣不能雜交的一切鴻溝,甚至在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互通有無,取長補短,滲透聯系。細胞工程得意于將不同物種或不同物種的生物細胞通過某種方法形成雜交細胞或雜交瘤,進而育成番茄馬鈴薯、向日豆、大豆米、山綿羊甚至克隆羊。生物技術的發展,引發育種技術上的革命,在動物、植物、微生物等所有物種間進行基因轉移和重組,極大地擴展了生物種質資源和雜種優勢的利用。生命的誕生是一個充滿各種可能的妙不可言的奇跡,然而克隆技術有可能根本改變人們對于生命的敬畏之情,把生命當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對象性規定。生命的祛魅,意味著人類由生命的守望者,變成了生命的主宰者和重塑者。對生命尊嚴的褻瀆,其后果必然是人的存在的危機。如果說,工業時代對生物多樣性的摧殘是粗暴的,但也直截了當,而現代農業時代對生物多樣性的摧殘卻披上了豐富物種多樣性的外衣,企圖通過基因復制將各物種的優點集于一身,并推而廣之。殊不知,物種多樣性喪失之后,再優良的品種也會面臨滅頂之災,因為,基因復制在生物界的大量應用必然會使生物演化出現一個逆向過程,即由復雜走向簡單。并且,基因復制過程中將使自身的缺陷超出個體范圍而被放大為整個物種的普遍缺陷,從而在總體上無法應對突發的災難,因為過于集中的優點恰恰是其缺點所在,正如最潔白的手帕最容易沾上污點一樣。
傳統經濟學的價值觀與發展觀及其指導下的極端的經濟主義、貪婪的功利主義、腐朽的享樂主義在發達國家登峰造極,同時為工業文明敲響了喪鐘。工業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產方式和高消費、高享受、高浪費的生活方式,使人類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會和反自然的性質,這是生態危機的直接根源。保羅·霍肯認為:“我們沒有去面對生態系統極限所提出的產出力的挑戰,而是暫時地繞過了這個問題,用更快的速度掠奪資源……這樣做不僅是借用了將來的資源,威脅到人類社會的長遠未來,而且還對這些生態領域中依賴同樣的資源生存的其他物種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個自然系統都在走向衰落。”[3]
(二) 人類生命的功能結構與人造環境的沖突造成人類退化危機
人類生命對人造環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人類生命的功能結構自形成至今,其變化不超過兩萬分之一,而人造環境卻大為改觀。進化論認為,當一個物種的功能結構不適應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又來不及作出基因調整時,就可能引起這一物種的滅亡。可以說,現代技術賴以成立的前提是需要的人為塑造,技術的開發進一步強化了人的需要,從而形成一個難以自拔的文明陷阱和文化怪圈。一切都是有代價的,在把一切活動技術化、秩序化的同時加快了能量的轉化和熵增大的過程。隨著環境熵值的提高,維持與創造新的秩序所花費的代價,也就越高。現代文明在使我們越來越少地消耗體力的同時,越來越多地消耗資源,導致人類生命結構與新的生活方式的沖突,伴隨而來的是各種文明病,而這些不完全歸咎于新陳代謝的紊亂,更多的當歸因于現代人造環境迥異于當初人類進化所要適應的環境所致。池田大作對人類的命運表示了關切:“如果我們繼續同自然的挑戰及室外的苦難相隔絕,我們很可能會失去機敏,作為生物的資質和耐久力就會衰退。如果我們由于某種原因,被迫從明天起就恢復更自然的生活,那就會感到非常困難。因為現代人當中恐怕不會有人適應這樣的生活。”[4]中國古人主張“天人合一”、“土木合一”,將“地氣”視為人的養生之源。老子曾以返樸歸真為美。可憂的是,我們正在步入瀝青之海、水泥之林、鋼鐵之間、網絡之中,我們的樸素尚有幾何?人的數字化存在使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談、心與心的碰撞轉化為人機對話,加之人類遷徙、人種混雜等促使人類進化因素的減少,從而使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面臨退化危機,因為社會屬性才是人的本質屬性。另外,就潛能而言,人類的智力資源也許是無限的,但人畢竟是復雜的有限之物,對智力資源的無限開發有可能導致非健全人類的產生。不必說生態失調產生的生態流民有引發動蕩的可能,更不用說核輻射與SARS對人類報復的現實。
三、 現代農業時代建設生態文明的思路
現代農業的崛起,將我們拋入一種全新的生存境遇之中,需要我們建構一種同樣是全新的生存方式和發展模式。然而,“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正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5]因此,對于如何建設生態文明,目前只能在觀念層面、實踐層面和制度層面上提出幾種可能的思路。
(一) 樹立生態意識
現代農業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而知識來源于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和對自然奧秘的揭示。人類知識的全面性與豐富性只能建立在自然界事物本身的全面性、多樣性和豐富性基礎上,任何對生物物種及其平衡系統的破壞,就是對人類可能具有的知識資源的破壞,因而保護物種多樣性對現代農業的發展而言具有本源性意義。生物多樣性受到的威脅,昭示著被馬爾庫塞稱為“技術時代舒舒服服的奴隸”的現代人在征服自然的同時反被自然所征服。這種雙向異化根源于人與自然愈益疏遠的分裂,凸顯了現代文明的悖論:追求理想家園卻破壞了現實家園。因此要重新體認自然資源存量的有限性、分布的地域性、結構的有機性和利用的非逆性等特點,重構自然資源觀,使生態意識滲透于人們的現實中以改變生活方式。所謂生態意識主要指生態價值意識、生態憂患意識和人與生態共存意識,它內涵著一種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價值定位或理論預設,昭示的是整體、系統和聯系的觀念。
自然界整體結構的動態平衡是整個地球生命賴以生存的支持系統,但超過生態閾限之后就可能導致整個支持系統的崩潰。具有二重性存在的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受自然整體動態結構平衡的限制,并構成其實踐行為的絕對限度。而人又是社會的存在,主體性是其本質,他必須能動地改造自然才能存在。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以滿足需要的基本樣式被稱為生活方式,人與自然的關系狀態和人與社會的關系狀態往往決定著人的生活方式。在征服自然能力增強的同時,人類對自然的外在感也不斷增強,以個性化為特色的生活方式包含了一些共同的生活選擇和預期,結果是人的存在被物化了,物質存在卻被個人化了。人與自然的對立和人與社會的對立促使人們形成一種以社會對物質的無限商品化轉換和人對物質的無限占有為目標的生活方式,最終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的普遍困惑。環境問題的凸顯,使人類向自然以及個人向社會的回歸成為一種優勢需要和重要生活目標,使生態意識的確立成為必要,也使價值目標的重建成為可能。過去,我們通常認為,某個物種的滅絕對其它物種不會有太大影響,實際上系統中每個物種的數量都存在一個臨界值,超越之后它的數量會不可遏制地減少,甚至導致生態系統的全面退化。地球上滅絕的物種已經太多了,如果人類不盡早形成科學的生態意識,那么在滅絕物種的名單上,再添上一個小小的物種——人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既尊重人又尊重自然、既重視人類文化又重視自然生存、既重視文化價值又重視自然價值的生態倫理學,為我們重新體認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野與維度,它是可持續發展得以確立的學理依據或賴以成立的文化前提之一。生態科學與生態倫理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從生態科學的“是”,不能直接推出生態倫理的“應當”。這一認識,有助于我們重新指認與把握科學與倫理的辯證關系,消除科學與人文的絕對界限,并在一定條件下實現由事實到意義、由存在到價值的轉換。因此,我們承認自然價值時,要從更深層的涵義去理解體現人與人關系的生態倫理,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以自然界為中介折射出人與人的倫理關系。同時反對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規范拓展到人與一切自然物之間,因為如此推理在理論上會導致倫理學的非主體性和實踐上人獸行為等同的荒謬性。生態倫理使我們能夠正視自然生命的客觀存在,克服人類的統治主義和沙文主義,擺脫人類的“洞穴假象”,消除人類生存主導性的盲目性,避免再次落入困境。此外,要提倡道德的約束并使之成為人們選擇生活方式的重要驅動因素。可持續發展是立足于現實著眼于未來的,這個識度的提出是人類發展觀的革命,要使之變為實踐還需價值觀革命。只有樹立科學的生態意識,才能產生正確的價值觀,使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成為自覺行動。生態意識的價值導向就是深化人們的環境意識,它不是從純粹的功利角度闡發人對自然的依賴性,不是人類應對特殊生存境遇的權宜之計,而是更加強調從人之為人的本質內涵上詮釋人與自然和諧的根據,強調知行合一。
(二) 建設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是人類理性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并進而反思文明進程的產物,如果文明的結果是對人類自身存在的否定,那么這種文明的價值就值得懷疑。在生態文明視野內,自然對人而言不僅僅是一種手段性的存在,而是一種始源性和本然性的規定。人與自然的分離和對峙,只是理性視野的偏執造成的假象。這種批判性的理解為倫理價值視野投向整個生態系統提供了合法性。建設生態文明,意味著人對自我本根性的自覺追尋,是向本原的復歸,從而自然界及其規定對人來說不再是異化的超倫理視野的領域,而是通過天人一體與人的倫理價值內在相關的東西。生態文明不是對人類發展的完全否定,而是在順應自然規律基礎上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這就在天人共同構成的有機系統中把理性與價值的尺度內在地統一起來,從而為人與自然關系的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價值視野在生態領域的確立,使人們不再囿于理性視野所給出的可能性,而是給予是否“應當”的價值限制。生態文明為人類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理性與價值的有機整合,提供了一種操作上的可能模式,它表征著人與自然關系的進步狀態。人類需要重新學習在地球上生活的藝術,這是生態倫理的主題。人類應該把握生態時間,從理論和實踐上抵制經濟社會超速、超前發展的邏輯,對可持續發展的主體形象進行內容上的充實,從生態意義上理解人類生命的價值。
生態文明是社會實踐的產物,人的實踐活動的廣度、深度及其結果同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與完善是一致的。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和完善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證。當實踐主體的本質力量與實踐客體的物質力量達到有機、協調的統一,實踐活動就能取得積極的、肯定的結果。反之,則可能產生主客體間的沖突。沖突超過一定范圍,就會導致自然系統失去平衡。因此,要消除生態危機及其災難,最根本的就是促進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和完善。以人為本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出發點,也是建設生態文明的歸宿。只有全面提高人的素質,人們才能樹立與生態相適應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形成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健康生態人格,促進生態文明的真正實現。當自然獲得了真正徹底的完整性與獨立性,人也就具有了本質的豐富性與完整性,也就是人與自然達到了“同時性顯現”的狀態。“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6]
(三) 健全制度保證
建設生態文明,除了非正規的道德約束之外,還需要正規的制度保證。首先,建立國際性合作組織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必要前提。其次,制定國際性法規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制度保證。當然,國際社會有待進一步制定明確的獎懲制度,實現外部收益內部化,消除環保外部性問題中的搭便車行為。另外,科學的人文約束也需訴諸制度設計,如對科學技術及其社會歷史后果的價值評估、對人工環境和人工產品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延遲效應和潛在效應的評價,都需建立專門機構履行人工約束職能。應該將生態文明內在地體現在法律制度、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之中,并以此作為衡量人類文明程度的標尺。需要強調的是,私有制依然是生態危機的重要社會根源,因此,撥正社會發展價值取向,僅僅批判科技異化,“發泄高尚的義憤”(恩格斯語)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進行制度批判,從根本上否定私有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超越社會發展價值向度的偏離和社會發展創造的物質財富的奴役,才能增強社會發展的主體性效應,遏制住主體效應和非主體效應的嚴重沖突,從而歸正社會發展的價值向度。
總之,現代農業給生態文明建設帶來的正、負效應將導致歷史合理性與道德合理性的沖突,這一沖突只有在現代農業的高度發展中才能得以最終消解,而不是以遏制現代農業的發展或以放棄發展的持續性為代價。當然,預測是一種冒險,沒有人保證它一定會實現。邏輯不能完全保證預測,因為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中;經驗也不能完全保證預測,因為經驗再多也只是過去,不能保證未來。然而,理性決定了人類不會停止預測,因為有根據的預測或多或少會為未來的實踐活動提供一些指導意見。
參考文獻:
[1]E·拉茲洛.用系統的觀點看世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2]徐崇溫.全球問題和“人類困境” [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3]保羅·霍肯.商業生態學——可持續發展的宣言[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4]池田大作,奧銳里毆·貝恰.二十一世紀的警鐘[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 楊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