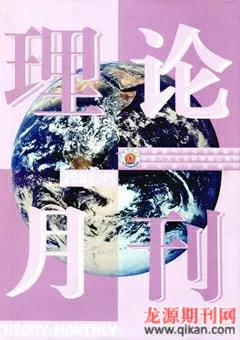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觀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
摘要: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平等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反映的是一定社會形態下的經濟關系,而不僅僅是法學或道德范疇;平等受一定的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制約,其實現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平等和公平,是與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相適應的,在實現的程度上還不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整形態的社會主義公平的發展水平。
關鍵詞:平等觀; 公平; 馬克思; 恩格斯;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8)11-0012-04
公平與平等的話題與人類社會一樣久遠,但不少人對公平和平等的認識還不深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平等是具體的、歷史的,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反映一定經濟結構的價值觀念,它們的實現程度不可能超越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可能實現”。[1]然而,有些人卻不顧歷史發展水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希求沒有差別的平等和平均主義的公平,這只能流于意志的幻想或理論的空談。
一、 平等是一個歷史的范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具有特定的內涵
平等的要求,是對經濟的棍棒、政治的皮鞭和精神的枷鎖的回應。它在奴隸制下表現為道德的訴求,在封建制下表現為宗教的呻吟,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理性的要求,所以,平等觀伴隨著私有制和階級出現而歷時已久。于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就認為,平等是人的自然法權所要求的普遍正義,是亙古不變的永恒真理。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批判道:“平等觀念什么都是,就不是永恒的真理”,[2]它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內涵。
1. 平等是一個歷史范疇。在原始的共同體里,“在個人權利方面平等,不論酋長或軍事首領都不能要求任何優越權……自由、平等、博愛,雖然從來沒有表述為公式,但卻是氏族的根本原則。”[2]在奴隸社會,“最多只談得上公社成員之間的平等權利,婦女、奴隸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人們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視得多。如果認為希臘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公民和被保護民、羅馬的公民和羅馬的臣民,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2]封建制度是容忍專制、神權和世襲的平等觀。“他們(佃農)過去不管在經濟上怎樣厲害地依附于地主,但在法律上是同他們的地主平等的,現在他們在法律上也成了地主的臣屬了。經濟上的屈從取得了政治上的認可。”[4]資本主義社會通行的是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間進行的公平等價交換,“這種平等和自由證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5]“這樣一來,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協調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據。”[6]而“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和資源日益增多的情況下,……誰如果堅持要人絲毫不差地給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產品,別人就會給他兩份以資嘲笑。……那末,平等和正義,除了在歷史回憶的廢物庫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兒還有呢?……可見,平等的觀念本身是一種歷史的產物”。[7]
同時,平等不等于無差別。正如恩格斯指出,“在國和國、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總會有生活條件方面的某種不平等存在,這種不平等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8]而且,“抽象的平等理論,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較長的時期里,也都是荒謬的。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無產者或理論家想到要承認自己同布須曼人或火地島人之間,哪怕同農民或半封建農業短工之間的抽象平等”。[7]所以,平等任何時候都是包含差別的平等。
2. 社會主義平等仍然殘留資產階級法權。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它在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由于實行按勞分配,消費資料的分配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所以,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但是,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而且個人負擔不同,在同勞同酬的情況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此另一個人富些。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但是這些弊病,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6]完全的平等才能真正實現。
3.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具有過渡性。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脫胎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尚且保留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和資產階級的法權;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這里的平等必然是既保留了資產階級的法權(不僅是等價交換的法權,還有一定程度的剝削),又殘留著前資本主義因素的平等,即封建的專制、特權、神權的殘留。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階級差別,因而是政治、經濟地位無差別的平等;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剝削作為一個階級已不存在,但社會階層和階級卻是廣泛存在的,所以,這里的平等必然是容忍階級和階層差別的平等。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城鄉差距,因而平等是沒有腦、體勞動重大差別的平等;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城鄉差距巨大,而且地區差距也異常明顯,所以,這里的平等必然是容忍城鄉、地區差別的平等。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消滅分工的社會,因而是在人逐步實現全面發展基礎上的平等;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職業區分普遍存在,而且一個人終生從事唯一職業也是普遍的現象,所以,這里的平等只能是容忍職業差別的平等。正像在奴隸社會把奴役、封建社會把專制、資本主義社會把雇傭勞動被看成平等一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同樣把這些差別看作平等。總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平等,從發展層次上說,只能是處于向完全的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因而具有過渡性。
二、 平等的實現程度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要求不能超越歷史發展階段
平等觀屬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部分。唯物史觀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又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決定了上層建筑的性質和水平,從而也決定了平等的層次和實現進程。
1. “人們……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取得自由的”[9]馬克思、恩格斯把生產力的發展作為他們的整個理論體系的立足點和邏輯展開的基礎,指出,“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這種發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9]物資匱乏、爭奪生活必需品,是不平等的經濟根源,而生產力的不發達帶來的階級壓迫是不平等的政治根源。然而,“即使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2]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是實現平等的必要條件。
2.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0]時代只能根據歷史進程提出符合時代發展水平的平等要求。私有制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但“私有財產是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在私有財產成為新出現的生產力的桎梏以前是不會消滅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所必不可少的條件”。[9]所以,“只要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競爭成為多余的東西,還這樣或那樣地不斷產生競爭,那末,盡管被統治階級有消滅競爭、消滅國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們所想的畢竟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此外,當生產關系還沒有發展到能夠實現這個意志以前,這個‘意志’的產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像之中。”[9]在這種情況下,“‘正義’、‘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這種或那種要求,但是,如果某種事情無法實現,那它實際上就不會發生,因此無論如何它只能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11]這種要實現的“事情”,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和公有制的建立。所以,就像不消除某一物體就無法消除它的影子一樣,僅從思想上消除不平等而不是求助生產力發展的做法必然流于荒謬。
3.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起點,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平的邏輯起點。盡管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應該看到,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力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這就是基本國情,也是我國的社會主義仍然處于初級階段的現實依據。我國現實生產力的狀況是:第一,總體水平低。表現為,在世界生產力水平已進入信息化時代的今天,我國還沒有實現普遍的機械化,農村更是基本上停留在手工勞動階段。手工生產力為主、機器生產力為輔、電子生產力剛剛起步,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總特征。第二,結構不合理。表現為,少量知識性勞動和大量體力性勞動并存;少量現代工業和大量的落后工業并存;少量農業機械化和大量人力、畜力并存;小量第三產業和大量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并存。第三,發展不平衡。表現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生產力差距巨大。從生產力中的決定因素——人——來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人口的63.91%生活在農村,全民具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3.61%,傳統意義上的文盲還有6.72%。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十五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表明,我國上網用戶總數為9400萬,不到人口的7%。這意味著,近93%人口不能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而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文盲”。要提高這樣龐大群體的科技文化水平和生產實踐能力已不是易事,而要全面提高其文化修養,樹立現代觀念、現代意識,則更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因此,從生產力發展水平上講,我國的社會主義不僅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甚至也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相當的差距。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其二是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我們只能在這種生產力發展水平上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平等和公平問題。
三、 平等是反映一定經濟結構的利益關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平必須與現有的所有制結構相適應
人們往往看到,社會不公平總是存在于政治領域,表現為權利的不平等。稍微深刻些的思想家,能夠從政治的太空來到經濟的人間。但至多也只停留在分配領域,提出所謂“公平分配”的要求。他們不知道,平等反映的是現實的經濟關系;分配永遠不能超出現有的經濟結構。
1. 所有制關系決定了人們的經濟地位,也規定了平等的性質。恩格斯用兩個實例,生動而深刻地分析了經濟關系對平等的決定作用:“只要是談到道德,杜林就能夠認為他們是平等的,但是一涉及到經濟學,那就不是這樣了。例如這兩個男人,一個是美國人,一個是柏林大學生,前者熟悉各種行業,后者除了一張中學畢業文憑和現實哲學,再加上根本沒有在擊劍館受過鍛煉的雙臂,別無所有,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可能談到平等呢?這個美國人生產一切,那個大學生只是這里幫幫,那里幫幫,而分配是依照每個人的貢獻來進行的;不久,這個美國人就具有對殖民地日益增長的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進行資本主義剝削的手段”,[7]一切不平等因此產生。下面一份契約更能說明問題:“眾所周知,我無衣無食,所以求您(主人)開恩,我希望受您的庇護并投靠于您,條件如下:您按照我為您服務的情況和應得的報酬負責供我衣食;而我只要還活著,就要按照一個自由人的樣子,聽候您的使喚,并且,我終生都不脫離您的權力和保護,一輩子留在您的權力和保護之下。”[4]在這種“自愿”的奴役下,談什么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呢?所以,馬克思說,“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12]這種經濟力量所決定的不平等、奴役,在當時的奴役者看來完全合理,在被奴役者看來也并不是不公平。
2.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10]以杜林為代表的一些所謂社會主義者由于不懂唯物史觀,不是根據現實經濟制度,而是求助正義、平等的觀念要求所謂“公平的所得”。對此,馬克思批判指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關系產生出法權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種極為不同的觀念嗎?”[10]所以,“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10]同樣,“對平等工資的要求(也)是基于一種錯誤,是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妄想。……在雇傭勞動制基礎上要求平等的報酬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什么東西你們認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這與問題毫無關系。問題在于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下什么東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13]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什么樣的經濟結構,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試圖在不改變生產方式的情況下改變分配方式,無異于企圖從染缸里拉出白布,絲毫也不能把平等推向前進。
3. 多種所有制并存,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有差別的平等。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生產力的多層性、不平衡性,必然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結構。一般說來,公有制以信息化、自動化的機器大工業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條件,個體所有制則能充分調動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小生產的積極性。目前的情況是,公有制是主體并掌握國家經濟命脈,但在存在方式和實現形式上卻是多樣化的。既有國有制、集體所有制,也有社會所有的股份制。而且,公有制在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階段、城鄉之間從規模到比重上都有所不同。同公有制并存的是大量的非公有制經濟形式。應當明確,私人經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則屬于社會主義經濟。因為它們不僅通過參資、入股、租賃、兼并等形式與國有、集體等經濟體實行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聯合,而且它們的實現程度、范圍和發展也受到國家法律的制約、行政的調控和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桿的調節。因而這些經濟成分依附于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體制內而非體制外的異己力量。這些經濟成分,是與現階段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且在促進就業、調動經營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商品流通和經濟繁榮、增加社會財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與這種混合所有制的經濟結構相聯系,必然是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多樣的分配必然帶來收入差距。這是如影隨形的事實,也是有因必果的邏輯。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平等只能是有差別的平等,這就是初級階段的公平。
總之,盡管平等觀表現為道德的良心、法律的理性或政治的仁善,但它始終是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經濟關系的反映。所以,平等的要求總是具體的,而平等的實現則完全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就我國而言,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和性質決定了必須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種所有制形式也就決定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而這種分配制度必然帶來收入差距。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平等只能是容忍差距的公平。這個公平,是邁向更高層次的平等的過渡和基礎。
參考文獻:
[1]恩格斯.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恩格斯.反杜林論[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恩格斯.法蘭克時代[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I)[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恩格斯.卡爾·馬克思[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7]恩格斯.反杜林論資料[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8]恩格斯.給奧·貝貝爾的信[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1]恩格斯.民族的泛拉斯夫主義[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2]馬克思.臨時協會章程[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3]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責任編輯劉鳳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