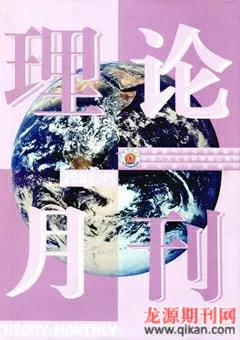《資本論》中的勞資關系思想研究
摘要: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資本論》實質上就是一種勞資關系理論,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勞資關系理論,是研究《資本論》中剩余價值理論的核心。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勞資關系,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下勞資關系的本質。人格化的資本和被異化的勞動,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的基本內容。勞資關系的本質不是平等,而是雇傭;不是自由,而是專制。
關鍵詞:勞資關系; 資本論; 雇傭勞動; 剩余價值
中圖分類號:A8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8)11-0016-04
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無論是從馬克思早期的經濟學著作還是從晚期的代表作來看,其核心部分都是在論述勞資關系,這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恩格斯在評論《資本論》時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1]《資本論》實質上就是一種勞資關系理論,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勞資關系理論,是研究《資本論》中剩余價值理論的核心。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勞資關系,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下勞資關系的本質。抽掉經濟關系的這個特定規定性,就不能看清被形式的平等所掩蓋著的實質的不平等關系。人格化的資本和被異化的勞動,是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的基本內容。勞資關系的本質不是平等,而是雇傭;不是自由,而是專制。
一、 剩余價值生產中的勞資關系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是剩余價值學說。《資本論》的中心問題是講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無論資本主義生產和經濟生活有什么變化,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剩余價值生產這一點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勞動過程,即使用價值的形成過程;另一方面是價值增值過程,即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就是商品的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的統一,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勞動過程的勞資關系和價值增值過程中的勞資關系具有不同的性質,應該分別研究它們的倫理關系。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過程對資本家和對工人有不同的意義。對工人來說,勞動是為了得到工資,以維持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對資本家來說,則是消耗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以獲得剩余價值的過程。在馬克思所考察的那個資本主義時代,這樣的勞動過程有如下兩個特點:第一,工人在資本家(或代理人)的監督下以規定的強度進行勞動,其勞動由資本家指揮和控制。第二,工人勞動的產品不屬于工人,而屬于資本家所有。生產資料成為榨取工人勞動的手段,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役使工人。
從資本家的觀點來看,勞動過程就是他購買勞動力后使用這個特殊商品,把其他的生產資料加進去,以勞動力為活酵母,經過必要的生產過程,得到他預計得到的產品。在這里,資本家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所關心的只是兩件事:一是生產出使用價值,即能夠出賣的商品;二是生產出商品的價值要大于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勞動力價值和生產資料價值的總和。就是說,不僅要生產出使用價值、交換價值,而且要生產出剩余價值。工人勞動之所以有價值,對資本家來說就在于它能夠滿足他的這些需要,最終滿足他的生產剩余價值和資本增值的需要。由此可見,勞資之間的倫理關系在這里包含著深刻的利益對立。一者是為了剩余價值,一者是為了生存;一者把自己當目的,一者把自己當手段;一者是主人,有占有勞動的權利,一者是雇傭者,把自己的勞動力交給資本家役使。
如前所說,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創造的價值是不同的。后者比前者包含一個增值,兩者是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不是出于道德動機同情勞動力的生活貧苦,而是為了得到勞動力的勞動增值的盡可能大的差額。生產出有用的產品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它只是價值的載體,其根本目的還是生產出盡可能大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勞動力這個特殊商品的特殊使用價值,正在于它是價值增值的源泉。這正是資本家看中勞動力并從市場上花錢購買勞動力的根本原因。
勞動力一旦出賣,他的使用價值就不再歸勞動力自己所有,而是歸資本家所有,全部勞動力都歸資本家使用。資本家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取得了勞動力一天勞動創造的價值。資本家用種種方法加大價值的增值,因此這個價值必然大于勞動力價值的一倍到幾倍。馬克思說,“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2]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資本”[3]這里既揭示了資本的特征,也揭示了資本家的本質。這里要注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并不是資本,它們只有在同時還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資本是能增值、能流動的一種特殊的物,但它要實現自己的增值,就必須有一定的人對它關心,承擔它的運轉,實現它的增值。就是說,必須使人成為資本的化身和代表。這就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人格化。資本不人格化,就沒有靈魂,就不能在運動中實現其增值的目的。作為資本化身的人就是資本家。資本家的目的就是資本增值,資本家的意志就是使資本增值。這是決定勞資關系性質的主體條件。作為資本家,在資本運動過程中的行為動機,就是為了實現交換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增值。他所以要關心使用價值的質量、數量,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價值的增值。因此,資本家不僅要以資本所有者的身份出現,而且要以資本的有意識、有意志的執行者和運作者的身份出現,行使資本的職能,創造剩余價值。為此,他必然在生產過程中,從直接的生產者身上榨取剩余勞動。這就是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存在的歷史價值,其本身就是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內容,也是形成勞資關系的實體性內容。
資本家被資本的力量驅使著,狂熱地追求價值的增值,因此具有“絕對的致富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托·約·鄧寧在《工聯和罷工》一文中的一段話。說:“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4]資本家以資本的名義對生產進行指揮,以資本的力量對社會進行統治,不僅具有致富欲,而且具有強烈的統治欲。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們是工業的領導人,而是因為他們是資本家。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是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只是工人的要求和斗爭迫使他不得不去關心,是資本增值和競爭的需要促使他不得不去關心。資本家個人所作的“應該如何”的選擇,正是基于這個必然性和必要性所作的選擇。在這里,馬克思指出了一個客觀的法則:“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5]所以,馬克思說,“這也并不取決于個別資本家的善意或惡意”。[6]當然,這里又有它客觀上的積極方面,即這種力量也促使資本家努力去發展生產,擴大和發揮資本的作用。馬克思說,“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正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奴隸制、農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7]
二、 勞動力價值和勞動日的道德界限
雇傭勞動的特點是工人的勞動力成了商品。工人逐日將自己的勞動力賣給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換得工資,以求生存;資本家購得勞動力,使之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生產出超過投入價值的價值,即剩余價值,以謀取利潤。勞動力成為商品,需有兩個條件:一,工人不像奴隸或農奴人身依附于奴隸主或農奴主那樣,只能在自家主人的驅使和強迫下勞動,而是已經獲得了人身自由,有權自由地出賣勞動力給任何一個資本家;二,工人也不像個體農業和手工業勞動者那樣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可借以謀生,而是除勞動力外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過活。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上,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勞動力的時間決定的,或說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這些生活資料雖然在形式上可能有變化,但是在一定社會的一定時代,它們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它是一個不變的量。變化的只是這個量的價值。另外,還有兩個因素決定勞動力的價值:一個是勞動力的發展費用,這種費用是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另一個是勞動力的自然差別,即老少、強弱的差別。就是說,勞動力的價值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時間可化為勞動力生存的生活資料生產所必需的時間。勞動力的價值就是這種生活資料的價值。這就是說,維持正常生活條件下的勞動力包括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一定的自然條件;另一方面是必需的生活資料范圍和滿足需要的方式,這取決于國家的文化水平、歷史條件、生活習慣等。因此,勞動力的價值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包含著歷史的、道德的因素。因為勞動力是人。人的價值與勞動力的價值是不同的。人的價值是一個社會范疇,勞動力的價值是一個經濟范疇。人可以是一個勞動力,從事某種勞動,但他同時還是其他多種社會關系的代表,還具有其他方面的價值。作為人,他是目的,具有目的價值;作為勞動力,他是手段,具有手段的價值。在合理的社會關系中,人的價值高于勞動力的價值,在不合理的社會關系中,人的價值低于勞動力的價值。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個工人必須首先是工人,然后才是人。就是說,他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掙得飯吃,才能成為人。從另一方面看,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存在著某種倫理關系和道德調節問題。必須把人當人看待,不能只當作商品拿來交換,只當作手段用以使役。
在資本主義市場上,確定勞動力買賣過程的形式是契約。勞動力買賣雙方簽定契約時,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還沒有轉到買者手中,勞動力的價值是作為使用價值讓渡給買主以后、投入勞動過程中才實現的。這就是說,勞動力的讓渡和實現在時間上是分開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在契約訂立前確定的,工人在拿到工資前就已經消費了勞動力,而資本家買到勞動力之后使用一段時間才付工資。因此,這就構成了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一種信貸關系。從工人方面說,工人要依靠自己的積蓄干活,要等一、二個月,或一、二周才領到工資,因此要信任資方到時發工資。資本家一方則按照契約規定使用勞動力,在生產進行一段時間后要守信用,按契約規定付給工人工資。契約就是實現這種勞動關系的保證。工人貸出了自己的勤勞,資本家從這里得到利益。如有以下情況,這種勞資關系就會受到破壞:一是資本家破產;二是資本家變相克扣或減少工資。當然,如果工人反對原定契約,采取否定合同的行動,也會破壞這種勞資關系。不過,要從實質上了解勞動力買賣的性質,不能只在市場交換中就作出判斷,還必須到生產過程中去看個究竟。
首先,就是要看工人的工作日的勞動時間。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資本家以廠主或代理商的面目站在作坊老板的背后,曾為資本主義生產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和夜間勞動奠定了基礎。因而,這個勞動時間在歷史上就存在著一個道德界限問題。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工作日本身是不定的,是流動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內變動。它的最高界限的確定取決于:(1)身體界限,也稱自然界限,即人的生命力定量。人在一個24小時的自然日內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必須有一部分時間用于其他需要。這是純粹身體的界限。(2)道德界限,也稱社會界限。這是工人滿足精神文化和社會需要的時間。這種需要的范圍和數量,是由一般的社會文化狀況決定的。就是說,工人的工作日是在身體界限和道德界限之內變動的,工人生命的極限也就是道德的極限。
其次,要看控制道德界限的權力在誰手里。上面所說的兩個界限都有很大的伸縮性,伸縮的權力不在工人手里,而是在資本家手里。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執行資本增值的職能。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允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工人勞動的時間就是資本家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的時間。因此,工人的無酬勞動就是他們進行競爭的基礎。如果工人利用這個時間做自己的事,就被看作怠工、偷竊,就要受到廠方的懲罰或法律制裁。就是說,在界限內,勞資關系可以作非強制性的道德調節;在界限之外,道德調節便轉化為強制性的法律調節。一般來說,微觀的調節,取決于工廠主對待工人的態度和具體經營情況;宏觀的調節,則取決于工人階級的力量和勞資雙方斗爭的情況。
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是工人階級經過幾個世紀爭取和斗爭的結果。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滿懷激情傳達的工人的呼聲:“我賣給你的商品和別的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創造價值,而且創造的價值比它本身的價值大。……你經常向我宣講‘節儉’和‘節制’的福音。好!我愿意像個理智的、節儉的主人一樣,愛惜我唯一的財產———勞動力,不讓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費。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發展所容許的限度內使用它,使它運動,變為勞動。可是你無限制地延長工作日,就能在一天的時間內使用掉我三天還恢復不過來的勞動力。你在勞動上這樣賺得的,正是我在勞動實體上損失的。使用我的勞動力和劫掠我的勞動力完全是兩回事。……因此,我要求正常長度的工作日,我這樣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為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情面可講的。”[8]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種斗爭在那個時代曾是全體資本家和全體工人之間的斗爭,即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如果說這個斗爭的權力是平等的,那么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
三、 所謂“公平的工資”
19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的50年間,英國工人運動中流行一個口號:“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也是當時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觀點。這個口號對鼓舞工人為公平而斗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什么是“公平的工作”?什么是“公平的工資”?所謂一天的工作,就是消耗工人一天的勞動力,同時又不以損害工人第二天的勞動為限度。所謂“工資”,就是保證工人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貨幣,即保證工人的工作能力和他延續后代所需要的錢。從這兩方面來看,工人和資本家在這種關系中是一種合法的交易。這種交易就是:工人把一天的全部勞動力交給資本家,得到的是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但工人付出的多,得到的很少。盡管如此,工人為了生存還是要到資本家門下去做工。而且,一者認為這是“天經地義”,一者以為“干一天活拿一天的錢”也公平。可是,實際上卻是不公平的,工人并沒有得到他干一天活所應得的工資。首先,競爭不是在公平的起跑線上進行的。資本家有工廠和資本,工人一無所有。資本家不愁沒有人給他干活,而工人沒有工作就要挨餓。因此,工人即使在事先拿不到應得的工資的情況下,也只好勒緊褲帶去給資本家干活。其次,由于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進行競爭。為了生存,工人和工人之間也相互競爭,其結果給資本家造成了壓低工資的機會,使工人的工資常常得不到保障。工人之間的競爭更增加了資本家的力量,削弱了工人自己的力量,從而有利于資本家和資產階級。
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的轉化形式。一般來說,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初期,工資有兩種基本的形式,即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計時工資是直接表現勞動力的日價值、周價值的轉化形式。計件工資不過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兩種形式都包含著資本家玩弄的花樣,即以低于勞動力的價值支付工資。在計時工資里,資本家通過延長勞動時間來降低工資,往往不顧工作日的道德界限,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正常的限度而不給工人任何相應的報酬。在一個產業部門里,工作日越長,工人的工資就越低。計件工資是資本家克扣工人工資和進行社會欺詐的最有利的源泉,是最適合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因為勞動的質量和強度是由工資形式本身控制的,因此對勞動的監督就變成寄生的中間盤剝的包工制。這種包工制就構成層層剝削、壓迫制度的基礎。那些中間人的厚利完全來自于資本家支付的勞動價格和中間人實際付給工人的那部分勞動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就是那時普遍存在的“血汗制度”。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工人階級為提高工資進行的斗爭連續不斷,這正說明工資最敏感地反映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決定的利益分配關系的不公正。當然,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資本的需求也會超過勞動的供給,這時工人的工資就會提高。這種情況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工人的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使工人對人格化的資本的從屬關系,在永久化的基礎上變得比較安適和寬松,從而使勞資之間的緊張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和改善。馬克思認為,如果道學家面對資本主義分配說“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分配”,那么這句話與政治經濟學沒有直接的關系。這不過是說,這些經濟事實與道學家的道德感有矛盾。它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是不是”的問題,是經濟規律的問題。
四、 雇傭勞動關系的本質
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的增殖也具有決定的意義。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資本是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增值的,但它要以流通領域為媒介。可以說資本增值既在流通中進行,又不在流通中進行。事實上,取得剩余價值這種交換對買者是幸運的、有價值的,而且是“公平”的,但對勞動力的賣者來說則相反。因為,資本家用各種方法加大增殖,取得剩余價值,這就使貨幣轉化為資本,使一般的服務變為剝削。但這個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沒有違反商品交換的規律,它以流通領域為媒介,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增殖。
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過程就是價值增值過程。在這里,產業資本起著決定性作用。產業資本使資本的職能不僅是占有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而且同時是創造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因此產業資本決定了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也決定了勞資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在這種關系中,資本家實施生產過程的監督,目的是要生產出剩余價值。生產剩余價值,賺錢,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是資本家作為資本家行為的絕對動機。按照黑格爾所說,“行為的動機就是我們叫做道德的東西”。[9]那么,對資本家個人來說,他作為資本家行為的動機,就是他的行為的道德動因,也就是他的道德。作為資本運行主體的資本家,他的這種動機就在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上,確定了它的道德性質。資本家作為資本家的行為動機,與貨幣關系、買賣關系連在一起的就是利己主義、功利主義。因此,產業資本的存在不僅鑄成了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階級對立,而且也包含著勞資之間關系異化的經濟根源。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已是一個總體,而不再是單個人的服務。在資本家的工廠中,勞動作為一個結合的總體,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彼此之間不是交換服務,而是互不相干。作為總體,它不是單個工人個人的事情,而是“不同工人的共同事情”。這個“共同事情”,是說工人們被“外力”即資本的力量擠合在一起,而不是他們自己互相結合的,不是工人作為勞動主體的自為的結合。工人的勞動就其結合體來說,是服務于資本家的意志和智力的。工人的勞動被資本家的意志和智力所支配,其“精神的統一”處于他們自身之外。勞動者的勞動作為個人的勞動被否定了,這種被否定的個人勞動就構成了被肯定的“結合勞動”。它首先作為“結合勞動”表現為資本家的財產,同時也使資本成為起支配作用的主體和主宰,使勞動者成為被支配的客體和工具。因此在這種經濟倫理關系中,是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和奴役。這才是勞資關系的本質。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固定資本像是“有靈性的怪物”,把科學思想客觀化了,成為一個聯合體同工人發生關系,而不是作為工具同工人發生關系;相反,工人卻作為有靈性的單個的、活的、孤立的附屬品從屬于它。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結合勞動”,是自在的結合。因為這種結合既不表現為共同勞動的個人相互發生關系,也不表現為這些個人支配其特有的職能或支配勞動工具。因此工人把自己的勞動產品看作他人的產品,同樣也把這種結合勞動看作他人的勞動,把自己的勞動看作是異己的,被強制的“生命活動力”。正像勞動產品一樣,勞動者的勞動,作為孤立的勞動者的勞動被否定了,而資本作為社會勞動的存在,既是作為主體又是作為客體的結合。資本表現為起支配作用的主體和他人勞動的所有者,因而也成為勞資關系的主導力量。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關系的異化。首先,資本發展成為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本身的控制和指揮權力。人格化的資本監督勞動者以限定的強度進行勞動。生產資料成為榨取勞動者的手段,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通過資本家的意志使用工人,使工人作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而失去其作為人的價值。機器生產的出現使勞動異化的形態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工人的意志被資本家和資本家手里的機器所壓制,不能正常的發揮出來,因而使勞資關系不僅失去平等,而且失去自由,使一方只享有權利而不盡義務,另一方只盡義務而沒有權利。其次,資本家依靠他的權力,迫使工人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范圍而從事更多的難以忍受的勞動。工人在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創造的產物的支配,勞動是異己的、被強制的生命力活動,成為勞動者的沉重的、痛苦的負擔。不僅如此,在工廠生產中,資本家通過私人立法和監工,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奴隸監督者的鞭子。工廠主是絕對的立法者,監工是執法者,工人由于自愿訂立了契約而必須遵守資本家的立法,服從監督。在這里,對工人來說,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自由不見了。而對資本家和監工來說,罰款和克扣工資的處罰使犯法比守法對他們更有利。正是這種剝削關系體現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勞資關系的本質。它不像奴隸主占有奴隸那種勞動關系,也不像農民依附領主(地主)那種勞動關系,而是保持一種契約形式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雇傭剝削的勞動關系。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5][7][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3、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9]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責任編輯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