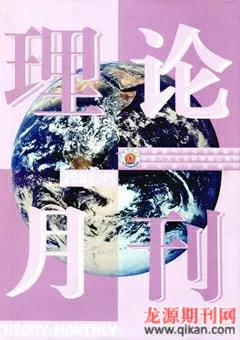龔育之在中共歷史研究中的治學特點淺析
摘要:在中共歷史學領域中,著名學者龔育之獨樹一幟,從諸多方面為黨史研究做出了獨特貢獻。龔育之的突出貢獻是與其思想境界、學術風格密切相連的。系統總結他的治學特點,如:立足現實、關注時政的研究態度,思想解放、與時俱進的理論境界,文風簡約、論證有力的學術風格,畢生敬業,筆耕不輟的工作精神,有助于其他學術同仁全面了解龔育之的卓越貢獻,更有利于年輕學子從中獲取為學教益。
關鍵詞:龔育之; 黨史研究; 治學特點
中圖分類號:D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8)11-0057-03
知名學者龔育之在黨史學領域獨樹一幟,建樹甚豐。他從很多方面為中共歷史研究做出了獨特貢獻,如:致力文獻編輯,開創文獻研究新局面;編寫黨史要著,貫穿全新別致思路;關注學科發展,闡述黨史研究原則方法;分析自身見聞,存留諸多重要史料;著文立說,提出大量新穎見解,等等。深入思考,仔細體會后,就不難明白龔育之的醒目貢獻是與其思想境界、學術風格密切相連的。
在長期的黨史研究中,龔育之形成了自己鮮明的治學特點。系統總結他的學術風范和理論風格,有助于其他學術同仁全面了解龔育之的卓越貢獻,更有利于年輕學子從中獲取為學教益。本文力圖從如下四方面對龔育之的治學特征進行粗淺的探析。
一、 研究態度:立足現實,關注時政
龔育之絕對不是那種固守在學齋里、局限于書堆中的學究,他向來倡導理論學習、歷史研究、現狀研究三者的結合。他曾在文中寫道:“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在新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進行的,而對新的實際,我們要用極大的努力去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發展新理論”。[1]他不僅號召同輩學人努力面對新實際,而且自己也一直踐行著這一理念,深深扎根于今天的時代和社會,從變化著的形勢和情況出發,用理論研究的成果為現實服務。他的不少宏論都是應客觀需要而發,而且針對性強,很少有空泛的、主觀的議論。即便是回顧歷史的文章,也很少有沉悶感,總力求站在全新的高度去追溯歷史,直面、還原、鳥瞰歷史后,分析總結出其中的經驗教訓,令讀者從中獲益良多。
潛心學術研究的龔育之,同時積極加盟政治宣傳,注重發揮黨史研究的特有功效。通讀龔育之的作品就會知道,他的文章幾乎都與黨的重要會議、歷史性事件相關。如:歷史決議通過和改革開放以后,他撰寫了《遵守黨的決議和保障科學研究的自由》、《經濟改革和思想解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新概括》等重要論文;南方談話和十四大以后,他又有《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讀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國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南方談話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黨史研究》、《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由來和意義》等力作涌現;鄧小平逝世和十五大以后,他趕出了《業績·思想·風范》、《十五大精神和黨史研究》、《從十五大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鄧小平理論:新中國五十年歷史的科學總結》、《從鄧小平南方談話到江澤民“七一”講話——紀念南方談話十周年》等不朽篇目;十六大以后,他及時發表了《十三年:奮斗歷程和基本經驗》、《再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獨特的超越——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黨的最高領導層的新老交替》等引人深思的文章。細心的讀者會在龔育之著作中發現這樣一段話:“1991年秋天,理論界許多同志分外深切地感受到認真學習、研究、和宣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多么的重要,在國際變局和國內風波中,我們之所以能夠站穩腳跟,不就是因為十多年來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偉大成果嗎?堅持沿著這個理論指引的方向繼續前進,中國社會主義就有前途,中華民族振興就有希望,停止甚至倒退,是決沒有出路的。而這樣的學習、研究和宣傳,還做得很不夠。從自己做起吧。于是,我重讀了……”[2]雖然他在此介紹的是《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的成文背景,然而從中可管窺到他關注時政的寫作習慣。他不但關注時政,而且,無論局勢怎么變幻,無論詆誹多么荒誕,他仍然高度自覺地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
“文章合為時而作”的龔育之矢志不移地將政論與史論密切結合,頗有“兩胡”遺風。數十年來,對黨的決策、方針、政策做了不少系統論證、深度闡發與科學評價,其研究成果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實踐目的,真真切切地起到了黨史研究鑒往知今、資政育人的作用。也正因為他有著求真務實而又政治立場堅定的科學態度,眾人眼中的龔育之:是儒雅的官員,更是杰出的學者;有著理論家的敏銳,也不乏歷史學家的深邃。
二、 理論境界:思想解放,與時俱進
龔育之思想向來開明,其“心不與年俱老”。他從來都不曾停止前進的步伐,幾近古稀之年仍能輕松地將寫作方式由“提筆”改為“敲鍵”,讓人心生欽佩。在賀其好友于光遠九十大壽時,他送上了“不背初衷,與時俱進”八個字,并解釋說: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管經歷了多少復雜和曲折,都不背離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同時,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是一個盲目信奉的馬克思主義者、抱殘守缺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歷史的實踐中不斷反思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開拓未來中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者。[3]其實,龔育之贈給于光遠的這一贊譽,何嘗不是他自己人生追求的真實寫照?也何嘗不是他本人精神境界的簡單概括?
深諳解放思想重要性的龔育之,多次強調學術環境寬松之必要。在論及胡喬木的訪美學術報告時,龔育之特意較為詳盡地介紹了胡另一關于寬容的談話。在胡喬木看來:科學事業是在困難與寂寞中成長起來的,領導者不應讓自己長期形成的習慣和利害影響自己對科學問題的判斷。引述者龔育之對此看法的認同或共鳴是不言而喻的。確實,寬容常駐的科學環境,才能為解放思想提供沃土。在《思想更解放一點,理論更活躍一點》的發言中,龔育之又提議認真總結理論界工作歷史的經驗教訓,以便我們在主觀指導上為理論的健康發展,更多地排除一些障礙,更好地創造一些條件,從而使理論界在今后的新階段中更有效地服務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他深惡痛絕“動不動就拿大帽子嚇唬人”的做法,認為它“勢必窒息理論工作的生機和活力”、“阻礙和遲滯真理發展”。他自己將十四年(1978-1992)理論界工作的歷史經驗總結為:“最根本的有兩條:一條要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如果一切本本上有的東西、固定框框中有的東西就一概不能動,沒有的就一概不能說,如果是這樣一種思想路線,就根本不會有理論的活躍和前進。再有一條是要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實事求是的對立面是本本主義,百家爭鳴的對立面是帽子主義。”[4]這些鏗鏘的話語,今天讀來,還極富啟迪性。
龔育之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勤于思考,善于得出新知新論,而不是墨守陳規,因循守舊。他在宏觀理論上的開拓創新,顯而易見,無需多說。對于許多看似細微的問題,他也一貫勇于表達個人見地。如意識到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廢除以后,領導集體分代的界線較為模糊,前后領導代之間難免重疊,他遂將自己文章中“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之提法分別修訂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的核心”。其修改理由是:第一代、第二代等稱法雖自鄧小平1989年提出以來,被黨中央的文件沿用至今,自己當然懂得也擁護這些提法的重要政治含義,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完全可以在自己文章中采用表述上略異之說法,而不是非得一字不改地套用正式文件中的提法。[5]即使是別人習以為常的一些問題,龔育之也總能窺見其中的“異常”。如贊同胡喬木批評名人死了不及時見報的陋習之余,他又毫不隱諱地指出另一流弊:新聞總愛堆砌一大串頭銜才講出死者姓名,這種播報法常讓聽眾半天都納悶究竟是誰死了。因此,在編寫《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時,深有感觸的龔育之首倡了一項改革:先寫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同志逝世,然后才介紹他生前擔任過的職務。這種直截了當的敘述方式無疑科學多了,龔育之不落俗套的風格也可見一斑。
思想解放、與時俱進并非龔育之在某一階段的做法,而是貫穿于他整個學術生涯的顯要特征。一時一事的思想解放并不難,難的是一如既往地保持創新魄力、一以貫之地堅守正確結論。龔育之就有這種可貴的學術風骨,他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束縛,堅持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來觀察、分析問題,即使暫時處于逆境,或偶爾陷身弱勢,依舊信念堅定,執著追求真理。如,《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和《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兩文的發表,在當時的理論界產生極大反響,卻也招來某些非議。龔育之并沒因此動搖、退縮,而是冷靜地科學分析:“除了因為我行路不當心踩了人家腳上的雞眼,只好十分抱歉以外,主要當然還是因為市場經濟問題。‘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的影響的確很深,換腦筋很不容易”。[6]也因為有著“任憑風浪起”,“我自巋然不動”的廣闊學術氣度,使龔育之能在重大問題上堅守自己的正確觀點,凸顯出可敬的理論風骨。
當然,主張思想解放、與時俱進,也并非倡導不合時宜地抱住一己之見不放。黨史研究要堅持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結合,政府應保障科學研究的自由,學者也要堅持歷史決議的正確決定。顧全大局、嚴守紀律是龔育之黨史研究中的又一特點,他明確贊成“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想的要比說的多,說的要比寫的多”。[7]他相信為革命而探索真理是不應該受到重重限制的,但學者也要為自己說出來特別是寫出來的東西負責,要顧及社會影響,對于關系重大而個人考慮還欠成熟的想法,就不能輕率地隨意散布。
三、 學術風格:文風簡約,論證有力
瀏覽過龔育之作品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他的特色寫法。相對于厚實的大部頭著作,龔育之似乎更喜愛用單篇獨文來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1999年,他更是在《學習時報》上開辟了黨史札記專欄,依托看似散漫的札記形式,著眼于現實中的一些問題,闡述富有創見的個人認知。雖然,黨史札記價值之不同凡響并沒有一開始就被所有讀者意識到,甚至習慣了陳言俗規的某些人還對他那看似“不規范”的寫法頗有微詞。但是,沒過多久,札記在義理、辭章、考據方面的組合優勢就顯山露水了,許多讀者對它引人入勝的敘述方式也大為贊賞。龔育之所采用的獨創性札記體裁,簡單而隨意,有質又有文,形式多樣,或長或短,時敘時議,甚至客問主答,主題清晰,重點突出。正是在數百篇札記中,龔育之輕而易舉地記下了自己的回憶或思考,創造出簡約樸實的文風。
龔育之的文章,論證非常有力。眾所周知,龔育之學貫兩科,文理交融,思維縝密,邏輯嚴謹,表述準確。他常常在條分縷析中游刃有余,敘述事情,有“庖丁解牛”般的嫻熟自如;論說道理,如“剝繭抽絲”式的有條不紊。為此,石仲泉在悼念龔育之的文章中毫不掩飾自己的羨慕之意:同一件事,同一個理,我們一般人往往只能作一些大的方面敘說,再往細處、深處講,就感力所難及。而在龔育之的筆下卻是另一番景象。講事,能將其來龍去脈、原委細節娓娓道來;論理,能旁征博引,如數家珍地論列文獻,或從多側面的視角,講出一般人難以講出的道理。從石仲泉的評價中,能夠進一步感覺出龔育之說理論事功力之爐火純青。龔文論證有力,與他的論說方式相關,也與其文獻、史料的豐裕有關。他的不少文章,文獻征引翔實,史料披露詳盡,令人嘆為觀止。得益于多年的文獻編輯工作,使他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地信手引用一些重要文獻;由于他本人特殊的歷史經歷,還能見人之所未見,知人之所未知,又有著隨手記錄的良好習慣,故對他來說,往事并非如煙霧般縹緲模糊,一陣翻箱倒篋,總能持之有據,準確抖出不少史實、史料,與大伙共享。史料,對于黨史研究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龔育之比一般人更懂得搶救史料的重要性。他曾建議就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胡繩說法”,自己也和時間賽跑,全力記載保存相關史料。可惜,還沒來得及口述完于光遠“素描”,他就乘鶴遠去了,給人留下些許遺憾和無盡感傷。
四、 工作精神:畢生敬業,筆耕不輟
龔育之堪稱黨史學界的奇才,早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學系,卻因時代和國家的需要,積極投身于黨的理論和歷史的宣傳、研究工作,理論水平卻較其它黨史學者絲毫不遜色。他用一生走出了一條革命理想和科學信念交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融合的非凡道路,將個人的追求與社會的需要緊密結合,以個人的發展促進時代的進步,最終在推動社會進步中實現了自我價值,在當今社會樹立了良好的道德典范。
龔育之畢生敬業愛崗,忘我奉獻。他年輕時就得了慢性腎炎,以后身體一直較弱,但卻把事業看得很重,像健康人一樣正常工作,甚至比常人更大負荷地忙碌。他一輩子沒忘使命,不背初衷,信奉“花堪折時直須折”,堅持“勤修案牘不修窩”。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龔育之也沒改變多年來爭分奪秒思考的習慣,不顧醫生的勸阻,繼續于治療間隙在病床上艱難寫作或竭力口述,卻常因體力不支而昏迷過去;身受病魔肆虐的劇痛,他仍舊不忘囑托夫人清理家里刊物時留好有關黨史和歷史的資料,照例讓家人替他標記好所讀報刊書籍的有用內容,以便日后引用;在離去前夕,他依然掛念著繼續寫作,叫女兒給他“重新配(眼鏡)”的交代竟成唯一遺言。難怪熟悉龔育之的韓鋼一度困惑:他是用生命來堅持寫作還是以工作在延續生命?像他這種以生命寫史,生命未息寫作就不止的奉獻精神,怎么會不感人至深、催人淚下呢?
綜觀龔育之的一生,他在科學海洋里鍥而不舍地探求至理,在黨史園地中嘔心瀝血地精心耕耘,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對于龔育之的學科出身和經歷優勢,其他黨史學人自然無法如愿復制,然而,他的治學之道與理論風范卻是完全可以被黨史新兵們大膽效仿的。許多學者眼中的龔育之,“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秉德無私參天地”,“道德文章啟后昆”,其獻身學術的高尚情操,燃燒自己照亮他人的紅燭精神,尤其值得青年人好好繼承,用心弘揚。
參考文獻:
[1]龔育之.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2]龔育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增訂新版)[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3]本書編輯組.懷念龔育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4]龔育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增訂新版)[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5]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6]龔育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增訂新版)[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7]本書編輯組.懷念龔育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楊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