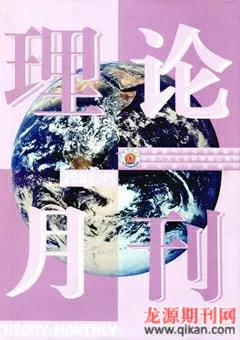從哈佛課程改革歷程觀大學責任的演進
摘要:哈佛大學的課程體系歷久彌新,在其370余年的發展進程中,時刻不忘把握時代脈搏,主動進行改革,培養為社會所需要的人。從哈佛課程改革中培養目標的調整觀大學責任的演進。
關鍵詞:哈佛; 課程改革; 培養目標; 大學責任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08)11-0153-03
一、 引言
哈佛大學(以下簡稱哈佛)的課程體系歷久彌新,經亨利·鄧斯特、查爾斯·艾略特、勞倫斯·洛厄爾、詹姆斯·科南特和德雷科·博克的不斷發展,日臻完善,成為20世紀世界大學的典范。然而21世紀的世界瞬息萬變,為了適應知識經濟社會的來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進程的深入、社會劇變和職業流動的日益加快,哈佛于2002年10月啟動了新一輪全面綜合的本科課程體系改革(以下簡稱課程改革),“核心課程”(即通識教育)改革是此次改革的中心任務。6年來,改革成績斐然,僅通識教育改革就出臺了4個報告:①關于課程審查進度的中期報告,②哈佛學院課程改革報告,③哈佛學院課程評審報告;④通識教育改革最終報告。2007年5月15日,根據最終報告起草的“通識教育課程新計劃”以168比14票通過了教師團立法(Faculty Legislation)。[1]至此,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全面付諸實施。
二、 哈佛課程體系中培養目標的調整
改革是哈佛課程發展的主題之一。回顧哈佛建校370余年的歷史, 課程體系主要經歷了以下6個階段。
哈佛大學歷次課程改革在培養目標上都有所調整,1637年的課程以培養有教養的人為目標;1869年的改革強調賦予學生充分的個性發展空間;1909年改革著力于構建合理的專業主修與分類選修課程結構體糸;1945年通識教育改革目標為培養自由社會中的公民;1981年的核心課程改革是提供學生探索知識的方式與途徑;2007年通識教育課程新計劃則提出要培養全球性公民。本文將圍繞以上線索,探討在哈佛課程改革培養目標的調整。
(一) 通過博雅教育,培養有教養的人
哈佛始建于英國殖民時期的1636年,與其同期成立的美國高等教育學府還有耶魯學院(即今耶魯大學)等其他9所常青藤盟校,它們承襲英國大學特別是牛津和劍橋大學的傳統,以修習古典文學和古典語言為核心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來培養有教養的人。
從1637年起, 哈佛校長亨利·鄧斯特(Henry Duster)就把歐洲教育發展的三種傾向,即中世紀的七藝(文法、邏輯、修辭、幾何、天文、算術、音樂)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對希臘和拉丁古典作品的興趣以及體現宗教改革思想的宗教教育運用于哈佛的“博雅教育”之中。這種以牛津和劍橋的傳統課程為框架、以培養紳士為目的、注重人文修養的早期課程,較為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人類知識體系,體現了博雅教育精神,因此一直保持了200余年。
與此同時,經歷了新大陸移民、獨立戰爭、南北戰爭等不同時期的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大學內部的固步自封,課程設置的一成不變,使得個性不同、志趣各異的學生不愿去迎合同一種課程模式、按照同一種步調學習,結果導致高等教育課程設置的價值受到社會的嚴重質疑,改革勢在必行。
(二) 實施自由選修制,賦予學生充分的個性發展空間
1869年,年僅35歲的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出任哈佛校長。他上任后一改學校過去對課程設置嚴格限制的做法,逐步將本科生所有的課程全部改為選修制。他曾開宗明義地宣布自己的施政綱領:“本校要堅持不懈地努力創立、改善并推行選修制。”他認為,每個學生天生的愛好和特殊的才能,都應當在教育中受到尊重; 只有充分發揮學生獨特才能的課程,才是最有價值的課程。學校提供自由選擇的機會,可以進一步培養和訓練他們的自我責任感學生步入社會以后會將這種責任感發展成對社會的責任感。這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2] “自由選修制”(Free Electives)的實施,滿足了學生對各種課程的要求,為其個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間。同時,改革也促進了學科分化,增加了新課程的數量和種類,加強了實用學科的建設,滿足了學生就業的需求。
“自由選修制”一直深受學生的歡迎,在艾略特任職的40年間,哈佛學生得到了極大的學習自由。然而,由于“自由選修制”對學生學習的課程選擇沒有任何限制,一些弊端也漸漸凸現:一是學生所選課程之間往往缺乏系統性和統一性,難以產生全體學生共同必修科目,無法形成共同文化。二是一些學生選課時常常根據授課時間是否方便和是否容易取得學分而選課,造成學習上的盲目性。三是為了適應學生的需求,有些教師開設的課程學術價值不高,影響了教學質量。四是少數學生的功利選課法造成集體主義觀念的削弱,并使之失去對共同目標和價值觀的追求。到了1890年,很多教師開始對“自由選修制”持批評態度。
(三) 采取集中與分配制,構建合理的專業主修與分類選修課程結構體糸
1909年,勞倫斯·洛厄爾 (Lawrence Lowell) 接替艾略特就任哈佛校長。他吸取“自由選修制”的經驗和教訓,把德國的完全自由選修制和英國的導師制結合起來,形成了獨具美國特色的“集中與分配”(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課程體系。“集中”是指從16門可供選擇的課程中,必須選修6門本系的專業課,以確保重點;“分配”是指另外的6門課要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3個不同的知識領域中各選2門,以保證學生具有比較廣泛的知識面;其余4門課程由學生自由選擇。[3]這種“主修”“分修”與“選修”相結合的制度,既保證了專業課學習的深度,又擴大了學生的視野,同時也可給學生的個人愛好留下適當的余地。輔之以優等生學生計劃( Honors Program )和獨立學習計劃 ( Independent Study ),使教育質量大為提高。然而,由于沒有獨立的師資和管理實體,學生“分配”部分的課程往往得不到足夠的指導,造成所選課程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學到的知識支離破碎。加之專業教師對于教授非專業的學生沒有足夠的經驗,授課的內容和方式不能恰當地適應這類學生的需求。到了1945年,哈佛的課程體系被形容成圣經中的諾亞方舟: 學生象諾亞挑選世界上各類動植物標本一樣挑選課程,每一個知識領域都涉足一點,但沒有完整的學習計劃和總體目標。這些弊端的逐步惡化促成了1945年《紅皮書》(The Red Book)的問世。
(四) 實踐通識教育,培養自由社會中的公民
詹姆斯·科南特 (JamesConant) 擔任哈佛校長后,任命哈佛教授和校外知名人士組成專門委員會,研究通識教育問題。歷經兩年研究,該委員會提交名為《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報告書,即美國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紅皮書》。《紅皮書》將“通識教育”定義為: “首先將學生教育成民主社會中負責任的人和公民的那一部分教育”。通識教育計劃(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要求每一位學生必修以下3門課程:“文學名篇”、“西方思想和組織機構”以及任意1門物理學或生物學方面的課程。除此之外,學生必須在人文學科、自然學科和社會學科這3個領域各選1門全年的課程,學校開設的絕大部分課程按年級高低和學科類別被編為4組。這種課程模式把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結合得很緊密,而且先后有序、互相銜接,形成了以通識教育為基礎、以集中與分配為指導的選修制度。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科南特所強調的由所有學生共享的知識核心已被類似洛厄爾時代的分配制所代替。象以前的改革一樣,由于通識教育仍舊沒有自己獨立的師資和管理實體,造成這部分課程的教學質量無法得到保證。
(五) 依據核心課程,提供探索知識的方法與途徑
1975年身為哈佛校長的德雷科·博克(Dereck Bok )吸取前幾次通識教育改革失敗的教訓,任命文理學院院長亨利· 羅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組成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研究本科生的課程設置情況。通過調研,該委員會一致認為:除專業課和選修課以外,應建立一套本科教育的“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這一套課程設置不應該以課程的內容和類別為依據,而應該以教授這些課程的目的為準繩,即培養學生的智能和思維方式。經過數年的努力,哈佛終于形成了獨具匠心的“核心課程”體系,并于1981年正式開始實施。“核心課程”要求學生從6個領域中挑選8門課進行學習。通過“核心課程”的學習,學生應該了解人類組織、運用和分析知識的方式和手段。
“核心課程”的最大突破在于通識教育設立了自己獨立的管理和師資實體。從社會組織學的角度看,在各種類型的組織中,最重要的是正式組織。因為“組織是可以提供抵抗環境擾亂的堅強堡壘”,[4]是工作正常進行的保證。核心課程的管理機構由1個常務委員會和7個下屬委員會組成,委員會中的每一個管理人員負責一個課程領域的管理和建設,從而保證了通識教育的實施質量。
(六) 遵循通識教育新計劃,培養全球性公民
隨著科技的發展、知識體系的更新,美國高等教育發生了許多新變化,同時對“核心課程”的基本原理也提出了挑戰。導致哈佛新世紀課程全面改革的最直接原因,首先是核心課程所倡導的“獲取知識的方法和思考的方式”標準模糊不清,有時甚至被忽略;有的核心課程太難,有的又太容易;[5]其次是美國有史以來迅猛而又廣泛的教師和學生規模的轉型,導致精英層面的教授和學生從白人和男性主導轉向越來越國際化和綜合化。為了與社會、知識、文化發展相協調,改革勢在必行。此次改革責成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具體負責,并根據各個時期的要求,組成人員不同的工作小組和若干專題委員會。科比在其致哈佛同僚的信中說:“我們必須開展自我批評,目的是為了改進。哈佛大學之所以成為一流大學,是通過連續不斷地回顧自我、反思自我和更新自我取得的。”[6]在當今全球化不斷深化、相互聯系日益緊密,同時又多元化的、支離破碎的世界里,負責任的教育應該提供當今世界需要的廣博知識。基于這一點,課程改革指導委員會指出,改革后的通識教育課程要求學生解讀文化產品,參與政治過程,應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衍生物,與擁有各種背景的人互動,評估公共話語中的科學主張,勇于面對個人或職業生活中的倫理兩難問題。[7]這些課程定位于廣博的材料領域(文本、思想、基本原則和發現),跨越學科體系和學術專業的界限,為進一步學習和探究提供廣博的概念框架。
此次改革的最大亮點是把“培養全球性公民”定為哈佛的培養目標,為學生生活在文化和文明不斷變化的全球性世界做準備。作為引領世界潮流的高等學府,哈佛不僅有責任把學生教育成本國公民,而且有責任把學生培養成世界公民,并為此專門開設了元旦短學期課程,以確保相當程度的國際體驗。
三、 從哈佛課程改革中培養目標的調整看大學的責任
哈佛歷次課程改革都根據社會的需求在培養目標上進行恰當的調整。1869年的選修課改革賦予學生自主選課的自由;1909年的集中與分配制改革強調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的平衡;1945年通識教育改革強調培養自由社會的公民;1981年的核心課程改革提供學生探索知識的方法與途徑;21世紀的課程改革目標是培養全球公民,提倡課程跨學科的綜合性和靈活性,強調教育國際化和科學技術教育的作用。從每次課程改革中,不難看出大學責任的演進。
(一) 把握時代脈搏,培養社會需要的人
大學的第一職能是培養人。哈佛在對時代特征和社會發展大趨勢進行了透徹分析和整體把握的基礎上,每次改革都適時地調整教育使命和培養目標,為社會培養所需要的人。從培養“有教養的人”(1636)以應新移民之需,到培養“自由社會中的公民”(1945)幫助樹立西方價值觀,再到培養“全球性公民”(2007)以順應國際化的浪潮,都對大學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進行了很好的詮釋和科學的論證。
(二) 主動進行改革,在發展中不斷創新
毋庸置疑,教育需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進行改革。然而,改革有主動和被動之分,主動的改革意味著對過去的某些東西進行部分或全部的否定,這需要極大的勇氣與堅定的信心。1869年自由選修制的實施、1909集中與分配制的探索、1945年通識教育計劃的實踐、1981年核心課程的誕生和發展,以及2002年新一輪改革的啟動都展現了哈佛主動進行改革,在發展中不斷創新,從而引領21世紀大學新潮流的氣魄。
(三) 堅持傳統與創新的結合
新世紀哈佛課程改革有4大目標:一是培養全球性的公民;二是發展學生適應變化的能力;三是使學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四是讓學生意識到他們既是文化傳統的產品,又是創造這一傳統的參與者。這4大目標以“通識教育課程新計劃”的方式體現出來,并被分為8個類別:①審美和詮釋、②文化和信仰、③實證與數學推理、④倫理推理、⑤生命系統科學、⑥物理宇宙科學、⑦世界諸社會、⑧世界中的美國。另外,所有本科生還必修1門說明性寫作課和1門外語課。從上述4大課程目標和8個新的課程領域中不難發現:哈佛堅持把通識教育的優秀傳統與培養具有科學素質和國際化視野之人才等新的理念相結合,以不斷創新引導社會前進。
無論是古希臘柏拉圖的學院、亞里士多德的經院,還是12世紀意大利和法國的大學,抑或英國紐曼理想中的大學,雖說大學的基本形態和理念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是,大學培養人的基本任務和責任卻從未動搖過。哈佛作為20世紀大學的典范,在其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和逐步完善的課程體系在培養目標上的調整,對大學責任的演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艾略特時期的“自由選修制”、洛厄爾時期的“集中與分配制”、科南特時期的《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博克時期的“核心課程”到2007年的“通識教育課程新計劃”大都圍繞這么一個主題展開:大學的責任是什么?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在哈佛看來,無論大學的職責如何演進,在21世紀如何把學生培養成一個良好的全球性公民以便他們有能力在全球過著奉獻性的生活,這就是大學對學生的首要責任。
參考文獻:
[1]Harvard Faculty Approve New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B/OL](2007-05-15).http://www. fas.harvard.edu/home/news-and-events/releases/gened- 05152007. html.2007-06-07.
[2]陳向明.美國哈佛大學本科課程體系的四次改革浪潮[J].比較教育研究,1997,(3).
[3]趙長林,董泉增.哈佛大學的課程改革及其啟示[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0,(1).
[4]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5]Dean Kirby . Letter to Community from Kirby April 26, 2004. [EB/OL]http://www.fas.harvard.edu/curriculum-review/essays-pdf/ Deans-Cover-Letter.pdf.2007-06-07.
[6]William C. Kirby . Dean William C. Kirby’s Letter to Colleagues October 7, 2002. [EB/OL]http://www.fas.harvard. edu/curriculum-review/backgroud.html.2007-06-07.
[7]張家勇.密切博雅教育與現實生活的關系——哈佛大學普通教育課程改革最終報告評介[J].中國高教研究,2007,(7).
責任編輯王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