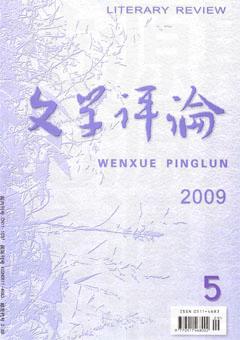深化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之我見
靳明全
國統區抗戰文學也被學界稱為大后方抗戰文學。因本文涉及的文本多是國統區抗戰文學的稱謂,故維持原名。以空間時間及內容來界定,國統區抗戰文學乃中國現代文學特殊階段的主流文學。無可否認,國統區抗戰文學的研究不乏成就,但深入地思考,其研究之缺欠也毋庸質疑。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們的報紙、電視上隆重介紹表彰了一大批抗日英烈,其中包括了許多我們的史書上很少提及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表達了一種全民族韻敬意。在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更是在講話中指出:“在波瀾壯闊的全民族抗戰中,全體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奮勇作戰。”我們的黨秉承與時俱進的原則,在對相關歷史的評說上,表現了對事實的尊重和非凡的理論勇氣。與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的講話,以及主流媒體的旗幟鮮明的態度相比,我們的抗戰文學研究者卻顯得畏首畏尾,在傳統觀念的束縛下邁不開步子。
研究欠缺之一是對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抗戰作用的淡化評價。丘東平小說《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寫了國民黨軍隊的一個連長林青史,率領連隊三次主動出擊日軍,挽救了戰場危局,但終被其上司按貌似公正的軍紀處以死刑。《友軍的營長》寫國民黨軍隊一個營突破日軍猛烈槍火而生還,結果營長因此而違反了專橫暴戾的軍紀選擇了上司對他的重刑。吳奚如的小說《蕭連長》,寫了國民黨軍隊蕭連長的上司在戰斗中與蕭失去聯系,便猜疑他臨陣脫逃。而事實上,蕭連長卻以少數兵力出奇制勝地奪回了陣地。當蕭連長返回旅部時,卻因上司猜疑被處死。此外,蕭乾的《劉粹剛之死》、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蕪的《兩個傷兵》、羅烽的《橫渡》、丘東平的《中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作品的研究者都高度評價了國民黨軍隊下層官兵的抗日愛國精神,同時,又指出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在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戰政策下,國民黨下層軍人抗日的艱難性。對于國民黨軍隊作戰內容的作品,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者均不厭其煩地選擇上述作品為研究對象,教條式地重復上述的研究結論,并引導讀者走上了一個誤區:抗戰中。國民黨軍隊下層官兵總體是正面的,他們的上司,即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多是負面的。實際上,作戰勝敗誠然以軍事力量優劣為物質基礎,但軍隊戰斗力的充分發揮,則直接取決于各級軍官。整體戰斗力的發揮,取決于高級將領。戰爭全局更是操于最高統帥部之手。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主要作戰。由于中日軍事力量的物質基礎存在很大差距。正面戰場的作戰,國民黨軍隊敗多勝少。對之描繪的國統區抗戰文學,主要宣染了作戰之悲壯及勝利的曙光。這是鼓舞抗戰斗志的需要。但是,對這些作品的評價,雖然強調了鼓舞抗戰之重要性,可卻引導出悲壯作戰及勝利主要取決于下層官兵,國民黨將領特別是高級將領乃至最高統帥是無能的或不作為的結論。且不說對國民黨軍隊作戰的全盤否定的評價,即使對下層官兵充分肯定而淡化上層將領的積極作用,也是對國民黨軍隊作戰的整體性否定評價。這種研究結論是不符合戰爭規律及作戰實際的。在抗日的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取得了許多悲壯式的勝利,有的文學作品對之進行了形象描繪。但這類作品的研究者們。均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人格力量及軍人操守的崇高評價,他們的抗戰功績也未得到充分肯定,這不能不說是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的一個欠缺。
欠缺之二是戰時首都重慶形象及重要地位扭曲化。長期以來,宋之的的《霧重慶》被視為國統區抗戰文學描寫重慶形象的代表作。對之反復的研究,所下的結論幾乎千篇一律:陪都重慶不過是國民黨達官顯貴的花花世界和腐蝕青年心靈消磨抗戰意志的罪惡魔窟,因為,流亡到重慶的青年們,或窮途潦倒,或卜卦算命,或當交際花,或開飯館,或患病死亡等都與“戰時首都重慶”有牽連。有研究者還特意點出重慶“濃霧”既是對重慶自然環境之特點,更是吻合抗戰時期生存在重慶的人生命運之象征。象征著戰時首都重慶被沉寂、閉悶、醉夢、利誘、險惡等似濃霧一樣地圍裹著。置身其中,必須步步管醒,以防大街小巷無形的眾多陷阱。在濃霧中掙扎,更要提防強人打劫。打劫的強人者,自然要聯系上重慶的統治者——國民黨政府官員。巴金《寒夜》也是國統區抗戰文學中以重慶為主要背景之代表作。對其研究結論多是陪都重慶儼然深夜地凍霧濃的“寒夜”:黑暗、陰冷、心寒、膽顫。重慶多霧,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冬天寒夜也冷。為什么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者們喋喋不體地對戰時首都重慶如此地大力渲染昵?這不過是文學批評的一種政治性引導。戰時重慶是黑暗統治,其形象當然是黑暗的,這種政治引導式的文學研究及批評,往往是重慶與延安的形象評價相映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重慶的天是陰沉黑暗的天。延安無愧于光明的象征,重慶則為“濃霧”之借代。研究者懷著這種引導性的審美價值去尋覓國統區抗戰文學文本,可以說俯首即拾。但倘若與這種引導性的審美相反,去尋覓描繪抗戰時期重慶光明形象的文本,不能否定,那又是汗牛充棟了。問題是作為與美國華盛頓、英國倫敦、蘇聯莫斯科并列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名城,她是中國抗戰文化抗戰精神的載體。一味地將重慶形象用政治引導方式特指為陰冷黑暗。如何理解她所載承的值得中華民族發揚光大的抗戰文化抗戰精神呢?
欠缺之三是反復強調揭示社會黑暗,而忽略中國國民性之弱點。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揭示中國國民性弱點,魯迅是首屈一指,但“七七事變”前夕,他不幸病逝。“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展開了全民的抗日戰爭。抗戰文學承擔起了鼓勵中華兒女積極投入抗戰的偉大使命。國統區抗戰文學成為了中國特殊階段的主流文學。動員民眾,積極抗戰是國統區抗戰文學主要特征。針對國統區政局復雜,黨派斗爭紛紜,戰事變幻的狀況,揭露社會黑暗一度成為了國統區抗戰文學的趨勢。然而,揭露社會黑暗之際,國統區抗戰文學也亮出了揭示國民性弱點的零星“閃爍點”。作為文學研究與批評,除了分析作品內容形式,啟發讀者的審美情趣外,更要開掘文學作品殊為珍貴的“閃爍點”,以啟迪讀者思考社會現實。就此而言,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欠缺明顯。沙訂小說《在其香居茶館里》一直被評價為國統區抗戰文學之重鎮,對其研究評論均反復強調,作品揭露了國民黨兵役制度的弊端,揭露了國民黨整治地方吏治的虛偽,揭露了國民政府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的絕境。不可否認,這種研究結論有其合理性。抗戰時期,國民黨兵役制度弊端重重,有目共睹。“拉壯丁”及“逃兵風”成為抗
戰時期中國軍隊戰斗力較弱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一景,《在其香居茶館里》及抗戰時期流傳的劇目《拉壯丁》不過是此景的一個縮影,難免眾多研究者不斷地如此地闡釋。然而,在抗戰背景之下,動員能作為壯丁的中國人上前線,為什么這么艱難呢?壯丁為啥要硬“拉”呢?民族存亡之際,中國人普遍存在躲避上戰場表現出來的麻木不正是魯迅所揭示的國民性弱點嗎?還有更嚴重的,抗戰時期,中國人充當偽軍較反法西斯戰爭的其它國家尤為突出。文學作品的描寫,無非是痛罵之,鄙視之,作品研究亦如此。可研究者忽視了偽軍生成如此多如此快的更深層原因。剖析清除中國國民性弱點,國家民族方能存活強大,深刻反思抗戰為何如此艱苦卓絕,發揚抗戰精神才顯得更加重要可貴。國統區抗戰文學的研究,比如對茅盾的《腐蝕》、《清明前后》、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陽翰笙的《天國春秋》、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沙汀的《淘金記》等作品,結論都是揭露了國民黨統治的社會黑暗,而忽視了對社會黑暗背景下凸現出的國民性弱點之剖析,即使對之剖析也僅為零星的閃點。這不能不說是研究之欠缺。
欠缺之四是有些“禁地”沒有深入地研究。例如,土匪抗戰、地主抗戰、資本家抗戰的研究就很膚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軍大舉南侵,中國大片土地淪陷。戰爭混亂狀況之下,各地武裝土匪蜂起。土匪武裝除投降日軍被編為偽軍及占據僻地橫行鄉里者外,有很大部分是不堪忍受日軍蹂躪而由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他們以各種形式打擊日軍,與國民黨、共產黨武裝保持若即若離關系。
抗戰前,地主具有大量的土地,資本家都有一定的產業。抗戰爆發,淪陷區地主的土地和資本家的產業都被日軍掠奪。這些地主、資本家對日軍有著切骨之恨。他們本能地要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受日寇侵犯。從這個角度來認同抗日主張,投身抗日活動的地主資本家是很多的。無論是抗日根據地實行的減租減息,或是國統區實行的加大增稅政策,都是戰爭的必然要求。這些地區的地主、資本家絕大部分是認同抗日主張投身抗日活動的。
國統區抗戰文學反映上述社會現象的比較少(當前,反映這方面的文學創作有了一些突破),而對之研究長期以來被視為“禁地”。研究者往往強調:土匪形象與偽軍形象掛勾,地主形象與漢奸組織聯系,反動政權中穿梭著昔日資本家的身影。這三類人物多是賣國者、妥協派、投降派或是消極抗戰的縮影。
缺欠之五是意識形態主流高高地壓過了審美情趣。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對戰國策派陳銓作品的研究了。抗戰時期,陳銓寫了劇本《野玫瑰》、《金指環》、《藍蝴蝶》、。《黃鶴樓》、《衣櫥》等,出版了長篇小說《狂飆》,其中《野玫瑰》當時獲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的學術獎。
長期以來,對陳銓上述作品都是從意識形態主流出發給予了內容之否定并附帶以審美價值的否定。《野玫瑰》寫了國民黨間諜夏艷華為國家民族利益,拋棄個人情感與大漢奸斗爭的故事;《金指環》刻劃了土匪偽軍劉志明與國軍將領旅長太太尚玉琴曲線救國的情節;《狂飆》寫了立群、慧英、國剛、翠心四個青年之間的糾葛,宣傳了日寇侵略下必須提倡民族主義。陳銓的其它作品大同小異,以抗日為背景,大力宣揚民族主義民族意識。如果聯系到陳銓上述作品闖世之際,國民黨當局提倡的以民族主義為主的戰時文藝政策,同時聯系在抗戰相持階段國共統一戰線出現較大的裂痕及軍事摩擦等現實,站在新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陳銓作品體現的國民黨政治意識方面的某些否定,是有必要的,但若站在全民抗戰的高度,對陳銓作品之否定則無不斷地加碼之必要了。于文學研究者來說,對作品進行審美情趣和審美價值的評價也是重要之一環。許多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者對陳銓作品審美情趣和審美價值評價很低,冠之以“圖解國民黨方針”、“圖解民族意識”、“概念化、公式化傾向嚴重”、“缺乏藝術感染力”等等,這種研究結論是植根于意識形態主流高壓下的審美情趣的拋棄。如果拋棄這種“高壓”進行審美情趣、審美價值的判斷,給陳銓上述作品冠之以“情節曲折”、“形象生動”、“重視戲劇結構”、“語言剔透簡潔”等等,并非虛偽的溢美之詞。以陳銓上述作品研究為例,推而廣之,長年以來的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難道不是熱衷于意識形態的闡釋,疏忽于審美藝術開掘,有意無意地使意識形態主流高高地壓過審美情趣了嗎?
究其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上述五個欠缺之原因及對策,筆者認為:
首先,研究對象,即抗戰文學作品本身存在缺欠。抗戰爆發,日本侵略軍十分猖獗,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際,抗戰作家們無論在前線或后方,無論是戰地生活親歷者,或無戰地生活實感者,都紛紛拿起筆投入抗戰。變動急劇的戰爭供給了抗戰作家異常豐富的材料,他們沒有時間來提煉,往往急就章地對抗戰生活進行形象描繪。早期的國統區抗戰作品大多是戰爭生活現實的斷片連綴及現實生活的浮光掠影。戰爭發展到中期相持階段,在呼吁創造偉大作品聲中,國統區抗戰文學出現了經過復雜藝術思考后的一些精品。戰爭后期,國統區抗戰文學大多克服了昔日選材狹小、形象單一、重生活表層、輕本質開掘等弊病,出現了刻畫戰爭的一批杰作。然而,這些杰作與世界名著描寫戰爭的相比,特別是在戰爭背景下深入挖掘文學本質即人性的東西,還存在很大的差距。面對國統區抗戰文學這種狀況,研究者有“源”“流”不足之感。戰爭期間,國統區社會問題成堆,文學文獻整理研究,難以正常開展。戰爭結束后很長時間,這方面工作未得重視,一度處于癱瘓。所以,現在研究者要尋到早已失散于民間的抗戰文學珍品,希望十分渺茫。然而,即使渺茫也要探尋,更要擴大已有的研究對象范圍。國統區抗戰文學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時不我待,勢在必行。
其次,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要克服意識形態主流支配下的格式化、狹窄化現象。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展開了中國現代史上的解放戰爭。1949年底,國民黨軍隊被趕出大陸,盤踞臺灣。人民解放軍在大陸取得徹底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在這種政治格局下,長期以來,大陸與臺灣處于敵視和臨戰狀況,表現國民黨軍隊內容的國統區抗戰文學的研究長期就在大陸與臺灣、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不同意識形態主流支配之下形成一種格式:大陸的國統區抗戰文學作品(或作史料叢編,或寫人中國現代文學史)要符合大陸的意識形態主流,以這些作品為對象研究的結論也要符合大陸的意識形態主流,這也是歷史發展之必然性。同樣地。長期以來,臺灣關于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也受其意識形態主流的支配。由于主流意識形態支配,我們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形成了狹窄化現象。國民黨抗戰高級將領的丑化,戰時首都重慶形象扭曲化,中國國民性弱點揭示的淡化,土匪、地主、資本家抗戰作用的弱化,審美情趣評價被拋棄或始終處于附屬的“第二”位置。意識形態主流隨著政治格局的變化而變化的。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兩岸關系,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現在有了很大改觀。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兩黨關系隨之有了很大變化。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和平統一發展已成為中國人之共識。所以,曾達成共識的一致對外的中國抗日戰爭的這段歷史,目前就成為了連接兩岸和平統一的一個“中介”,這樣,反思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欠缺就有了不同意識形態下去尋找共識的大前提,昔日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的格式化、狹窄化完全能夠沖破,這不能不說是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之幸事!
克服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之欠缺,還應加大區域文化區域文學研究力度。國統區抗戰文學既含時間內容,也含空間地域。雖然,戰爭進展給雙方占據的空間地域帶來較大的變化,但有一個總體的相對的穩定性,國統區正如此。抗戰文化抗戰文學中心是重慶,以重慶輻射桂林、昆明,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及周邊縣村。作為抗戰文化抗戰文學中心的重慶,其區域特色給國統區抗戰文學帶來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形式。帶著重慶區域性理念去研究國統區抗戰文學當然要圍繞抗戰下功夫,同時,更要結合重慶的地方特色,重慶的風土人情。重慶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進行研究。這樣,其研究成果才具獨特性、區域互補性、作品審視的多側面視角。試想,研究成果具有了這些要素,上述國統區抗戰文學諸多欠缺不是多少能得到克服嗎?同樣地,國統區抗戰文學研究,如果帶著重慶之外的(桂林、昆明,成都、西安等)區域性理念進行研究,本文所探討的國統區抗戰文學欠缺之克服,難道是一種奢望嗎?
責任編輯: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