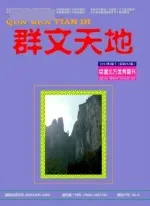淺談延安文學特質
郭 燕
延安時期,毛澤東積極創構并最終成形的新的意識形態話語對延安文學的形成、發展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延安文學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政治性影響,更在1949年后憑借其所屬意識形態話語權威的延續而楔入到了共和國文學的血脈中去。
一
在延安文藝的發展歷程中,文藝整風后的延安文學在其政治意識形態性上已經成了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毛澤東話語”的再生產場域,它的確立不僅依附這一話語,而且緊密依附于黨的權力意志。從創作主體來說,個人化的寫作方式在延安文學的創制中已經成為一個無法被照亮的黑暗領地,個人之小我隱匿并消融于集體之大我中,個性隱匿并消融于黨性之中。個人只能憑借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指引去參與集體化的寫作事業。
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政治與文學的糾纏總是剪不斷理還亂的,誠如楊義先生所言:“現代文學史是與現代政治因緣很深的學科”。延安文學正是把現代中國政治與文學之因緣引向一個獨異境地的文學。其獨異性在于,當它發展到文藝整風之后,它已經在一個較為封閉的地緣文化和政治文化場域中,依憑政治強力和新的意識形態話語,把“左聯”時期較為抽象、空泛并寄寓了各種知識分子自由想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實實在在推進到了與黨的權力意志緊密結合的政黨政治。吳立昌先生認為,“五四”后三十年到建國后三十年,中國文學在政治的強力干預下,自由度越來越小,最后幾乎等于零,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也因之日漸呈現為一個死結,怎樣才能解開這個結,關鍵不在文學,而在政治。“如果政治家還要迷戀‘武器的批判可以代替‘批判的武器,那么文學必將可悲地走入死胡同”。其間所言“政治”乃正是自延安文學發展至文藝整風后所曾遭遇過的政黨政治。所以,討論延安文學的意識形態化形成盡管難免要討論具有普泛意味的政治與文學的關系,但重要的是要把“政治”推進到政黨政治的核心層面來予以討論,因為只有這樣的“政治”才切切實實構成了后期延安文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和影響力,并使延安文學在整風之后呈現了與此前左翼文學迥然不同的文學形態。
二
胡喬木曾在檢討“黨的文學”這一概念時指出,“社會主義事業,它是人民的事業,不能因為它要有黨的領導,就把它說成是屬于黨的。文學藝術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黨需要對這種社會文化現象的發展方向進行正確的領導,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許多事情,不是在黨的直接指揮下,經過黨的組織就能夠完成的,而是要通過國家和社會的有關組織、黨和黨外群眾的合作才能進行的。而且,有許多與文學藝術發展方向關系不大的事情,黨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干預。因此,不能把文學藝術這種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納入黨所獨占的范圍,把它說成是黨的附屬物,是黨的齒輪和螺絲釘。”又諍諍告誡道,“黨的文學這種說法的含義是不清楚的。把文學這種社會生活現象完全納入黨的范圍是不合適的”。胡喬木是站在“黨的文學”從延安時期的形成、發展再到轉換為“國家的文學”后所帶來的沉痛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說出這番話的。逆向觀之,即可理解后期延安文學或整風后的延安文學及共和國成立后30年文學的真正面貌及其歷史走向之必然了。
三
延安文學研究,繞不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所體現的是當時一個革命家、政治家從他所領導的政治革命的利益的角度對他所領導下的文學藝術家提出的要求,而不是當時的文學家、藝術家從自身文學創作的角度對社會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提出的基本要求。這兩個角度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但是,文學藝術并不僅僅是服務于政治家和革命家的,而更多的是面對讀者,面對整個人類、整個人類社會、人類歷史的,是直接作用于廣大讀者的內在精神需求的。越是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越不僅僅停留在政治實踐的現實需要上,而是更關注人的內在精神需求。在這里,就有一個當下的政治實踐和長遠的精神發展的差異和矛盾的問題。“文革”前,將《講話》提高到文學藝術圭臬的高度,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文學藝術的這種獨立性、文學家與藝術家的內在精神追求,而離開了這一切,文學藝術作品就只能跟在政治實踐后面對政治實踐做程序性的過程描摹,也就失去了文學家、藝術家獨立創造的更廣大的空間。革命家、政治家要有所承擔,文學家、藝術家也要有所承擔。正是這種承擔意識,才能賦予文學藝術以思想的厚度和藝術的厚度。我們對《講話》也需要進行重新的感受和認識。
參考文獻:
[1]楊義.關于現代文學史編撰的幾點隨想[J].中國文學研究,2000(3).
[2]吳立昌.重評基點和論爭焦點——現代文學論爭兩”點”論[J].復旦學報,2003(6).
[3]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康濯.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