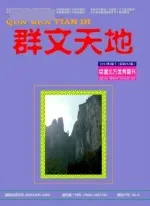英雄群像下的山城風景再現
長期以來,因為小說景物的描寫相對分散、缺乏整體性,造成對小說《紅巖》的故事發生地重慶的區域性特征研究,一直處于被遮蔽或缺失的狀態。
其實,小說《紅巖》除了集中描寫了革命者的地下工作和集中營的獄中斗爭,塑造了一個集體英雄群像(江姐、許云峰、劉思揚、成崗等)外,還執著地追求革命功利性與藝術完美性的辯證統一。“重慶的歌樂山,江岸邊的華鎣山,奉節縣城,都讓我記住了。我在心里說,有機會,我一定要去那些地方看看。”可以說,由這部小說既使讀者達到認識歷史、受到教育的目的,也激起了讀者了解重慶的強烈愿望。
重慶是中國抗日戰爭主要政治舞臺。山城厚重而特殊的歷史文化積淀,鑄造了城市的靈魂,其地理風貌,革命遺跡,文化景觀,市井沉浮,給人造成了強烈心理感受和視覺沖擊。小說從重慶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兩方面的描寫中滿足了讀者的閱讀需求。首先在自然景觀描寫方面。
1、霧。重慶地處長江、嘉陵江匯合處, 日照少、多陰天 ,秋冬多霧,是有名的霧都。霧,成為重慶的一個象征,一個不可或缺的意象。在小說開篇,作者就迫不及待地交代道:“抗戰勝利紀功碑,隱沒在灰蒙蒙的霧海里,長江、嘉陵江匯合處的山城,被濃云迷霧籠罩著。”一句話就把讀者帶入濃郁的山城景象中,在霧中,有人堅守革命意志,也有人經不起誘惑,迷失在霧中,甫志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霧,在書中增添了一種時代政治氣氛,透過霧,人們辨別偽奸,讓叛徒的面貌更丑陋,讓革命者的形象更高大。
2、歌樂山。作為故事的集中展開地,因為白公館、渣滓洞監獄坐落其中,歌樂山在小說中出現最多。一是從劉思揚的視角來寫的,如:枯樹叢中干澀的蟬鳴、黑夜里流淌的泉水,繪聲繪色的描寫,有著使人仿佛身臨其境的生活氣息,增強了對人物形象的立體刻畫。小說也從其他一些革命者如余新江、黃以聲、華子良等人的視角,三言兩語地勾畫歌樂山,鼓舞斗志。
3、嘉陵江。盡管《紅巖》以殘酷的獄中斗爭為人們熟知,但小說中少有的對嘉陵江的亮色描寫,彰顯著別樣的光輝。如成瑤眼中夕陽斜照下和晨曦霧散后的嘉陵江、李敬原坐著一葉扁舟渡過春水發了的嘉陵江等,極具浪漫色彩。文中有多處如此明朗的描寫,并不與《紅巖》主題相悖,反而恰到好處的豐富了小說的內容,填補了殘酷有余,優美不足的欠缺。
其次表現在人文景觀方面。在小說中,大篇幅地穿插描寫了的重慶市井風情,突出了山城的歷史風韻,拓寬了社會面的廣闊性。
1、革命活動地。作品中出現的一些地名,融合在人們的生活中,無不是山城歷史的真實寫照,紅巖村、周公館、南方局等中國革命的遺址、遺物、老一輩革命家曾戰斗過的地方,無疑是特殊的人文景觀。
2、方言。作為地域文化的承傳載體,方言與人們的文化心態、風俗習慣以及自然生態、地理環境等密切相關。小說在語言上雖然通篇都是白話,但是為了契合人物的身份,在某些場景和人物對話中運用了方言,如雙槍老太婆在大石橋意欲搶救江姐的傳奇經過,運用了很多方言俚語,人物的各色形象活靈活現。
3、陪都風情。在小說中最突出的就是陪都生活風情的再現,折射著城市的歷史,突出了城市的地標。“幾聲拖長的汽車喇叭,驚動了滿街行人,也驚散了一群搶奪煙蒂的流浪兒童。這時,紀功碑頂上的廣播喇叭里,一個女人的顫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熱鬧嘈雜的節日重慶,畸形繁華的商埠景象,在余新江一路行走中盡情展示。對山城夜景的描述也照樣有點睛之筆,幾句話就簡略地勾勒出山城的雨后的夜景。寫作者們還以優美的筆調寫到徐鵬飛的客廳的布置,營造出舒暢祥和的氣氛。在寫作過程中,作者們曾查閱了大量資料,走訪了許多人,系統補充了國統區的知識,因此個人記憶、家庭記憶、集體記憶借助于地域感受、時代風貌得以傳遞與重溫,從而塑造出曾作為陪都的重慶是一座富于歷史情感而又包容的城市。
此外還有對磁器口正街上鑫記雜貨鋪開張的描寫,有著別樣的古鎮風情。對重慶當時的交通工具方面也有所涉及:如長江輪渡、小劃子、滑竿,透露出重慶這個山水之城的地理特點。
“就一部文學作品與一個城市的關系而言,以及不同媒介產生的廣泛社會影響、對城市形象的塑造而言,很少有能與《紅巖》相媲美的作品。”小說所生動再現的重慶地域特色,恰恰是構成紅巖整體藝術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山城風景的多方面的展示。
參考文獻:
[1]葉辛.讀《紅巖》的日子[J].中文自修,1997,(1):4.
[2]羅廣斌 楊益言.紅巖[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
[3] 鄧偉.川渝文化合作論壇開放的川渝——地域意義生發下“川渝文化合作”的一個維度.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7,(6):21—25.
(作者簡介:張學福(1983.8—)男,漢族,河南信陽人,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