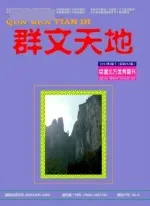封建法統下妻的地位
郭 敏
在封建統治時期,“平等”、“自由”、“權利”、“公平”、“人權”都與女性無關,可以說,封建時期的女性時刻都活在社會、禮教和法律的歧視與束縛中。“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是封建禮教對女性的規定,同時也窮盡了女性凄慘的一生。
封建社會提倡累世而居,由封建家長(或族長)治理整個家族,封建家長(或族長)一般由本族年長者擔任。女性未成婚時住在自己家族中,她們在家族里的地位很低,沒有獨立的財產,對于族的事務甚至自己的婚姻都沒有發言權與決定權。封建社會的歷代法典都對女性結婚的最高年齡做了限制,超過此年齡未婚的,一般會強制結婚,或者是處罰家長,漢初惠帝年間,詔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①,即女子三十未嫁,就會多收五倍的口賦以示懲罰。所以,“妻”是封建時期女性不可避免的一個身份。
(一)夫妻法律地位的不平等
封建時期的禮教與法律恰像兩個契合的半圓,它們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完美無痕的圓圈,將女性包圍在里面,絲毫不得僭越。禮教宣揚“三從四德”,宣揚“夫乃婦之天”②,法律也從立法上肯定夫妻法律地位的不平等,通過刑法的威脅和對違背的懲罰,迫使妻子不得不服從于丈夫,服從于現實。夫妻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主要體現在:
首先,一夫一妻多妾制。一夫一妻多妾是封建婚姻的基本狀況,一個男人只能有一個妻子,但是可以有多個妾氏。而一個女人卻只能有一個丈夫,否則會被認為觸犯了七出中的“淫”而被丈夫合理的休掉。
其次,毆殺處罰不同。以清朝為例,“凡妻毆夫者,但毆即坐。杖一百,···至折傷以上,各驗其傷之輕重,加凡斗傷三等;至篤疾者,絞;死者,斬;故殺者,凌遲處死。其夫毆妻,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二等。……故殺亦絞。”③妻子只要有毆打丈夫的行為即要受杖刑,如果導致丈夫受傷,則要處相當于平常斗毆三倍的懲罰,導致丈夫篤疾的,妻子就要被處以絞刑,而故意殺害丈夫的,則要被處以凌遲。而丈夫毆打妻子,只要不達到妻子折傷的結果是不受任何處罰的,就算因達到折傷的結果而受處罰,也會因為是丈夫毆打自己的妻子這個特殊情況而減輕處罰,刑法是以懲罰為后盾帶有威脅性的,一方面,將丈夫相對于妻子具有特權地位合理化合法化;另一方面,極大的束縛了妻子的反抗精神。
最后,服喪的不平等。唐朝夫妻服喪的不平等較為明顯,《唐律疏議》中將“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定為“十惡”中的不義罪,長孫無忌是這樣解釋的“夫者,妻之天也。移父之服而服,為夫服斬衰,恩義既崇,聞哀即須號慟。而有匿哀不舉,居喪做樂,釋服從吉,改嫁忘憂,皆是背禮違義,故為俱十惡。④按輩分算,妻子丈夫是一輩的,但是妻為夫服喪卻等同于子女為父服喪,如若在服喪期間改嫁,更為封建社會所不容忍,定為“十惡”中的“不義”,要被處以殘酷的刑罰。在某種意義上說,封建時期的女性根本是被法律所忽視的群體,但是卻承擔著諸多的義務,她們的權利和義務呈現出極大的不平衡。
(二)離婚的不合理
封建時期的女性在婚姻的解除上處于極端弱勢的地位,她們基本上沒有主動請求離婚的權利,此權利牢牢的被丈夫所掌控。古代的離婚就相當于“棄妻”。“七出”法律為“棄妻”提供的七個理由。《唐令》規定:“諸棄妻須有七出之狀,一無子,……七惡疾。”即使有“三不去”⑤約束棄妻行為,由于“七出”的主觀性比較強,再加上丈夫居于家庭的支配地位,他們仍可以輕而易舉的棄妻。相比之下,根據歷代法律,僅在三種情況下,妻子可以要求離婚,一是,夫縱容或強迫妻子與人通奸,《元史·刑法志》:“夫受財而縱容或勒迫妻妾為娼者,夫及奸夫淫婦各杖八十七,離之”;二是,丈夫服刑,《已成婚而夫離鄉編管者聽離》篇的判詞稱:“在法:已成婚而移鄉編管,其妻愿離聽。”三是,丈夫無故打毆打妻子,元律中規定:“諸以非理毆傷妻妾者······并離之”。這三種情況都是比較客觀的條件,所以,主動離婚對妻子來說面對的不僅是社會和族人的歧視,更多的也來自于法律的刁難。
(三)妻沒有財產處分權
在封建法傳統下,妻子僅有財產的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和處分權。在提倡同居共財的封建時期,家長(族長)才擁有財產所有權,家庭成員連私財都不可以有,更不用說有財產處分權了,即便分家,由于男尊女卑,也是由丈夫做家長而享有財產所有權,就連妻子隨嫁的嫁妝也是屬于丈夫的,妻子不能隨意處分。⑥
注釋:
①《史記·貨殖列傳》。
②班固在《女誡》:“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理,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
③《大清律例》,卷28,《刑律》。
④鄭顯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
⑤ 《唐律·戶婚》:“雖犯有七出有三不去。三不去者,謂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后貴,三有所受無所歸。”
⑥宋代案例集《清明集》中的一條判語說:“婦人隨嫁奩田,乃是父母給予夫家田業,自有夫家承分人,豈容卷以自隨乎。”
(作者簡介:郭敏,中南民族大學法學院07級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法學理論,主攻比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