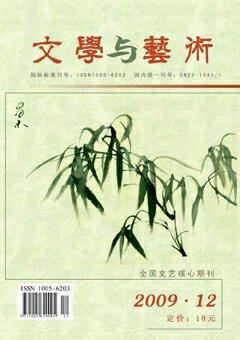中西女性主義詩學的背景差異
張 鑫
【摘要】由于,中國女性主義詩學的產生和成長不具有西方女性主義詩學得天獨厚的學術背景,使得中國女性主義詩學只能是西方女性主義詩學的橫向傳播、移植后變形的結果。因而與西方女性主義詩學相比具有明顯的差異和自己鮮明的本土特征。
【關鍵詞】女性主義;詩學;差異
女性主義詩學是20世紀70年代初首先在歐美各國崛起的的一種重要的文學批評模式與理論話語,它以對歷史文化、文學現象、文學文本的深入反思與創造性闡釋,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及對歷史傳統、文學乃至生活的既定認識。當代法國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代表人物之一露絲·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有一句名言:“在我們這個時代,兩性差別即使算不上最熱門的話題,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按海德格爾的說法,每個時代的人都會熱衷于探討一個問題。而且僅僅是一個。對性別差異的研究也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從理智上獲得拯救的關鍵課題。”[1] (P372)作為一位激進的女性主義學者,露絲·伊利格瑞的表述顯然不無夸張之處,但她準確道出了女性主義政治運動以及包括女性主義詩學在內的女性主義學說在當代西方政治生活領域與文化思潮中占有顯著地位。
經過三十余年的積累,女性主義不僅成為西方左翼文論的重要分支,亦與當代重要的文化理論相互借鑒,彼此聲援。在中國,雖說人們一般以朱虹發表于1981年第4期《世界文學》雜志的《 美國當代的“婦女文學” 》作為中國學術界最早引介西方女性主義詩學的標志,但嚴格意義上的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約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發端。1986年,西蒙娜·徳·波伏娃《第二性》中文版的問世,作為女性主義詩學進入中國的真正標志。從該年開始,翻譯、介紹與嘗試進行批評實踐的文章不斷增多,最終致使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傳播在1989年左右達到第一次高潮。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這一重要契機,更使該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女性年”,女性文化空前繁榮。
隨著譯介的深入,學術界先后涌現了一批自覺借鑒西方女性主義詩學理論的與批評方法并努力使之與中國文化傳統和文學現象的學者與著述,對中國現當代、國外文學乃至古典文學研究均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但是中國女性詩學的成長并不存在西方所擁有的那種得天獨厚的語境。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女性主義擁有自己鮮明的本土特征,即使是西方學者也敏銳的看到了這點。陶麗·莫依如是說道:“1984年秋,我對中國的短暫訪問使我懂得一件事情:把西方的女權主義樹立為中國婦女解放的權威不是西方女權主義者的任務。中國婦女在為把自身從她們的枷鎖下解放出來而英勇斗爭著—在我聲明與她們團結一心、并肩戰斗的同時,我必須承認,我在這個領域并不能儼然以先生自居。”[2] (P3)
相比較之下,我們發現由于女性主義在西方和中國發展的背景與環境不同,其形態與重心并不完全一致,產生影響的廣度與深度也不可同日而語。西方女性主義詩學直接受到了歐美歷史悠久且波瀾壯闊的女權運動精神的滋養,本身可視為女權運動在學術領域的自然延伸。它是以西方婦女長期以來對自身處境所進行的文化反思為基礎,在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弗吉尼亞·沃爾夫、西蒙娜·徳·波伏娃、貝蒂·弗里丹等數代先驅人物的號召與推動下形成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與20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兩次浪潮的實踐經驗與理論成果為女性主義詩學奠定了強有力的歷史文化基礎,婦女文本則以對女性生活和情感體驗的豐富表達,為研究婦女文學的歷史、傳統與美學特征,反思文化觀念中的性別歧視,提供了豐富的實踐資源。20世紀西方文論的多元發展,又為女性主義詩學提供了多種思維模式與方法論的參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女性主義詩學是西方啟蒙思想燭照下理想精神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
與西方女權運動反抗父權制的鮮明目標與決絕姿態相比,誕生于列強覬覦和階級斗爭的腥風血雨背景下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自始就與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血肉相連,成為有關階級、歷史與民族的宏大敘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五四以來由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男性先覺者首先倡導婦女解放的獨特背景,1949年以后執政黨有關男女平等的行政立法,使男女平等的觀念普遍超前于女性群體的思想覺悟水準和社會普遍的心理認同程度,成為一篇華麗包裝的官樣文章。父權制文化背景先在的決定了婦女解放具有先天不足的不徹底性和依附性,女性群體和個體宿命式地被男性解放者居高臨下地設定于接受啟蒙的位置,并被局限在“為奴隸的母親”、“黨的女兒”等空洞的能指和“妹妹找哥淚花流”的行為程式之中。其間,中國婦女被他者決定命運的被動狀態始終沒有獲得徹底改變。她們因之缺乏個體與群體的獨立意識,缺少對女性文化傳統的認同,將解放自身的愿望寄托于社會及男性的恩賜。20世紀30年代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嚴峻、階級斗爭日趨激烈的現實情境,更使中國現代史上曇花一現的“啟蒙”主題隱退為背景,“救亡”主題凸顯于歷史的天幕。涵蓋于“啟蒙”主題下的女性解放問題再度被擱置。正因為此,中國學者劉思謙激進地人為:“中國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自發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解放從來都是從屬于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3]
1949年以后,行政律令下“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深入人心,以及“大躍進”與“文革”期間令人匪夷所思的“鐵姑娘”現象的出現等等,有時人們在盲目樂觀心態的支配下將婦女問題視為過去,仿佛再提此類問題已不合時宜。女性不得不以壓抑自身的性征與心理感受為代價以迎合主流意識形態。新時期以來,雖然五四啟蒙傳統得到接續,但科技的發達與物質的富足又激發起社會的普遍對金錢和物質的欲望。在商品泛濫和物欲橫流的的背景下,是女性為性對象的封建主義沉渣再次泛起,女性再次被推入物化的陷阱。
傅立葉指出:婦女的解放是衡量一個時代人類解放的尺度。從這個意義看來,中國的文明發展形態就整體水平而言尚未達到自然產生西方意義上的女性主義階段。女性主義要成為中國公眾普遍的自覺還有待時日。作為大大超前于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和人們普遍認識水平的意識形態,女性主義觀念在中國只能局限于高等學府、科研院所中部分開放的知識分子和女作家的范圍之內。而且,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浸潤,中國知識群體中雖不乏對女性主義或婦女解放持歡迎、理解和同情態度的男性與女性知識分子,但愿意公開亮出自己的女性主義立場的卻不多。以上所述,便是女性主義詩學進入中國并逐漸展開的過程中無可回避的背景與現實。
由此我們得知,中國女性主義詩學的產生,只能是西方女性主義詩學橫向傳播、移植后在中國土壤的變形。在其本土化的過程中,經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碰撞、磨合,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期待與知識結構對立與錯位之后形成,并受到中國本土婦女問題的獨特性所制約。它在橫向傳播與發生影響的過程中,勢必會不斷產生意義上的損耗、術語理解上的分歧、形式上的變異。譯介者自身文化心理、知識結構與理解興奮點等因素的綜合作用和國情的需要等,又可使其意義不斷被發揮而產生增值。這就使此女性主義與彼原汁原味的女性主義必然并已然大相徑庭。
【參考文獻】
[1]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陶麗·莫依.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M].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
[3]劉思謙.關于中國女性文學[J].文學評論,1993,(2).
[4]楊莉馨.異域性與本土化:女性主義詩學在中國的流變與影響[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