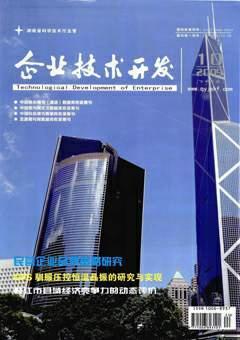傳統文化與和諧社會法制建設
田 磊
摘要:文章從“和諧社會”的政策目標出發,在分析“和諧社會”與法制之關系、傳統文化與法制之關系的基礎上,初步探討應當如何處理傳統文化和法制建設之間的三種關系。
關鍵詞:和諧社會;法制;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8937(2009)20-0163-02
1“和諧社會”與法制
自十六屆四中全會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今后一段時期的重要社會目標以來,全國各個行業中的各項工作無不以“社會的和諧”作為自己工作的目標。那么,首先要明確的是,什么是“和諧社會”?
在我看來,“和諧”一詞意指一種非沖突狀態;那么“和諧社會”便是指非沖突的社會狀態。如果將這種“非沖突的社會狀態”看作是一種應然之理想的話,那么它的標準在哪里?換句話說,達到它有什么樣的要求?在我看來,一個社會能夠稱得上“和諧”,必須具備如下要件:第一,該社會是一個包容多元價值觀的社會。第二,該社會整體上運轉有序而安定。第三,該社會中人人得以正當的手段追求自己理想中的幸福生活。
要滿足第一個要求,即“包容多元的價值觀”必須注重自由和平等;要滿足第二個標準則必須注重安全和秩序;要滿足第三個標準則必須注重人權和正義——自由、平等、安全、秩序、人權和正義——這一切恰恰是法制的內在基本理念!我們完全可以說,良好的法制是“和諧社會”的構成要件,法制是“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制度保障。
如果說,法律是由“規則——政策——原則”構成的話,那么“和諧社會”這一政策目標的提出,就對法制提出了一種更新的、同時也是更高的要求:
其一,它要求法制堅持和完善自由、平等、安全、秩序、人權、正義等基本理念。也就是說,我國的法制必須沿著既有的道路深化和發展,并盡快的修正在以往的實踐中的那些忽視上述理念的做法。其二,它要求法制拓寬自己的視野,在運轉——也即司法實踐的過程中,不能僅僅只重視“法律和諧”,也必須將“社會和諧”作為法制行動的目標。也就是說,法律不能再僅僅只以自身的邏輯行動,而必須以社會效果作為目標來行動。其三,它要求法制必須利用自己“正義的看門狗”的身份,去化解社會的沖突,把社會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保障社會的安定。
簡而言之,“和諧社會”目標的提出,在根本上是對法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進而也就對正在進行中的中國法制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們的法制建設既要提高法制自身的水平——改善既往那些不合理的法條和配套制度;也對法制的運轉范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法制在社會生活中更廣泛的發揮其自身的作用。
面對這種種的、更高的要求,法制建設必須注重更多的因素,必須仔細審視自己所身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以便與社會生活相協調,而傳統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個部分。
2傳統文化與法制
美國學者薩皮爾在《文化:真與假》一文中科學的指出,文化一詞有三種用法,進而也就有三種意思:
其一,指文化的物質和精神的兩方面;其二,指一種確定的、衡量的性價值標準;其三,指有關生活的各種普通態度和觀念。
在我看來,前兩種意思屬于對文化學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概念,對于法律學理探究來說,更重要的是第三種意思上的“文化”。因為法律是以調整人的行為為手段來達到自己所希望的社會關系的,而人的行為,總是基于一定的關于生活的普通態度和觀念來實施的。因此,對于普通生活態度和觀念進行探討,便在是法制建設上具有重要意義的——這種探討是處理“法制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的一個重要環節。
我國的法制(法律及其配套制度)是一個舶來品,其內含的對于生活的普通態度與觀點與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關于生活的態度和觀念并不完全相容——二者之間有交集但并不是全面重合。仔細思考,便會發現二者之間有三種關系:
其一,相同。也就是東西方社會所共有的那些普世性價值觀念。例如傳統儒家文化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事實上便是一種人道原則。這一點,和西方法制理念中的人道主義是相同的。
而這種相同的狀態,無疑會促進我國的法制建設。因為相對于法律是一種“應然意志”而言,文化總是一種“實然存在”。當實然存在的的某種理念、價值觀和意蘊與我們欲求的法律關系之間有某種共同之處的時候,這些實然存在的文化總會在事實上起作用去促進法制。
其二,相異。例如在西方法制觀念中,將婚姻看作是僅僅關于個人的事務;而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卻將婚姻看作是一種家族事務,并對婚姻的雙方附加了許多家族本位的責任——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便是從家族延續的本位出發對于夫妻雙方附加的一種生育上的責任。
人們在這些傳統文化的主導下有可能實施一些與法制理念不合的行為,但所造成的結果并不一定就與法律的欲求相違背。例如將婚姻看作是家族事務的觀念,就有可能從責任、義務的角度出發去要求婚姻雙方善良、忠誠行事,這可以使得婚姻更加穩定——這也是《婚姻法》的諸多欲求之一。
其三,相反。例如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有“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說法,這在事實上表現的是一種厭訟的情緒;而主張、甚至鼓勵人民用法律的手段和途徑來解決糾紛卻是西方法制的基礎理念之一。
正是上述這個“其三”,即傳統文化中與法制內核理念相沖突的這一部分,是值得去探討的問題——它可能是法制建設進程中的絆腳石,也很可能阻礙“和諧社會”的達成和實現。
人是歷史性的社會存在,在人的成長過程中,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和途徑去繼受該社會既往的文化觀念(事實上,當我們在閱讀所謂的“經典”著作的同時,就是在接受一些既往的文化)。這些文化觀念進入人的大腦,和個人的現實生活與際遇相結合,相“發酵”來生成個人的主觀精神。換句話說,傳統文化——尤其是那些關于生活的普通態度和觀念——是人的主觀精神的淵源之一。又由于人的行為,是其個體的在主觀精神支配下的所為;而我們法律是以調整人的行為作為自己作用的機理的;因此,法律便不得不考慮和重視傳統文化這種人的主觀精神的構成性要素。
一個社會傳統文化具有堅實的地理基礎、生物基礎、心理基礎和社會基礎,當這種堅實的、牢固的傳統文化發生作用,指引人們實施某些與法制理念不相符合的行為的時候,我們的法制應該如何去做才會、才能達成當下的和諧?才會、才能不制造新的矛盾?
3解 題
我個人認為,用現實消解傳統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原因只在于:
首先,傳統文化是一種歷史的、客觀的存在,這種特性決定了我們根本無力對其進行任何作為。因為——正如上一段所指出的——文化的產生是在一定的地理基礎、生物基礎、社會基礎和心理基礎之上產生的,而傳統文化是基于其產生當時的地理情況、生物情況、社會情況和心理情況的條件而產生的,面對既往已經客觀存在的地理、生物、心理和社會情況,我們根本無力也沒有任何可能去對其進行改變。這也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對傳統文化本身有任何作為。
其次,我們能作為的,可能改變的只是我們當下的現實。我們可以大罵秦始皇“焚書坑儒”破壞了文化的多樣性,禁錮了人民的思想,導致了文明的斷裂……。但是“焚書坑儒”這一事實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它已經成為我們永遠無法去改變的事實,我們唯一能作的只能是:①繼續承受“焚書坑儒”這一歷史事實給我們帶來的后果;②在已經明白“焚書坑儒”的破壞性后果的情況下,在今天不這么做。
在面對既往已經客觀存在的歷史的時候我們惟一能作的只能是去承受它帶給我們的后果,然后吸取它所帶來“教訓”。
綜上所述,我們只能去改變的是“當下的現實”,我們也只能用當下的作為去改變過去的那些“消極因素”。我們已經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乃至“信息社會”的轉變(盡管僅僅是在路上而未達目標),這種轉變給當下的中國帶來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繼續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不應該——事實上也不可能——回頭。那些產生于“農業社會”的傳統文化,如果和我們今天相沖突,那么就去消解它,改變它!
并且,在我看來,很多學者是過于夸大了傳統文化和現代法制理念之間的沖突關系。事實上,就像上面第二小節分析的那樣,傳統文化理念和現代法制理念之間存在相同、相異、相反等三種關系。“相反”這種導致沖突的關系只是三種情況中的一種——也就是說,傳統文化理念和現代法制理念之間的沖突事實上是有限的,是在某些極個別的領域中和極個別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沖突——此其一。
其二,一切社會中文化從根本上看都有一種“勸人向善”的內核。很多不同的民諺、學理學說從根本上看都具有這種指向。所不同的是,可能表達的角度相異,針對現實情景相異,表達的手法相異而已。這種“勸人向善”的基本內核,在我看來會產生良好的后果——只要當前的現實是良好的。這和法制的基本理念是“相通”的。
其三,正如上面第二小節所說的:文化觀念進入人的大腦,和個人的現實生活與際遇相結合,相“發酵”來生成個人的主觀精神。也就是說,傳統文化并不是單純的自己便成為人的主觀精神的一部分,它總是和人的現實際遇相結合的。人都是“趨利性的”,這種特性也決定了人會主動的去適應現實,進而也主動的去適應現實觀念,并且人也認為這是一種好的趨向——一個例子是“食古不化”一詞是一個貶意詞。當我們的現實為人提供一種能夠使其生活得更好,對其更有利的觀念,那么這種觀念會被他/她主動接受。惟一的問題只是——我們當下厲行的法制是否夠好,是否能保障他/她能夠得到一種好的生活。
因此,我認為,落腳到法制建設上的解題思路就是:第一,對理念相同的傳統文化,法律予以承認甚至強化;第二,對于理念相異和相反的傳統文化絕不妥協和退讓。只要我們的法制是“良法”,只要我們的法制足夠好——能夠為老百姓今日提供一種更好的幸福生活,那么法制應該站出來大聲對那些傳統文化說“不”——我們法制應該有這種勇氣,也有這種責任!
4結 語
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中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
第一,老百姓在生活中不尋求法律。當前出現的大量“私了”現象便充分說明我們的法律,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過只是一些訴諸紙面的“死法”,而并不是社會行動的“活法”。
第二,判決得不到遵守。即便是糾紛的雙方訴諸法院,獲得了判決,那么由于有“法律并不是值得信賴的糾紛解決機制”這樣一種認知存在,敗訴的一方也沒有一種道德上的壓力去自覺自愿的遵守法律的意志——這也就是執行難的問題所在。
一個可以對上述事實予以證明的事實是,在我國民間一直流傳的一句民諺“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在今天重新流行起來。如果仔細審視這句話,就可以看到在這句話的背后,事實上包含著這樣一種由思考和邏輯交織而成的對法律的認知——法律不過是金錢和權勢的附庸品,不過是為金錢和權勢的擁有者服務的;法律自身并不是正義和公理的代表。這句民諺產生于封建社會時期,它反映了老百姓對于當時的公權力的失望和對正義的絕望。但是,它在今天被老百姓屢屢提及而成為一句流行語,這種“流行”不也正反應了老百姓對于今天的法律及其配套制度的某種認知嗎?
如果進一步分析這兩種情況所產生的后果,我們便會發現:①法律被束之高閣,而這必然導致法律的意志被“空化”——已如前述,法制的內在理念(自由、平等、安全、秩序、人權和正義)是“和諧社會”的構成要件。那么這種法制理念的被“空化”就必然導致我們不可能達成和諧社會的目標;②法律制度不能去化解社會糾紛——這是因為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尋求其他的途徑解決問題,則糾紛在事實上依然隱性存在,這種隱性的糾紛隨時可能爆發來破壞社會的和諧;③法律本身成為社會沖突的助推器——當事人在尋求其他解決糾紛的過程中,必然伴隨大量的涉及錢、權的“灰色交易”,而這種“灰色交易”又是新沖突的制造根源。那么在事實上,我們的社會便一直坐在“火山堆”上,隨時有可能有新的沖突出現,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達成“社會和諧”的。
上述因素是我們邁向“和諧社會”的“絆腳石”。要真正的邁向“和諧社會”,我們必須搬開這塊“絆腳石”。但是難題在于:這塊“絆腳石”的內部因素之間形成了一個死結——各個因素之間互為因果。這種互為因果的關系使得我們無法破題——解哪一個環節都是必須的,也是可以的。但正因為這樣,導致我們無從下手。
這是法制的困局,是法制建設的困局,更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困局。如果說我們法制應該有這種勇氣,也有這種責任站出來回應傳統文化的挑戰的話,那么今天的法制是否有這種資格?
參考文獻:
[1] 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 (法)菲爾德伯格.權力與規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