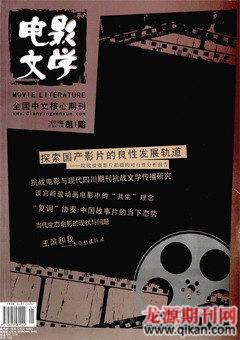阿甘正傳
劉座雄
[摘要]文章通過解析《阿甘正傳》的時代歷史背景,分析了美國夢在這一年代的時代特征。結合美國夢的這些時代特征,對影片中幾個主要角色阿甘、詹妮、丹中尉和巴布的各自夢想的破滅或實現進行分析,說明美國夢受到時代背景的沖擊。通過對阿甘和其他主要角色夢想的比較,影片體現了對特定歷史背景下游離于理性之外的美國夢回歸理性的呼喚。
[關鍵詞]《阿甘正傳》;美國夢;回歸
“美國夢”是美國人最為珍惜的信仰或夢想。傳統的美國夢是一種關于自由、土地、平等和機會的保證,篤信進取心、勇敢和辛勤工作是獲得成功的關鍵。美國夢是一種信念,一種文化,是人們的理想與追求。它的本質是機會均等,人人都有成功的希望和創造奇跡的可能性,人人都有機會“從小木屋走進白宮”,它令所有美國人對生活充滿樂觀和自信。美國夢推崇個人奮斗的英雄,從一貧如洗的學徒工到富甲天下的鋼鐵大王卡耐基;從平頭百姓之家平步青云登上總統寶座的林肯。“美國夢”就像人類社會的理想奇葩,在新大陸這塊嶄新的土地上萌芽發展,曾經那么令人心醉神迷。但是美國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時代特征,在電影《阿甘正傳》中美國夢就有著各種各樣不同的表現形式,反映出二戰以后美國人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的變化。同時電影也體現了對特定歷史時期的美國夢的理性思考。
一、時代背景
《阿甘正傳》橫跨了戰后美國50年代到80年代的歷史。這段歷史正是美國二戰后波瀾壯闊的30年。通過巧妙拼貼,戰后幾十年的美國歷史成了一部阿甘個人的成長日記,影片從一個智障者的視角,通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際遇來影射美國歷史文化的曲折起落,描述了美國這段時期生活的方方面面:種族問題,越戰,政治丑聞,外交風云,嬉皮士,艾滋病等等。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乃至于貓王和約翰·列農等一系列深刻影響美國戰后歷史的著名人物紛紛登場。這些歷史現象和事件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巨大變遷與人們的生活狀態——多數人的消極頹廢與盲目熱情,在這段歷史中,個人價值觀、社會價值觀都發生了扭曲變形。美國夢受到時代的強烈沖擊,被深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著名學者戴錦華先生對《阿甘正傳》評述道:“它及時地出現在當代美國文化四分五裂并喪失了穩定的價值觀念的時刻,為美國社會提供了一種社會融合和想象性拯救的力量。”
二、美國夢在幾個主要角色身上的體現
影片中幾個主要角色阿甘、詹妮、丹中尉和巴布身上都有美國夢不同的體現。
阿甘看起來隨遇而安,是幾個人中唯一一個沒有什么夢想的人。但我們從阿甘身上看到美國人所崇尚的全部美德誠實,勇敢、忠誠。阿甘已超出了一個普通的影片角色。在阿甘身上,我們看到了對生命的執著,對生活的希望,對信念的堅定。在影片中,觀眾看到的是在這種精神的支持下,阿甘這樣一個低智商的人上了大學,在戰爭中立了戰功,獲得勛章。再后來又參加了舉世矚目的“乒乓外交”,然后又在捕蝦中成了捕蝦業大亨,救助了巴布一家的生活,醫治了丹中尉的精神創傷,最后更在環繞美國的跑步中,給千千萬萬人帶來了勇氣和希望。影片中貫穿始終的奔跑已經升華成一種執著堅韌的精神力量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態度,說明堅持不懈的努力總能給人們帶來勇氣和希望。這也是傳統美國夢的重要信念。阿甘不僅是一個普通人,他代表和象征著一個幾乎被每一個美國人心中所珍藏著的那個美國夢,這種神話般的夢幻才正符合美國夢的精髓。相對于影片中其他角色如詹妮、丹中尉、巴布在那個時代遭遇到的歷史事件和災難所帶來的傷害和毀滅,阿甘可以被看做傳統美國夢的象征和守望者。
與阿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詹妮。作為《阿甘正傳》中的女主角,表面上看詹妮虛偽盲從,不懂珍惜與付出。而實際上,詹妮成長于美國20世紀60、70年代,美國的社會價值觀的轉型期,人們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改變。六十年代的“跨掉的一代”用他們獨特的“嬉皮士”生活方式來對抗主流文化和傳統價值觀。他們摒棄對傳統和權威以及傳統意義上英雄的尊敬,遠離家人和現有社會制度,選擇一種逃避現實、追求享樂、否定理性、強調本能的幻滅之路。性的解放、毒品帶來的幻游和遠離現實社會的流浪和群居生活是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沒有堅定的信仰和正確的人生觀,必然成為時代的“犧牲品”。作為這個年代青年人的典型代表,詹妮的夢想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她夢想能成為一個著名的歌手,去做那個時代“聰明”的年輕人所做的事情,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與阿甘回到現實生活,背著吉他與同伴去流浪。詹妮的夢想遠離了美國夢的精神本質。當這一夢想被證明是失敗而且沒有意義的時候,詹妮企圖用自殺的方式來結束她迷惘的青春。從珍妮身上我們看到了她的執著和無奈,更體現出她對主流社會的反叛。
丹中尉和巴布也有著各自的夢想,而且他們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群體。丹中尉是阿甘的上司。他正直、善良,心里充滿了建功立業、為國捐軀、為自己的家族增添新的榮譽的光榮夢想,就像阿甘給我們描述的:他的祖先幾乎每一代都有人戰死沙場,我想他是努力想要盡快趕上他那些英雄祖先。丹中尉是“以國為家”,“一諾千金,視死如歸”,“舍小家顧大家”的美國式英雄主義的縮影,本以為在越戰中能實現夢想。然而不幸的是,阿甘把他從死亡中拯救了出來,這場尷尬的戰爭非但沒能使他獲得任何精神意義上的成就感,而是讓他帶著殘疾的身軀回到了美國。于是丹中尉的戰后生活不可避免地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境地,他的夢想徹底破滅了,處在崩潰的邊緣。巴布是當時處于社會底層的黑人生活狀態和夢想的縮影。他生活的全部都與蝦有關,他的夢想簡單實際,就是能擁有自己的捕蝦船,自己當船長,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改變生活。但不幸的是他死于越戰,在這樣的一個年代,巴布這樣簡單的夢想也無情地破滅了。
三、美國夢的呼喚與回歸
《阿甘正傳》中只有阿甘從不考慮其他事情,努力做好每件事,他的信念和行為簡單而率性。阿甘身上的樂觀向上、堅忍不拔和堅持認為人人都可以創造奇跡的精神是數百年來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識所公認的美德和價值觀。世界是有一定的規則的,當人們無力改變這些規則的時候,像丹中尉和詹妮一樣一味地痛苦掙扎只會導致無能為力的自我毀滅。阿甘似乎沒有選擇余地,服從所有的規則并且堅持不懈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應該做的事,這才是數百年來美國夢的本質所在。與其說“天佑愚者”,不如說,世界更喜歡服從者。美國60~80年代的時代背景使幾乎所有的人都躁動不安,美國夢的信念也因時代的特征而扭曲變形。而阿甘則代表了全部主流文化的走向和祈求:誠實守信、做事認真、勇敢善良。影片恰恰讓這樣一個看似沒有什么夢想,做事簡單但勤勤懇懇的人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雖然用的手法帶有戲謔和傳奇的成分,但毫無疑問阿甘代表著真正的美國夢精神,體現了對“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機會取得成功、創造奇跡的美國夢的推崇和呼喚。
影片中除了阿甘,其他主要角色的夢想、尤其是詹妮的夢想都游離于理性務實的美國夢之外,結果都以破碎而告終。但夢醒時分影片又以不同的形式讓他們理性地回歸到傳統現實的美國夢中來。詹妮經過掙扎夢想破滅后所選擇的現實而平淡的生活,以及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選擇嫁給阿甘,影片給了她一個主流社會的家,回歸是她唯一的歸宿。丹中尉在經過人與神、人與命運的抗爭的失意痛苦后,在阿甘的精神感化下也回歸到理性的現實和理性的夢想中,通過自己的努力也取得了成功,影片同樣通過阿甘的成功使巴布的夢想也得以實現。所有人的夢想最后都回歸到了阿甘身上所代表的傳統美國夢的信念上。通過這種劇情安排,影片實際上是在呼喚現實理性的美國夢的回歸。
四、結語
羅伯特·伯格利在分析影片《阿甘正傳》時稱它“對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運動進行了批判,通過將黑人運動、婦女運動以及反主流文化運動排除在外,以盡力擺脫人們對60年代運動的文化記憶”。這種評論也體現了那個年代人們對主流文化和社會價值觀的背離。影片中唯有阿甘像母親教導他的一樣:“笨有笨的作為”,“奇跡每天都會發生”,始終洋溢著美國人所特有的樂觀向上、積極向上、勤懇務實的人性光輝。對于那個特定年代的扭曲變形的社會價值觀。影片通過阿甘的人生經歷和詹妮、丹中尉、巴布等其他主要角色的夢想破裂和重生呼喚理性現實的美國夢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