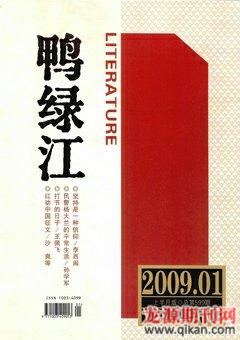秋日的況味
王本道,1947年生于哈爾濱市,1966年高中畢業,1968年大連長青島插隊“知青”。1972年返城,先在營口師專任教幾年,后調入黨政機關工作。曾任營口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盤錦市政府秘書長,盤錦市委常委秘書長,正市級調研員。長期從事散文寫作,作品散見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散文選刊》《隨筆》《美文》等期刊。獲全國冰心散文獎,遼寧文學獎。出版散文專著《芳草青青》《心靈的憩園》《感悟蒼茫》《云水情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盤錦市作家協會主席,國家一級作家。
我供職的市作家協會機關,坐落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庭院里,庭院周圍參差錯落的幾棟樓房里面,清一色是吃文化藝術飯的人,坊間稱它作“文藝大院”也是名副其實的。院子中間,是一處植滿樹木、花草的小花園。與庭院毗鄰的是一條叫做“螃蟹溝”的小河,河的兩旁滿是茂密的蘆葦。自從來到這院子工作,我時常在公務與寫作的間隙,獨自在那小花園里散步,恬靜淡雅的氛圍,讓我在一年四季的時光流轉中,總會有新的感悟。
幾天前那個深秋的下午,我照例在庭院里徘徊。小花園已顯現出枯燥的景象了,幾株曾經枝繁葉茂的梧桐,葉子已經凋零了不少,依舊留在枝上的也已風干得黃爽爽的,還有些綠意的,葉面上也滋蔓著青灰色,操盡了心似的憔悴。花草們也逐漸萎謝干癟,在日漸凄冷的北風之中,偎著九月的蕭瑟。眼前的景象清冷得如同一幅年月久遠的古畫,讓人不禁陷入沉靜凝重的思索。這樣徜徉了許久,伴隨著一陣微風,耳畔傳來悅耳的絲竹聲,并有此起彼伏的低吟淺唱。循聲望去,那歌聲和樂曲聲出自庭院西北隅市歌舞團的排練大廳。這倒讓我驀地想起了,此間正是市“愛樂”合唱團排練的時候。
這“愛樂”合唱團是由市文化部門出面組織起來的一個民間文藝團體,大部分由全市各行業退休人員自愿組成,但加入合唱團必得經過嚴格的把關。條件是:有基本樂理常識;有過專業或業余舞臺演出經歷;身心健康;自娛自樂,報酬無取。就這樣,在自愿報名的數百人之中,精心挑選出一百人組成了“愛樂”合唱團,于去年夏天揭牌。團長是我三十多年前的老朋友了,他早年畢業于沈陽音樂學院,后來陰差陽錯地做起了市間某個局的副局長,雖已年近“耳順”,但“樂心”不死,又被聘來重操舊業。“愛樂”合唱團借用市歌舞團的排練廳,只是每周六、周日下午例行排練兩次。許多寫作者都有擇日寫作的習慣,我是習慣于雙休日或節假日來辦公室寫作的,但整整大半年,卻并未聽到“愛樂”合唱團的聲息。只是有朋友介紹說,合唱團的成員雖多屬退休人員,但在工作崗位上時都是有些“身手”的。其中有高級工程師、記者、教師、機關干部等。雖退出了原崗位,但還在做著各自的事情,如擔負著某項科研課題,參與某個工程項目的籌建等,還有幾位竟是我們作協的會員呢。
去年歲尾,忽然接到請帖,誠邀我參加2008年新年音樂會,節目單上的壓軸戲竟是“愛樂”合唱團的無伴奏合唱。
我是帶著全家參加新年音樂會的。先前的節目已經記不清了,照例是火爆、喜慶、熱烈。臨到“愛樂”合唱團演出,我屏息凝神。大幕之下,整整齊齊一百人的長方隊形,個個粉妝登場,神采奕奕。隨著我那位朋友——合唱指揮那纖細的指揮棒,行云流水般的歌聲汩汩流淌。先是一曲紅色經典《十送紅軍》,悠揚、哀婉、悲壯,唱出了當年革命老區在花落野嶺,草木衰落之際,人民群眾與紅軍的骨肉深情。雖然是無伴奏合唱,但每一位演員情真意切的表情,字正腔圓的演唱,直把臺下觀眾聽得情切切而淚淋淋了。接著是一曲《茉莉花》,抑揚頓挫,情意綿綿,妙趣橫生。最后一曲《難忘今宵》,臺下觀眾主動用掌聲為臺上演員伴奏,臺上臺下融為一體。謝幕之時,相鄰座位上幾位以往的同事簇擁著我到臺上與演員們合影,在與他們逐一握手時,竟認出了合唱團演員之中,有許多我在工作崗位上時熟悉的面孔。
循著花園中的小徑,我邊走邊諦聽著耳畔的樂曲和歌聲。這一刻周遭的一切竟那么地溫暖而明麗,毗鄰庭院的那條彎彎曲曲的小河,河岸不遠處廣闊的收獲田野,都透出一種蒼勁的秋光。隨著樂曲和歌唱的戛然而止,結束排練的合唱團成員們三三兩兩走出歌舞團的大樓。從經濟主管部門退休的老張是我多年的朋友,見我在園子里散步,老遠地跑過來與我搭話。幾個月前,他患胃癌做了切除手術,但看起來還是那么矍鑠。問起他的病情,他樂呵呵地說:“算是判了個‘死緩,但也想開了,這世上哪有‘無期的人啊!”說著又伏在我的耳邊,神秘兮兮地說:“有件事還想求你老兄幫忙通融一下呢。這次手術回來,團長找我談話,為了照顧我的身體,打算把我從高音部調到低音部,我有想法,能不能不調了?”我開玩笑回答說:“做了那么大的手術,不讓你下野出局就不錯了。”他聽了立刻急著說:“我真的能唱高音,不信唱一嗓子給你聽!”看著老張那一臉的癡情,我想這個忙真的是要幫了。順便我也向他提了一個積蓄心中已久的問題:“合唱團的每一個曲目要分很多聲部,許多人在整個曲目中只唱那幾個固定的音符,不枯燥嗎?”聽罷,老張立刻眉飛色舞地說:“怎么會枯燥呀?雖說自己只唱幾個音符,但每個音符都是和弦中必不可少的,大家合起來,不就是完美的曲目嗎?其實這世間,每個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整個社會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環環緊扣,整個社會的鏈條就堅不可摧了,這也是和諧啊!”老張的話深深打動了我。
颯颯秋風之中,老張邁著沉穩的腳步與我揮手道別。老張身前身后,“愛樂”合唱團的人們談笑風生地漸次走出“文藝大院”。這些年逾“耳順”的人都曾在不同的崗位上奮斗過幾十年,各自都有著堅定的信念和良好的習性。如今雖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但卻退而不休,及時行樂,心地寬闊而仁愛,見利不惑而獨善其身。這種逍遙自適,飄逸豁達的精神,實在是人之真性的一種睿智和溫良。僅就年齡而言,說他們“老氣橫秋”抑或是“徐娘半老”都不為過,但是換一個角度詮釋他們的“老”,又何嘗不是一種風韻和底蘊的標志呢?內在教養的優雅,使得這些“耳順”之年的男女們神態飽含著端莊的恬靜與幽然,讓他們的生命天然地充滿著澎湃的活力,相對于那些本來日子過得已經很富足,卻終日焦灼、緊張,為高檔轎車、高檔時裝、高檔裝修而奔忙的人來說,這些人所具有的才是一種真正的高貴之氣。
秋風漸緊了,蕭瑟的秋風之中,我聽到有絲絲哨音在鳴響。啊!是河邊那片灰黃的蘆花在與秋風共舞。我曾贊美過蘆花的瀟灑,它有配合風聲的勇氣及在風中不屈的舞姿。南方的竹,北方的葦,自然界中再也沒有像它們那樣最能代表各年齡段女性風采的植物了。身旁的幾株梧桐似乎在風中沉默著,它的每一片綠也完整,黃也完整的葉子,毫無愧色地完整地飄落下來,鋪滿了石階磚徑,任風去橫掃,任人去踐踏,依然是蒼綠,依然是焦黃。“天下皆憂得不憂,梧桐暗認一痕秋。”蘆花之舞,梧桐葉落,不正如這些走進秋天的男女們此時的況味:滲透著一種尊重自然,洞悉自然的人生大度!
淹沒生命的只有自然,而強有力的生命以及生命所煥發出的悠閑之氣卻能創造出多彩而又從容的人生季節。
責任編輯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