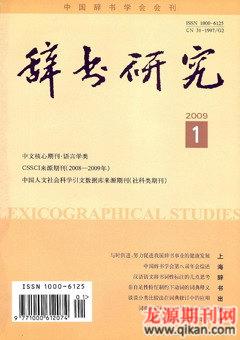詞典釋義提示用語的混亂例談
顏 娜
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是全國絕大多數高校所采用的漢語語言類教科書,符淮青先生的《現代漢語詞匯》也是很有分量的詞匯學專著,這兩部極具權威性的著作在詞的轉義方式這一問題上,基本上都認定,詞的轉義方式只有比喻和引申兩種。在新詞新語的研究中,很多學者受借代造詞的影響將“借代”視為第三種舊詞新義產生的途徑,因為這種情況特別少,所以所舉之例往往很難充分說明其觀點。但是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借代義”(韓陳其《詞的借代義》,見《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這種提法確實值得我們重新考量頭腦中所固有的語義形成規律的可靠性。
比如,“紅領巾”一詞的第二個義項“少年先鋒隊員”(見《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既非比喻義,又非引申義,而是明顯的特征代本體的關系,所以應該被認為是借代轉義。再比如,第5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烽火”一詞的釋義,第一個義項是本義,“古時邊防報警點的煙火”;第二個義項為轉義,“比喻戰火或戰爭”。(見《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很顯然,把第二個意義視為比喻義是不合適的。“比喻”這種轉義方式,是以詞的本來意義為基礎,根據對事物之間相似性的聯系的分析和認識,使原義派生出新義的方法。我們可以判斷“烽火”與“戰爭”之間的這種關系并不是相似性,只能認為是相關性而已,所以,這個義項不應該看作是通過比喻的途徑產生的。然而,這種相關到底是引申方式里強調的相關性還是借代這種方式所認定的相關關系呢?我們無從區分。還有“伯樂”一詞的釋義,《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和其他一些新詞詞典當中對這個詞的轉義義項陳述如下:
后用來比喻善于發現和選用人才的人。(《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現引申為指善于發現、引薦和使用人才的人。(語文出版社《新詞新語詞典》增訂本)
現借稱善于發現、舉薦和使用人才的人。(四川辭書出版社《新詞新語詞典》)
同一個詞,不同的提示語,體現出編者在判定其轉義途徑上存在分歧,同時說明我們在詞的轉義方式這一問題上的概念界定是非常模糊的。
“比喻”和“引申”作為各種語言中詞義發展最普遍、最重要的兩種轉義方式,從詞匯系統的角度看,它們主要是根據語言經濟原則運用的一種特殊的、以不造詞為造詞的命名方式;從語義運用的角度看,前者借助的是修辭的方式,后者借助的是聯想的方式。“借代義”同“比喻義”一樣,是從修辭借代用法固化而來并可以脫離具體語境而被理解的意義。雖然“借代義”是由詞在修辭上的借代用法發展而來,但并不是所有在修辭上有借代用法的詞都可以固化為詞的借代義,當修辭現象轉化為詞匯現象的時候,就必須從詞匯學的角度來判定了。在詞匯學中一直強調語義對于詞的內容和形式的重要性,因此對詞的轉義方式的判斷必須認真分析舊義與新義的語義重心之間的邏輯關系,判定引申義所遵循的關聯性原則,確實很容易和借代方式所認可的相關性混淆。但是我們認為,只要明確能被認定為借代轉義的,其舊義和新義所強調的內容大多是整體與部分或是本體與特征、屬性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這種關聯性產生的前提是事物之間的整一性,因此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轉義同本義之間的關系距離比建立在聯想方式上的引申轉義要密切得多,這應該是判定這兩種轉義方式的最本質標準。
有鑒于此,我們認為“烽火”一詞轉義的第二個義項的提示用語應為“借指”或“借稱”,而“伯樂”一詞的轉義既非“比喻義”,又非“借代義”,而應該是引申之后的泛指義。《現代漢語詞典》作為規范性的辭書,在這一問題上還應斟酌。
詞的轉義方式是學者們就現有的詞匯現象所總結出來的一種語義形成規律,它不可能是恒定不變的,隨著語言事實的發展變化,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它的科學性。只有不斷地去完善這些模糊概念的界定,才能使我們在應用性領域中做到“有法可循”,編纂出高質量的辭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