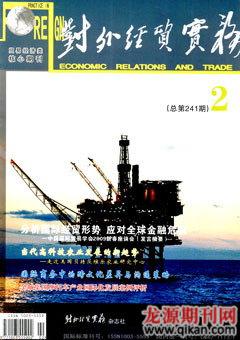2009年我們將被帶向何方?
孫立堅
(一)
2009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嘯將把我們帶向何方?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就要對這場危機的特征給予充分的認識。縱觀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我們遭遇過很多次危機的洗禮。單單是“金融全球化”浪潮不斷推進的這幾十年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危機就有三個:第一次是70年代后期中南美的債務危機,起因主要是在于這些國家的政府為了將沒有“活力”的私營企業打造出競爭力,便采用國有化的方式來推行改革。為此,大量發行了政府債券,由于國內百姓收入能力有限,中南美政府在“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下,主動去借助不斷開放的國際金融市場,進行大量舉債——“對外赤字融資”就成了當時拉美國家資金的主要來源方式。于是,它帶來了銀行信貸的盲目擴張,這又嚴重損害了當時想通過固定匯率制度來控制自己國家高通脹的外匯管理模式。結果,國家財政赤字蔓延,貨幣發行泛濫,造成了市場的匯率價格嚴重偏離政府所執行的固定匯率水平。于是,廣大的消費者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紛紛開始將本幣換成價值穩定的外幣,這種“資本逃避”行為很快使得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被市場掏空。而且,外債的償還由于當時沒有了外匯儲備和國家創造財富的經濟環境而變得十分渺茫。后來,國際金融市場真正擺脫中南美危機的困擾,還是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當時,債權國的銀行集團在日本首相倡導的“宮澤構想”的框架中達成了共識——以放棄或減輕中南美債務的形式,幫助中南美債務國走出了低增長的怪圈,而國際金融機構也終于從巨額的不良資產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國際資本重新流入新興市場的狀況標志著金融全球化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總之,那場危機的特點是國家財政狀況惡化,貨幣發行泛濫等因素導致了大眾自發的資本逃避行為,而引發了十年之久的拉美債務危機。
第二次,較大的危機是92年來自于歐洲較發達的先進工業國家。那里之所以爆發了較為嚴重的貨幣危機是因為歐洲貨幣聯盟執行了兩個互相沖突的政策目標。一是保就業,這主要來自于各國工會的壓力,因此貨幣和信用的增長是在所難免的。二是為了更加強化歐洲區域的經濟聯盟,各國貨幣制度上采取了盯住德意志馬克的匯率制度,這就要求央行的貨幣政策要有節制,不能“獨立”擴張,否則會造成本幣對馬克的貶值,從而嚴重影響到自己國家貨幣制度的穩定。當時,市場的投機力量也已經意識到這兩種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各國政府一定會放棄其中一個,而且這一個目標就是盯住馬克的貨幣制度。于是,市場投機力量就大量拋售意大利里拉和英國的英鎊,很快危機就蔓延到其他歐洲國家,一開始為了保住這雙重目標,各國央行還收緊本幣,但后來工會反對這種做法,使得各國央行不得不放棄固定匯率制度來保證自己國家就業所需要的貨幣增長。這場危機也更堅定了后來歐洲搞統一貨幣的決心。雖然這場危機對發展中國家影響不大,但是,它確實放慢了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的節奏。
第三次危機是94年墨西哥危機以及97年東亞危機。這屬于同一類的新興市場危機。主要還是反映出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各國經濟基本面出現了惡化狀態,比如,實際匯率升值,貿易逆差擴大,資產泡沫崩盤等。與此同時,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開始日益顯現出來。一些金融機構的壞賬成了國內海外機構的心病。在拉丁美洲,缺乏流動性的資本市場,經不起外資流入和流出的沖擊。尤其是94年夏天,當墨西哥政局出現不穩定事件——總統候選人被暗殺的時候,再加上美國政府為了控制投資過熱不得不進行加息的時候,資本外逃現象的日趨嚴重,就讓墨西哥股市大跌,匯率大貶,通脹水平也一下子高騰起來,這些國家的經濟為此承受了嚴重衰退的代價。另一方面,在東亞危機的案例中,由于大量的外商機構,意識到新興的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和中國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紛紛撤離東盟國家和地區而進入中國大陸,于是,這些東盟國家的金融機構就靠大量的短期外債來支付進口設備所需要的外匯,同時靠短期外債來支付生產項目的開支,以沖銷外商直接投資的撤離所造成的項目投資規模下降的問題。結果,這種融資模式造成了兩大不匹配問題,這也是東亞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一是幣種不匹配。借外幣投資國內項目,爭取本幣的投資收益。因此,匯率風險隨時都存在。二是期限不匹配。就是借短期外債去做長期項目投資。于是,資金的流動性被犧牲掉了。結果,當市場需要流動性,需要外幣的時候,國家只能動用外匯儲備來干預,隨著外匯儲備不斷減少,外債不斷增加,進口設備導致的貿易逆差也在不斷擴大,海外金融機構恐慌性的“銀行擠兌”勢力就變得越來越猛,掏空了東盟國家的外匯儲備,造成了這些國家和地區本幣大幅貶值,銀行倒閉,股市崩盤,從而將東亞所打造的實體經濟的奇跡,拖入了泥潭,失業問題也變得十分嚴重。東亞危機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銀行信貸管理和監管機制嚴重缺失,最終導致外匯儲備減少和外資擠兌行為發生,并迅速蔓延到開放程度高、但本來不應該發生危機的國家和地區。
上述三個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發生在金融市場對外完全開放的環境下。中國幸免危機也是因為我們還有一道防范外部沖擊的資本市場管理的防火墻!今天,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大海嘯再次爆發,它到底會不會像上面那些危機那樣,對發展中國家產生巨大的影響,還是會很快平息,不至于影響到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2009年世界經濟會受到哪些較大的挑戰?中國經濟怎樣才能擺脫金融風暴的糾纏?這些都是全社會上下,甚至包括海外各界都共同關注的問題。
(二)
我們認為,這次危機,和以往不一樣,它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首先,它已經從個別的信用危機(第一階段的特征)演變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系統性的“流動性危機”(第二階段的特征)!其主要原因在于監管模式的落后和“金融創新”的濫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新興市場國家重蹈覆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金融創新濫用導致的“去杠桿化”行為確實讓支撐世界經濟發展的歐美投資和消費迅速減少。這樣就會嚴重影響到對其市場依賴較大的新興市場國家制造業出口的規模。這也是解答了為什么亞洲的破壞主要是來自于對外部經濟嚴重依存的實體經濟方面的疑惑。其次,這場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必然結果。一邊是貿易赤字不斷膨脹的消費大國美國,一邊是貿易順差不斷積累的制造業大國東亞,甚至歐洲。總有一天,當債務國的償還能力無法讓債權國信賴的時候,債權國的資本撤離一定會讓美國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今天的金融大海嘯雖然是世界經濟失衡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但是,今天債權國身份的發展中國家自身也離不開美國,主動去解決貿易逆差的動力
也因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壓力而顯得力不從心。于是,人們放棄投資,減少消費,確保自己流動性的恐慌時刻,毅然選擇了擁有貨幣主導權的美元!美元不跌反漲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前,雖然美聯儲通過零利率政策來增加持有美元的機會成本,為今后美元貶值打開了“方便之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金為王”的流動性恐慌階段已告段落,即使美元告別了恐慌性的升值,未來歐元的強勢或其他貨幣此起彼伏的增值現象依然可見。2009年要擺脫這樣的恐慌階段,讓市場進入修復和資產重構的調整階段(危機的第三階段),奧巴馬新政府還需要盡快找到讓海內外信服的新的增長點。比如,新能源技術推廣就可能是美國下一個增長戰略的“候選之一”!盡管如此,世界經濟的失衡格局在短期內絲毫無法解決,而就業和增長卻可以在一個新的增長環節中得以緩解。也就是說,如果明年世界各國政府鼠目寸光,打起“貿易保護”戰,那么,它所導致的世界經濟的進一步萎縮反而會讓我們的危機修復時間變得更長、更痛苦!
當然,制造大國出口所造成的大部分美元資產還只能再流回美國去實現保值的功能。這種回流客觀上也是為美國的金融創新和杠桿融資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流動性保證。所以,今后防范這種金融創新濫用類型的危機,就不能單靠一國的力量,而要靠各國之間的合作來完成。比如,要求跨國公司、跨國金融機構對自己的投資項目和理財產品要給予足夠的信息公開。同時,要在每一環節中,加強對高層管理人的監管,否則,高智商的貪婪者一定會設下圈套讓無知者“心甘情愿”的鉆進來,從而再上演金融大海嘯的悲劇。又比如,改變世界經濟失衡牽涉到各國自身的產業結構調整,非一國政府能獨立完成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經濟失衡并不是件壞事,可能是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環境中,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控制金融創新濫用和消費過度(償還能力不足)的問題。如果這類問題能被有效解決或控制,那么,世界經濟暫時的失衡也不會產生像今天這種致命的問題。
(三)
總之,這次“金融大海嘯”不像前三次危機那樣,影響只局限于危機國家和局部區域,對付前三次危機的重演,我們只要控制好自己國家的財政赤字、信貸規模、資本市場開放程度,匯率制度,外債管理和貨幣政策目標之間的協調性,以及區域范圍內的金融合作,就能很快度過難關。而且,當時各國經濟增長,很快就借助內外市場有效的調整機制走出了危機的低谷。但是,這次完全不同,它是由擁有貨幣主導權的美國所造成的。長期以來,由于它獨到的金融創新能力,技術和品牌的核心競爭力,全球資本和商品都“自發地”匯集到美國,造成不可持續又無法有效控制的失衡格局。對付這場在金融全球化環境下所爆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我們只有再次利用好經濟全球化的環境,加強世界經濟的合作和政策的協調才能根本擺脫危機的糾纏。
具體而言,2009年在各國政府積極的救市行為的作用下,會在上半年結束“流動性恐慌”的危機第二階段,而進入“修復和資產重構”的危機第三階段。至于能否盡快擺脫低迷發展和市場蕭條等第三階段的危機特征,這就要取決于各國政府之間政策的“協調”程度。如果我們堅持對外開放,提高對金融活動中“委托與代理”關系的激勵監管程度(強化對人的監管),不搞“沖銷型”的宏觀經濟政策,比如,降息競爭等,而讓市場從恢復的價格體系中找回信心和感覺,那么,即使明年貿易逆差或順差進一步擴大,資金周轉所帶來的市場活力一定會讓金融大海嘯造成的財富損失和心靈創傷控制在最小的范圍內。但是,如果過分強調各自眼前的國家利益,不顧對方經濟發展所能應對沖擊的承受能力,而在貿易順差和逆差上斤斤計較,那么,即使從局部看或從一個國家層面上看,貿易不平衡確實在縮小,但是,日益攀升的保護主義勢頭所導致的世界經濟規模,就一定會不斷萎縮,各國就業和增長的恢復也會變得更加漫長。當然,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生態環境,即技術創新、金融創新、監管模式創新和制度創新以及文化兼容等要素得以不斷改善,以及各國收入差距和發展階段的差異逐漸縮小,世界經濟失衡狀態的緩解,就必然是世界經濟格局演化和發展所帶來的客觀結果!而人為的通過貿易保護主義方式來“糾正”世界經濟失衡格局的努力將會顯得蒼白無力,弊多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