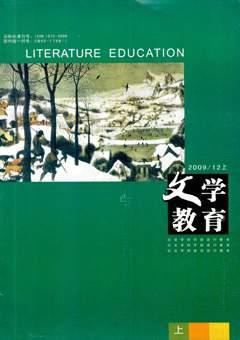白描背后的黑色幽默
2009-04-13 05:29:20李遇春
文學教育
2009年12期
這是一個“禮失而求諸野”的時代。置身都市的現代人在現代格式化生活中幡然醒悟,他們把眼光投向民間,投向野地,投向所謂的原生態,寄望于在民間野地中尋找到安妥現代人疲憊靈魂的憩息地。于是每逢所謂黃金周,城市人便像蝗蟲一般涌向鄉村,涌向那些所謂剛剛開發或者尚未完全開發出來的所謂新興旅游熱點。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到來不僅污染了當地人的純樸心靈,而且對當地的自然生態也是嚴重的破壞和吞噬。現代人已經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破壞者,盡管現代人時常以世界的拯救者自居。這是現代人生存荒誕的一種表征,也是現代人無法解脫的生存悖論之一。
但僅僅寫出這樣的荒誕還不夠,田耳的《到峽谷去》在現代旅游的時髦題材中開掘到了更深層次的荒誕意識。這篇小說雖然寫的是兩個城市婦女帶著孩子去一個偏僻山鄉旅游的尷尬經歷,但作者的用意顯然并不在于對這兩個城市婦女受到當地人的欺騙抱以廉價的同情,甚至也不在于對當地民風受到現代城市消費觀念的熏染而表達文化的批判,如果是那樣的話,這就是一篇蹩腳而俗氣的趨風之作了。田耳的這篇小說自有他獨到的地方。作者的構思帶有整體的象征性和寓言性。按說,題目曰《到峽谷去》,很容易喚起讀者的常規閱讀期待,比如小說中將敘述某種穿越峽谷的驚險經歷,或者穿插某種浪漫情感故事,嚴肅者類似艾蕪的名篇《山峽中》,低俗者就是那種司空見慣的拍案驚奇的通俗小說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少兒科技(2022年4期)2022-04-14 23:48:10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好孩子畫報(2018年7期)2018-10-11 11:28:06
今古傳奇·故事版(2016年24期)2017-02-07 04:29:04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
數學大王·低年級(2014年7期)2014-08-11 16:36:44
百花洲(2014年4期)2014-04-16 05:5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