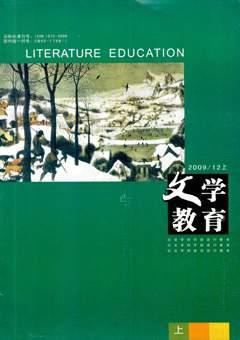為微小的生命歌唱
2009-04-13 05:29:20鄒建軍
文學教育
2009年12期
讀了東蕩子組詩《寓言》,人的心靈受到種種震撼:在永恒的時間面前,人類的生命何其渺小;在遼遠的自然山川面前,動物的生命何其微小;然而,只要有一種精神、一種信念,生命的價值就可以實現,生命的意義就得到體現。那么,再細小的生命,也是極為可貴的。同時,詩人在藝術上的種種講究也令人刮目相看:意象的新穎、意義的空白與語調的調適。
詩人對于生命的感悟與歌唱是令人動情的。不過要注意的是,詩里多半不是對自我生命的吟唱,而是對于他者生命的感悟。在《伐木者》中,詩人對伐木場工人那樣一種平凡的人生有所認識:他們雖然以自己力量、讓閃光的斧子砍倒“年老的朽木”,可是并不知道要堆放的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斧頭為什么閃光/朽木為什么不朽”這樣一些高深的人生哲學。在《王冠》中,詩人為哪些平凡的螞蟻而歌唱:“應該為它們加冕/為具有人類的真誠和勤勞 為螞蟻加冕/為螞蟻有忙不完的事業和默默的驕傲/請大地為它們戴上精制的王冠”。“螞蟻”是再細小不過的生命,然而在詩人看來卻十分偉大,因此要求“大地”為他們“加冕”。其實這正是對一種勤勞人生的禮贊。組詩的主題并不是什么政治譏諷,也不是什么時代想象,而只是表達對自己感受到的生命的一種崇敬,抒寫自己內心的一點觸動。這正是體現了詩人的獨立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每一個人都是地球母親懷中平等一員,生活著的時候是這樣,死去的時候也是這樣。……
登錄APP查看全文